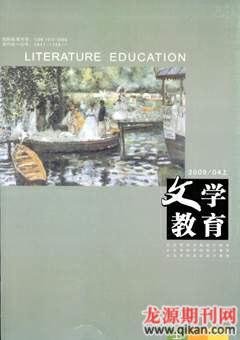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的生存論構想
自20世紀90年代始,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遇到了嚴峻的挑戰。雖然有人從素質教育、人文教育等層面為之開出了不少的藥方,卻依然難以打破其困境。為此,筆者認為,現當代文學教學不妨從“生存”出發重新設計現當代文學的教學理念與思路。
一
雖然在以前,現當代文學曾經在高校諸多學科中一直名列前茅,但是,從90年代以來,由于社會、文化語境的嬗變,現當代文學教學已經而且正在遭遇重大的挑戰。
其一、教學空間遭到大幅度擠壓。從90年代初期開始,為了生存,高校既要滿足黨和政府加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又要應對市場的殘酷競爭,不得不大量增加了與之相關的課程,從而導致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課時量大比例地降低。如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的現代文學史從144個學時減至當前的72學時,課時量整整壓縮了一半。當代文學的遭遇與現代文學相似,在此不贅。課時減少的幅度這么大,卻要完成同樣多的教學任務,對于教師來說,其難度可想而知。
其二、現當代文學日遭冷落,熱度越來越低。學生的興趣逐漸轉向流行歌曲、電子游戲等快餐式的消費文化,對其興趣越來越小;同時,為應對逐漸加大的就業壓力,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計算機、英語等應用性學科上,所投入的精力也越來越少。
其三、時代對其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為了應對人才市場的殘酷競爭,現當代文學教學必須圍繞著“市場”轉,將學生的就業放在第一位,否則就會被“市場”淘汰;另一方面,在消費文化泛濫的語境中,作為人文氛圍最為濃厚、最富有探索性、最需要為民族的發展提供價值支持與思想動力的文化中心的大學,時代更需要它為社會提供一個境界高遠、意趣高雅、能夠為整個社會文化的健康發展做出表率、引領時代揚帆遠航的“精英群體”。現當代文學作為人文學科,自然更應該加入其中,將學生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趣味等的優化放到更為突出的位置上來。可見,時代對現當代文學教學的要求是復式的,比以前更高,也更為實際了。
二
面對挑戰,現當代文學的教學模式卻依然比較保守、單一。迄今為止,最為流行的依然是以知識傳授型為主的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把現當代文學當作一堆業已死去的社會性知識群落,而不是鮮活靈動的生命現象和豐富多彩的審美現象;其目的只是讓學生了解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怎樣的文學現象,以及這種文學現象產生的必然律,而不是刺激學生的生命體驗、審美知覺,啟發學生的生命感悟與審美想象,更不是改造和優化學生的人格心理結構。故此,“滿堂灌”、“一言堂”等教學模式才根深蒂固,難以轉變。
當然,面對挑戰,不少專家也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有人深感現當代文學教學的“人文教育性質不足”[1],提出“從現當代文學‘人的文學核心命題與高等教育‘以人為本思想的關聯中,探尋現代教育如何培養具有人文關懷、人文精神高素質優秀人才的路徑。”[2]。他們把現當代文學看作中國現代“人”覺醒與解放的足跡,珍視其中所蘊含的人文價值與審美經驗,將教學目的轉移到學生對人的價值、人的覺醒等人性美與藝術美的追求上來;有人則針對市場需求,更為關注學生的專業技能,將重點放在學生的文學審美能力、文學想象能力以及寫作能力上來,主張通過現當代文學教學來培養市場所需要的具有高素質、高能力的應用性人才。如果說,上述兩類姑且名之曰“人文教育型”和“能力培養型”,那么,筆者以為,它們依然不足以解決當前的問題。要應對當前的挑戰,新的教學模式必須滿足如下三個條件:人文性、應用性與趣味性。缺乏應用性,只講究人文性與文學性,根本抵御不了殘酷的人才競爭;而不注重人文性、只專注于應用性技能,無論是審美、想象還是寫作能力的提高顯然也是無源之水;同樣,人文性和應用性都過于嚴肅、沉重,與大學生在輕松、休閑的娛樂文化氛圍中養成的生存心態與審美趣味有著相當的距離。
那么,真正的出路何在?筆者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應當走向“生存”,在生存論的基礎上重建其理念與思路。
首先,現當代文學教學只有立足于“人的生存”,將其目標指向“人的生存”,才能回歸本真,走出迷途。在生存論哲學看來,“先于別的一切,我們存在,我們在此”[3]。生存是“一切知識、事件或實物”的源頭。現當代文學及其教學當然也是應人的“生存”需要產生的,不能不歸結于人的生存。人的生存為我們追尋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的本體性價值提供了根本性依據。既然如此,現當代文學教學自然要面向生存。
其次,只有“面向生存”,現當代文學教學才能兼備上述三個條件,突出重圍。在生存論的意義上,“生存”有兩重含義。其一,此在的“實存”(living),也就是個人生命的存活。“實存”是生存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實存”也就沒有生存。所以,生存論哲學并不排斥人的經驗能力與社會能力,也不反對經驗科學。“此在依賴于經驗不斷地重構世界,并以其實存的目的來改造世界、配置世界。”[4]其二,生存更是一個力求把握人的生存真諦的反思性概念,并非只是“生命的存活”,更意味著“生成的存在”。“此在”絕非一般意義上的生命存在,總是在對生存意義的追問中存在,希望超越既定的存在狀態,從既存的不完善的世界和自我中超拔而出,再造一個更為和諧、美好的新世界和新自我。故此,現當代文學教學既不能只重“應用性”而抹煞人的存在意義與自我生成的超越性追求,也不能單單揪住人文精神與終極關懷不放而不食人間煙火,而只能是“既幫助人們‘利用厚生,又能夠幫助人們‘安身立命的整體性的、和諧性的教育。”[5]同時,現當代文學教學既然面向生存,就一定要以“人的生存”的豐富性來要求自己的內容和形式的豐富性。這樣一來,所謂人文性、應用性、審美性、趣味性以及它們之間的融合,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三
那么,現當代文學教學“面向生存”又意味著什么呢?生存論哲學在教學理念與思路上又能帶給我們怎樣的啟迪呢?
生存論哲學面向生存,把人視為生存論的出發點和根本依據。在海德格爾看來,生存是“人”的存在,他把人稱為“此在”,并認為,“‘此在是根源性的,意向性以此在為根據,此在是意向性之根。”[6]這種作為“此在”的“人”的存在,也就是“我”的存在,具有“屬我”的性質,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欲、有想法有追求的“我”:“此在之一切活動的目的,并不指向任何別的地方,而是指向‘其本己的自身”[7],他所選擇的總是自己的可能性,“在選擇中所獲得的也總是屬于自己,而不是他人。”[8]從“人”出發,從“我”出發,生存論把“生存”看作“在世存在”:“他處于與他人的關系之中,并且從一開始就處于某個世界‘之中;必須認識到,沒有‘他的世界,人就不存在,而沒有他,他的世界也不存在。”[9]然而,他被“拋入”世界,卻不想為世界所淹沒,不想死死固守“這些共享的公共的‘世界”所制定的文化標準與社會規范而成為“他者”,而總是希望將個人的印記打入這個世界。因此,“世界”換一個角度看也就是“存在的敞開狀態,即存在向我們展示出來的意義整體”[10];而“人的存在的敞開狀態意味著人在不斷地超越,而這種超越性實際上指的就是其時間性,即生存的意義”[11]。當然,生存意義不會自動地顯現出來,“此在必須對其生存目的有所洞察并以之作為生存的方向,當且僅當此在對其生存目的有所領悟之際,此在的生存意義才成為可能。”[12]那么如何領悟呢?海德格爾認為,只有“超越主客關系,從更高的基礎上回復到主客融合的整體……以內部體驗或參與的方法”[13]才能領會生存的真諦。需要說明的是,“生存”不僅僅意味著對生存意義的領會,更是“在起來”的意向性行動。簡而言之,生存論以“人”為本體性根據,把“生存”視為在世展開、超越既存、通過內在體驗來理解生存意義、并外展為意向性行動的人類活動。站在生存論的角度上來看,中國現當代文學就是中國現代人在血與火的考驗中擺脫生存困境、領會生存意義、追求生存與發展的圖景與足跡,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一個特定的知識群體以一種特定的文化為背景以特定的藝術形式對生存論哲學所作的形象展演與詮釋,它致力于對諸如“人”、“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人的尊嚴”、“人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存目的”、“人的生存質量”等一系列樸素而精深的問題做出自己的思索、追問和解答。如,“人肉宴席”與“想做奴隸而不得”等文字,其實是魯迅先生對“當下”、“此在”的悲痛與憤慨;謳歌涅槃的鳳凰、禮贊轟鳴的雷電,其實是郭沫若以詩的形式寫就的“此在論”;以《家》為代表的巴金作品,張揚的分明是反對禁錮和壓抑的存在的“屬我性”;以大量性愛描寫而在當時文壇獨樹一幟的郁達夫作品所宣泄的也正是一個有血肉、有情欲的“真人”的人性深層的生命躁動……
據此,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應當樹立“面向生存,以人為本”的理念,將“人”放在第一位,將培育在復雜的生存環境中以無畏的生存決心、勇氣與意志來追求超越、自我再生的“此在”視為其本真性目的。也就是說,從專業特點出發,現當代文學教學應通過對相關作家作品等的體驗、領悟與對話,激發并誘導學生養成以人為本的文化理念、追求卓越的生存決心、勇氣和堅忍不拔的生存意志,具備較強的生存能力、審美能力、思維能力與寫作能力。
為此,教學思路就不得不予以相應的調整。“以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主要是從歷時的角度梳理史的線索,在此基礎上,評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學現象和文學潮流,目的是使學生獲得應有的文學史知識,是一種典型的知識型教學模式。從以往的教學實踐看,許多同學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名作的理解,往往過于依賴文學史教材中的學術定論,而輕視或忽略了個體在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中對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將自身的情感體驗、生命意識融入對作品的審美體驗,因而雖然獲得了知識,但對自身的人格和素質,并未產生太大的影響。”[14]為改變此異化狀態,教學重點應從文學“史”轉向“文學”史,進一步提高與突出“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生存論視野中,它們不僅更為集中地展現了中國現代人真實的生存狀況,而且張揚了他們不甘平庸,擺脫生存困境、走向超越的精神追求,與當今學生的在世生存與未來發展有著更為密切、內在的聯系,更容易與學生達成共鳴。尤為重要的是,對作家作品的分析,要跳出社會學、文藝學的局限而以更為廣闊的視野,更為深入的層面,更為嶄新的角度,以生存論哲學切入,開掘其中豐富而深邃的“生存”論意義與內涵。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生存論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有著重要的借鑒與指導意義,以生存論為理據重新調整現當代文學教學的精神、路向與思路,不啻為一條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張傳敏.中國現當代文學教育教學研究現狀[J].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3):190.
[2]楊洪承.閱讀與闡釋:現當代文學課程教學理念的反省[J].海南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78.
[3]艾里克·勒梅.海德格爾入門[M].上海:東方出版社,1988,43.
[4][5][14]高偉.回歸生存本體的教育[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6,(1):14.
[6][7][8][10][11]譚大友.生存智慧的當代闡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111、112.
[9] R.D.萊恩.分裂的自我[M].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6.
[12]高偉.教育:面向可能的存在[J]. 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4,(5):13.
[13]艾小平等.“生存論”轉向與當代教育研究范式變革[J].煤炭高等教育,2007,(4):20.
[14]陳國恩.近年來武漢大學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4):278.
隋愛國,男,安徽財經大學文藝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文藝學和中國小說的古今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