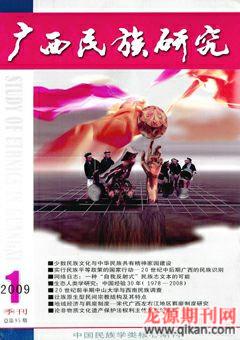明清民國粵港核心城市組合變化與廣西城鎮“無市不趨東”結構
黃 濱
【摘 要】明清時期,廣東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廣州-佛山-澳門”核心城市組合,到晚清民國時期,轉向以“香港-廣州”為核心,但“無市不趨珠”的總格局未變。在廣東商品經濟的強勁輻射下,廣西原來以桂林為總中心的城鎮中心發生了東移,逐漸演變為以桂東端城鎮梧州、戎圩為中心,并且呈現出越往東趨城鎮級別越高的等級分布體系。
【關鍵詞】明清民國;粵港;核心城市組合
【作 者】黃濱,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9)01-0157-008
The change of Guangdong-Hongkong core city combin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ll the markets tend towards Guangdong of Guangxis city and town during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rt Ⅵ of study on the radiation upon Guangxis economy from commercial economy of Guangdong and Hongkong Huang Bin
Abstract: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Guangdong had formed the core city combination “Guangzhou-Foshan-Macao” that centering on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it changed to centering on “Hong Kong-Guangzhou”,but the general pattern that all the markets tend towards Guangdong hadnt changed. Under the forceful radiation of Guangdong commodity economy,the centre of city and town of Guangxi from Guilin moved to east,developed gradually to the centering on Wuzhou and Rongxu that lies east of Guangxi,and displayed the grade distributing system that the more tend towards east the more high.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Guangdong-Hongkong core city combination;all the markets tend towards Guangdong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人們對城市發育成長規律認識和把握的需求日益增強,打破地域分隔,從經濟地理和長時段的經濟成長歷程,探究不同地域之間城市群成長的相互市場關聯,以提供給今人關于城市個性規律方面的借鑒,是經濟史研究的一個嶄新視角和嶄新課題。本人以晚清民國時期廣東、香港、廣西之間城鎮網絡的內在的等級分布和區域分工聯系為個案,探討珠江流域經濟圈西向扇面城鎮網絡機制。
民族經濟研究早在明清時代,廣東的西鄰省區廣西,民間流傳著“無東不成市”的民諺,意思是說:沒有廣東商人,廣西就成不了買賣,形成不了市場。在明清時期,廣東形成了“廣州-佛山-澳門”核心城市組合,在此軸心支配作用之下,造成了廣西城鎮“無市不趨東”等級分布體系的形成。這種格局,一直延續到近現代。到了民國時期,在20世紀30年代,千家駒、韓德章、吳半農幾位著名學者在對廣西經濟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后,驚異地發現:廣西商業經濟是受粵港支配的,廣西是廣東人的商業“殖民地”,并將其列為廣西經濟的特點之一。①稍晚,另一位經濟地理學者張先辰先生也在40年代的研究中發現:“廣西過去(指1938年湘桂鐵路通車以前——筆者注)在商業上屬于珠江系統,不啻粵港二地之附庸。與長江流域(自然含湘贛兩省——筆者注)及中原之隔膜,無殊異國。故廣西之商業以及重心,乃在于粵港接近之梧州一帶。”②廣西的整個城鎮經濟等級分布體系呈現出“無市不趨東”特點,廣西的城市總中心,并不在廣西的地理上的中心區域,而是在其東端城市梧州。進一步考察,將使我們發現,正是粵港這組在全國具有經濟總中心城市地位的總中心城鎮“廣州-佛山-澳門”、“廣州-香港”的最強大的市場組織力,分別規定著明清和民國時期廣西城鎮經濟“無市不趨東”的等級分布體系。
一、明清時期廣東“廣州-佛山-澳門”核心城市組合與廣西城鎮“無市不趨東”等級分布體系的形成
明代以前,廣東一直沒有形成市場性的城鎮經濟中心。廣東當時商品產出稀有,珠江三角洲地區商品經濟尚未發展起來。整個廣東,區域經濟的發展格局,仍然呈以中原地區北南走向輻射為軸線、以中原地區移民輸入為主動力的傳統的“北重南輕”格局(同這一時期廣西一樣)。這可從廣東全省主要地區當時人口密度分布格局上得到印證。據河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的劉佐泉著《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第63頁引用的統計,北宋時期從太宗太平興國到神宗元年的一百余年(976~1085年),廣東最靠近與中原連接孔道、接受移民最多的北部至東北部的幾個州,人戶增長幅度是最大的:梅州從1577戶增到12390戶,增長686%,南雄州從8363戶增至20339戶,增長143%,在當時,經濟的繁榮與人口的密集是成正比的。而據黃慈博輯《珠璣巷民族南遷記》(廣東省中山圖書館1957年刻印本)追朔,廣東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如番禺、順德、南海、新會等地,還是一派“煙瘴地面,土廣人稀”的荒景。這種情況下,自然商人隊伍弱小,經濟行業發育微弱,無法促成城鎮經濟的發育和它的網絡總中心的形成。
明以前,廣東早已出現城鎮,但如同一時期的廣西,基本上屬于軍政型城鎮,尚未具有顯著的市場性的組織功能。歷史發展最久、規模發展最大的廣州市,雖早已具有官統外貿的全國中心地位,但它并不是本地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產物,而是在行政指令規定下,匯總各省和海外官統外貿物資集聚發展起來的,它與廣東本區域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脫節的,尚未具備市場總中心的組織功能。其名聲還遠不如當時福建的泉州。廣州所處的珠江三角洲,巨大的商品經濟發展潛在優勢尚未充分發揮出來。所以,它一直沒有形成強大的市場引力和對廣西的商品經濟輻射力,促使最靠近廣東的廣西東端城鎮戎圩或梧州,形成廣西最大的經濟性城鎮。正因如此,明代以前,廣西東端的梧州,無論其人口規模還是經濟規模,從秦漢至宋元,一直遠遜于北部的桂林。
富庶的珠江三角洲位于廣東中部,是廣東最大的平原,面積11000平方公里,它主要由西江、北江、東江,還有綏江、潭江、增江、流溪河等帶來的淤泥在海灣內堆積復合而成。它較之地處粵東的廣東第二大平原潮汕平原的位置居中,面積大9.2倍。③至明清時期,廣東經濟重心迅速向沿海南移,珠江三角洲自然成為廣東經濟發展最核心的巨區。宋代及宋代以前,廣東經濟發展重心在粵北地區④,隨著經濟重心從粵北向珠三角南移,廣東的市場性城鎮經濟總中心終于在商品生產、商人隊伍組成和行業發育最為集中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形成,并以廣州(附澳門)—佛山為二元市場中心。⑤佛山,地處珠江三角洲地區中內貿經濟的最佳地理點上,它“控羊城之上游”,可將內貿經濟與廣州的外貿經濟聯結互托,又“當西、北江之沖要”⑥,能最便當地將珠江三角洲商品運銷全省各地,也能最便當地將各地商品吸納市中。加之自明代起,佛山日益成為民間用量最大的商品之一——鐵器用品的生產中心。因此,它從明初時仍然名不見經傳,沒什么經濟地位的農業性村落⑦很快發展成為最能吸引和聚集三角洲商人因而規模最巨的市場聚落。據佛山史專家羅一星先生考證,嘉慶道光年間,佛山已成“周遭三十四里”,人口二三十萬的繁華都會。佛山與京師、蘇州、漢口并稱明清“天下四聚”之一。⑧廣州,則地處珠江三角洲外貿經濟的最佳區位上。它內倚內貿巨鎮佛山,外扼珠江出海口,歷為省城和官府外貿巨埠,有很高程度的市場聚落基礎。隨著商品經濟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迅速發展,它自然也最能吸引和聚集珠江三角洲商人,發展成為規模最大、以外貿為主兼有內貿功能的市場聚落即經濟性城市。廣州與佛山構成的首先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市場二元中心,它們所集散的商品主要為珠江三角洲地區服務,構成它們的主體商幫,主要就是珠江三角洲商人。有人估計,嘉慶年間(1796~1820年),省會(廣州——筆者注)、佛山、石灣三鎮的客商中,“順德人居其三,新會人居其二,番禺及各縣各府、外省之人居其二,南海人居其二”⑨。廣州和佛山,實為珠江三角洲商人的大本營和派發珠商分往營造廣東各城鎮市場聚落點的總指揮部,從而也成為明清時期廣東全省范圍的城鎮經濟二元式總中心城市。依托珠江三角洲地區,廣州與佛山在本省內還造成了以自身為中心的全省城鎮環繞式分層的等級分布體系。⑩
尤其特別論及的是廣州南去約百公里、實為廣州重要外貿外港的澳門,其在省、佛二元中心運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澳門半島原稱壕鏡澳,為當時我國廣東香山縣地,位于珠江和西江三角洲的南端,原始面積為2.78平方公里,明中葉直至1840年6月,為我國國家主權仍充分行使之下,主要與廣州進行貿易的葡萄牙等國商人在中國形成的居留地。由于它是中西方直接交流的港口,又依托著富庶的西江、珠江三角洲,明清時期曾為具有中外貿易中心地位的著名的國際性港市。以它為樞紐,形成了葡萄牙——印度——中國——日本——菲律賓——墨西哥——秘魯、澳門——大小巽他群島等各條貿易航線。佛山、廣州二元中心所集匯的貨物,大宗是經過澳門出口的。史稱澳門地方貨港“均由省鎮、佛山各處市鎮轉運到澳售賣”,[11]而運銷海外的,大量從海外換回的白銀,許多是從澳門吸入的。據不完全統計,在1637年以前,經菲律賓輸入澳門的白銀就達1400多萬兩,約相當于從永樂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中國官營銀礦總產量的2.1倍,萬歷年間明政府國庫歲入的3.8倍。來自日本的白銀為數更多,在1636年一年中就達235萬兩,總數可能有1億兩左右。[12]據可靠推算,盛產白銀的日本此時所生產的白銀有近一半經過澳門輸入了中國。此外,葡萄牙、印度也大量運來白銀經澳門輸入中國。[13]澳門的外貿繁榮又強勁地壯大著省—佛二元中心在嶺南地區乃至全國的經濟中心城市的輻射功能影響。廣東省以上的區域經濟格局,我們可稱之為“無市不趨珠”(“珠”指珠江三角洲。下同——筆者注)。
廣東的西江水系地域以及由西江延伸貫透的廣西大部分地區,一并構成了粵港“無市不趨珠”環圈式城鎮等級分布體系的西向扇面。由于廣東尤其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在當時具有全國經濟發展最高梯度的地位,廣東省是商品經濟輻射入桂的主要省區,以廣州和佛山(簡稱省佛——筆者注)為中心的城鎮網絡,必然通過粵商拓展向廣西全域推進,此情勢之下,主賴粵商營造起來的廣西城鎮經濟必然始終保持著對廣州—佛山二元總城市中心的總向心力,始終以省—佛為終極軸心,并根據自身各個城鎮點與省—佛距離的近與遠,經濟聯系的強與弱,為省—佛服務功能的大與小,排布自身總體的等級分布體系——上列諸項越近、越強、越大,粵商聚居的梯度水平以及城鎮的聚落功能水平就越高,等級就越高,反之亦然。而珠三角和省—佛等軸心對廣西而言總是處于東向,這當然鑄成了廣西以東端城市為總中心,總體等級分布呈“無市不趨東”,越往東趨城鎮級別越高的體系結構。筆者曾對明清時期廣西此說有過專論:明清時期廣西城鎮經濟體系等級分布具體就是如此,桂東端的梧州及附近戎圩鎮為最大經濟總中心城鎮和圩市;然后由東而西,廣西的城鎮和圩市的等級規模不斷遞減而去。[14]
這樣,明清時期,廣西原先居北(以桂林為總中心)的城鎮中心,在廣東商品經濟省—佛軸心的強勁輻射下,發生東移。廣西城鎮經濟分布體系發生東傾,初步演變為以桂東端城鎮梧州、戎圩為中心的“無市不趨東”結構。這就為晚清民國時期廣東穗(廣州)—港(香港)二元式總城市中心地位規定著粵商對廣西城鎮經濟分布的“無市不趨東”結構的繼續維系奠定了歷史基礎。
二、局部微調而總局未變——晚清民國粵港地區廣州—香港核心城市組合地位與廣西城鎮“無市不趨東”等級分布體系
1.二元總中心城市組合的變化:從廣州—佛山到香港—廣州
自鴉片戰爭以后,以香港的崛起為突出標志,廣東的二元總中心城市的組合發生了重大變化。香港在1842年被英國割占、被宣布為無稅自由港以后,迅速崛起,在大約十數年間,一躍為廣東乃至全國經濟規模最大的貿易港市,加入了二元總中心城市的組合之中,并在這一新組合中成為位序高于廣州的首位城市。
從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上半葉,香港還成為遠東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市,形成了以下多條相對固定的全球性的國際國內航線。國際航線西向有:(1)英國至香港線。由英國的利物浦南行入直布羅陀海峽,經地中海,至塞浦路斯島,經塞德港入蘇伊士運河(1869年3月11日通航,使歐洲船只不必繞過好望角),經亞丁出紅海,經印度洋至印度加爾各答,過馬六甲海峽,抵新加坡,入南太平洋而至中國的香港,此為亞歐往來的主要航道。(2)法國至香港線:馬賽—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印度洋—越南西貢—中國香港。(3)德國至香港線:漢堡—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印度洋—中國香港。(4)荷蘭至香港線:鹿特丹—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印度洋—中國香港。東向有:(1)香港至北美線:中國香港—上海—日本或美國檀香山—加拿大溫哥華。(2)美國至香港線:舊金山—檀香山—中國香港。(3)日本至香港線:日本—上海—香港。其他方向的還有諸多航線:從香港至澳洲新金山、紐西蘭;至菲律賓馬尼拉;至越南西貢,泰國曼谷,緬甸仰光;至新加坡和印度加爾各答;至印度尼西亞和波羅洲。
國內沿海航線更是密布如織:香港至臺灣,至上海、青島、天津、大連等;至汕頭、廈門、福州等;至湛江、北海等。[15]由于香港較廣州更為前突的港口位置和更為寬松的貿易自由度,“各國商船亦將香港視作中國領海的第一中心港,先將貨物運至香港,然后再分別運往中國各埠(包括廣州——筆者注)銷售”[16]。這勢必分奪原屬廣州的最大宗的貨流,廣州雖然仍保持著對全省的市場控馭的總經濟中心地位,但在雙元組合中,已降為第二位。據記述,1872年時,廣州銷往全省的洋貨主要是由有“廣東省的保險倉庫”之稱的香港供應。[17]而廣州匯集起來的全省出口土貨,也多由香港中轉。如1914~1918年的四年間,廣州與港澳(主要是香港)之間的航行進出旅客,共6848250人次,占廣州同期與外地各口岸之間航行進出旅客共7175889人次的95%,這也可理解為廣州與外地客商往來中與香港最為大量、頻繁,占絕大多數比重。[18]因此,香港顯然形成了對廣州的控馭,構成了雙元總中心組合中的第一軸心。至1894年時,香港在廣東口岸城市群中的首位度已大得驚人。據統計,香港該年僅與中國內地的貿易總額為13321.79萬海關兩。[19]而該年廣州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為1951.96萬海關兩[20],僅為香港對國內貿易額的22%。即使當時廣東的6個口岸(廣州、汕頭、九龍、拱北、瓊州、北海)相合,當年的進出口總值也不過8731.17萬海關兩,僅占香港一埠對內地貿易一項總值的66%。[21]
佛山已退出了二元總中心位置,它原先的第二軸心地位,則由被香港取代首位軸心地位的廣州來頂替。港—穗二元中心運行機制類似于明清時期的省—佛二元中心,即聯體運行,內外貿易分工——廣州主要擔當起以往佛山內貿中心城市的任務,而香港則專門承擔著以往廣州的外貿中心城市的職能。誠如陳明銓先生在比較近代穗港情形以后指出的:“如果說那時的香港是近代中國華南產品的‘外貿部,那末廣州就起著這些出口產品‘采購收集作用和進出口產品的‘分配傳播作用。”[22]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與上述局變相應,一直作為廣州外貿外港的葡萄牙占據的澳門也隨廣州地位的下降和香港的崛起,失去了重要國際商埠和外商在華主要居地的地位,經濟一落千丈,商業多向香港轉移。[23]這也是近代廣東二元中心城市組合變異的一個側面的表現。
2.“無市不趨珠”:總格局未變
近代中心城市組合的變化,卻始終沒有改變廣東城鎮經濟總體上的“無市不趨珠”等級分布結構。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