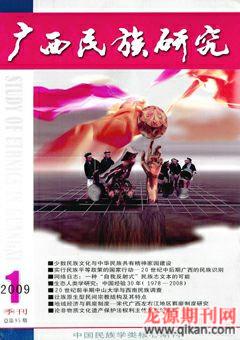黑衣壯:“我”的表述與建構
呂俊彪
一、問題的提出
從某種意義上講,“黑衣壯”已成為繼“劉三姐”之后壯族“傳統文化”最為重要的標識之一。不過,盡管被賦予“原始”、“原生態”、“古老而神秘”、壯族文化的“活化石”等諸多浪漫想象,享受著某種意義上的“詩意的人生”,并實現著所謂的“審美化生存”①,但“黑衣壯”作為一種大眾化的文化符號的出現,其實是一件相當晚近的事。1999年,在廣西南寧市舉辦的首屆“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上,青年歌手黃春艷以一首動聽的壯語歌曲《壯鄉美》讓世人見識了黑衣壯人獨特的服飾和歌聲。此后數年間,經過地方政府的精心包裝和媒體化運作,“黑衣壯”迅速成為一個頗具競爭力的地方性文化品牌,并在國內娛樂圈掀起了一股“黑衣壯”文化熱潮。②身著黑色的節日盛裝、載歌載舞的少女,逐漸成為黑衣壯人的一種文化標識。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這場黑衣壯傳統的發明運動當中,那些肚子里裝著一大套黑衣壯歷史、民間宗教和地方掌故的黑衣壯傳統文化的主要傳承者——道公,以及黑衣壯人的傳統儀式,則在相當程度上被冷落了。③由此所引發的問題似乎就是,黑衣壯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文化群體?誰是黑衣壯文化的真正代表?黑衣壯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族群?他們通過何種方式來表述、建構自己的文化身份?而更進一步的追問,則可能涉及到這樣一些問題:族群認同是如何得以實現的?它的動因和基礎又是什么?海力波的新著《道出真我——黑衣壯的人觀與認同表征》(以下簡稱《道出真我》),試圖超越以往黑衣壯研究中宏大敘事式的研究取向,以主位視角和實在的田野工作,透過廣西那坡縣“文寨”黑衣壯的人觀表述、族群認同以及當地文化表征的考察,探尋黑衣壯族群建構的歷史蹤跡和現實生活,展現黑衣壯人的生活世界。
二、黑衣壯:被想象的“我”
1999年以來,黑衣壯人以其“原生態的歌聲、原始的舞蹈、原汁原味的風土人情、延綿千年的生產生活方式”,成為一些地方媒體關注的對象。這個“以黑為美”的族群,“帶著‘不要問我從哪里來的另類魅力,向世人撩起了神秘的蓋頭。”④從某種意義上講,“古樸、善良、浪漫”的黑衣壯人,正是經由現代媒體如此這般的“宣傳”而廣為人知。不過,海力波的研究表明,盡管黑衣壯村里的姑娘小伙子們通常會在傳統干欄(房)的大門或者墻上貼上一些影視明星、流行歌星的招貼畫,當地人的家里通常也會有電視機、影碟機等,一些人家甚至可以收看衛星電視,但是對于那些生活在類似于“文寨”這樣一個2000年才有碎石路、最近幾年才通電的村子里的黑衣壯人而言,他們對于外界的覺知仍然十分有限,而他們“神秘的”的社會生活,也鮮為外地人所知。這種情狀,即使在交通、通訊條件已經變得比較便利,包括黑衣壯民歌在內的“那坡壯族民歌”入選2006年6月中國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編號Ⅱ—32)⑤,黑衣壯族群文化形象聲名日隆的今日,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事實上,世人之于黑衣壯人的“了解”,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倚賴于媒體的宣傳以及個人的想象,“神秘的”黑衣壯對于那他們而言,在較大程度上,乃是一個想象中的當代“異邦”。
成果與學者評介世代生活在中越邊境地區的崇山峻嶺之中,自稱為“敏”或者“布敏”的黑衣壯人,由于與外界的相對隔離,在服飾、婚姻制度、民間信仰、生計方式、生活習俗等方面呈現出與山下的“布央”⑥、漢人以及其他族群的某些差異。這些差異,似乎成就了黑衣壯人“原汁原味的族群習俗”,而其民風民俗也因此被一些人譽為壯族的“活化石”。⑦與此同時,由于生存環境相對惡劣、經濟發展相對滯后,黑衣壯人則被一些從結果上考察少數民族社會生活的學者,描繪成一群“孤僻、寡聞、少歡、封閉”,“缺乏創新活力,墨守成規,滿足于傳統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普遍有惰性和排他性心理、缺乏進取心的“原始”族群。⑧從某種意義上講,黑衣壯“原生態”文化的浪漫想象,以及黑衣壯“原始”、“落后”的社會生活狀況的基本定位,構成了黑衣壯這個當代“異邦”想象的重要內容。能歌善舞的、靚麗的黑衣壯少女與“孤僻、寡聞、少歡、封閉”的黑衣壯少年,似乎已成為主流媒體中的“黑衣壯文化”的典型代表。
對于黑衣壯人這種“異邦”式的當代想象,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后果。海力波認為,在浪漫主義的“原生態”的話語當中,黑衣壯人及其文化作為“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恰好可以彌補主流社會中已經缺失的美好品質;而在啟蒙主義的“原始”話語中,黑衣壯人及其文化則恰恰承載著主流社會所力圖擺脫的自身所具有的負面品性。但無論在哪一種話語之中,黑衣壯人始終是作為一種異己的“他者”而存在。⑨海氏的洞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黑衣壯的族群建構以及黑衣壯文化的再生產在當代得以順利展開的深層社會原因。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看來,所有比成員之間有著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更大,甚至于包括這種村落在內的一切共同體都是想象的。“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并非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在于他們被想象的方式。”⑩對于黑衣壯人而言,問題的關鍵似乎還不止于此。事實上,黑衣壯人如何想象自己、建構自己,甚至比他們如何被別人想象更為重要。這樣,進入黑衣壯人的生活世界,透過其社會生活的一些文化事象,探尋黑衣壯人的自我認知、自我建構過程,就顯得尤為必要。這大概是海力波寫作《道出真我》的初衷。
三、“我”的表述
長期以來,“文寨”的黑衣壯,這個“穿黑衣”、“吃玉米”的族群,由于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物質生活水平相對較低,在總體上被排斥在當地族群社會生活的主流之外,處于現代化的邊緣。1990年代以前,這些住在崇山峻嶺之中被“外面的人”污稱為“黑衣崽”的黑衣壯人,不僅因為物質生活上的相對窮困而少與山外“吃大米”的“布央”、“布農”通婚,因為水田少不種水稻而受到其他族群的歧視,更由于生存環境相對封閉、服飾穿著習慣與主流社會相異而一度成為當局“除陋習,改服飾”的主要對象,其社會地位處在當地族群“差序格局”的最底層。
《道出真我》之于那坡縣“文寨”黑衣壯人的研究,雖然也涉及到一些與當地社會生活相關的自然生態環境、歷史沿革、人口分布、生計方式、生活周期等方面的內容,但與傳統意義上的民族調查(研究)不同,海氏研究的著力點,主要放在“文寨”黑衣壯人的人觀、族群認同與文化——政治實踐之上。海氏的設想,大致是從觀念與行動兩個層面,展現黑衣壯人認識自我、建構自我的社會過程。
作為能力和行動的基礎,以及自我觀念與情感的重要表達方式,人觀(personhood)是族群認同最深層、同時也是最隱晦的表達方式之一。《道出真我》把黑衣壯的人觀作為研究的切入點,無疑是一個極好的選擇。透過對黑衣壯人在其社會生活中展現出來的宇宙觀、空間觀、時間觀的細致描述和分析,作者認為,以“好功德”作為自我核心觀念的黑衣壯人,自認為在道德上具有其他族群所不能比擬的優越性,而這種優越性來自于他們對于“道法”、“秘法”的深入理解和圓滿實踐。[11]在海力波看來,“好功德”的道德觀,對于“善好生活”的追求,對于“傳魂”的焦慮,以及“魂、名、骨”三位一體的身體想象,構成了黑衣壯人的人觀的核心內容。而借由信仰與儀式來達到“功德”上的圓滿,實現肉體與靈魂在時間、空間秩序中的順利循環,遂成為黑衣壯人自我認知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也是黑衣壯文化自信心之所在。[12]
黑衣壯族群認同的表述,與當地人傳統的人觀、社會生活狀況以及國家話語形態的變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如果說“穿黑衣”、“吃玉米”、“住山上”是“布央”等其他族群的人對黑衣壯外在的族群特征的基本認定的話,那么,“好功能”、盡孝道、“講文明禮貌”、知羞恥、懂“做人道理”等,則是“文寨”黑衣壯人的自我定位。盡管生態環境與物質生活水平的差異一直存在于黑衣壯人與“布央”人之間,但民國時期,“穿裙又穿褲”成為黑衣壯人區別于“穿褲不穿裙”的“布央”人的明顯標志,而“布央”對黑衣壯人的排斥,也甚于漢族和其他族群的人。海力波認為,這種狀況的存在,與1930年代國民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以及當地政府強迫黑衣壯人改裝有著直接關系。為了追求所謂的現代化“新生活”,躋身于“現代國民”的行列,黑衣壯人的某些族群特征在無可奈何的情狀之中被夷平了。1949年以后,通過報紙雜志、廣播電影等官方媒體的宣傳,以及升學、參軍、“提干”(提拔干部)、戶籍登記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實,統一的壯族認同逐漸成為當地“布央”、“布敏”(黑衣壯)最為重要的族群認同方式。[13]在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當中,“布央”、“布敏”之間的族群界限有逐漸模糊之勢,然而,黑衣壯人深層的族群意識并未因此而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