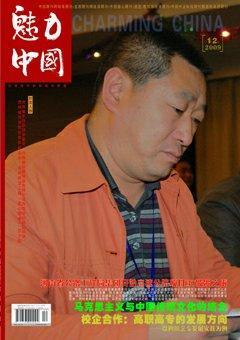私有財產權保護入憲模式之分析
董志武 陳泉鑫
中圖分類號:D9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992(2009)12-086-01
摘要:目前大部分國家憲法都將私有財產權保護條款規定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我國憲法卻將之規定在總綱部分。本文圍繞這一入憲模式展開討論,通過分析其原因以及在現今面臨的挑戰,進而得出應將以基本權利模式的構建來保護私有財產權的結論。
關鍵詞:私有財產權;憲法;公民的基本權利;總綱;五四憲法
私有財產權保護入憲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將之放置于“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部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均采取這種方式。也有少部分國家是將之放置于憲法的除“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其他章節中。我國自1954年憲法起就一直將之放在“總綱”部分。這不僅是一個憲法體例的問題,而且反映了我國對私有財產權的定位和認識。如下,本文將試著圍繞這一現象展開分析。
一、憲法意義的私有財產權概念
私有財產權首先是指一種與公有財產權相對稱的財產權類型。私有財產權是以私人的意義對財產擁有全部權利,“意味著在資源的利用上明顯地以獨立的私人使用為取向,排除了所有的公共性和共同性。” 此外,憲法層面上的私有財產權區別于民法上的私有財產權,其具有如下特征:①其權利客體指向的并不是具體化的物,而是與人的自由與尊嚴緊密相連系的一項基本權利,設定的是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界限;②其性質上屬于公權利,具有母體性、穩定性、對人的不可缺乏性、不可取代性和不可轉讓性;③其在憲法上對應的義務主體主要是國家;④憲法上權利體現為主體的某種資格。總之,憲法對私有財產權的確認是民法財產權取得的基礎和前提,使民法充分發揮保護財產權的作用。
二、我國私有財產權入憲模式之分析
1.傳統觀念之桎梏
“中國的傳統社會是靠武力為基礎形成的王權統治的社會”。在這樣的“王權支配社會”里,一切的土地和財物最終都歸君王控制和支配。中國歷史發展中并沒有發展出可以對抗公權力“私有財產權”的概念。這種傳統觀念也深深影響著新中國建立初期的立憲者,其將之與私有制簡單等同起來,不認為擁有財產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因此一直沒有將其列入“公民的基本權利”部分。
2.立法技術的不成熟
有學者發現“1954年憲法的結構接近于前蘇聯1936年憲法的結構,關于總綱、國家機構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三章的某些條文”。前蘇聯1936年憲法雖然在第十章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但卻未將私有財產權納入其中,而是在第一章“社會結構”的第十條予以規定。我國五四憲法同樣未將其納入“公民基本權利與義務”部分,而是在總綱中的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立法技術的不成熟,是導致我國五四憲法同樣未將其納入“公民基本權利與義務”部分的因素之一。
3.理論基礎的必然邏輯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制度就是對這種客觀經濟基礎的確認、調整和維護。因此作為經濟基礎的法律形式的經濟制度也必然反映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及產品的分配形式這三項基本內容,與之相應的就是所有制、財產權和分配制度三項基本經濟制度,應當在國家基本經濟制度中對財產權進行規定。此外,馬克思通過對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財產取得方式的考察發現,決定最終產品的所有權在于誰享有對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種可以支配所有權的“所有”,馬克思稱之為所有制。當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參與到財產的分配中時,決定財產所有權的就不是勞動而是所有制了。因此,對財產權的確認和保障必須以所有制的明確為前提。
三、我國私有財產權入憲模式面臨的挑戰
時代在發展使得我國私有財產權的乳腺模式面臨著隨之帶來的挑戰,主要體現在:
1.保護所有權就是保護財產權嗎?
現代財產發展的趨勢是逐漸擺脫與物的聯系,一些英美法學家將之稱為“財產權的解體”。有學者分析認為,大陸法系以所有權為中心制度在面對現在社會許多新的財產現象時,正陷入解釋力不足的困境。主要原因在于:“它賴以存在的經濟條件發生了顯著變化:第一,經濟形態由‘相對靜態到‘頻繁交易。第二,價值目標由‘歸屬到‘利用。第三,利益實現由‘自主管理到‘價值支配。”所有制意義的財產權,“首先是對財產權作為文明社會的價值支柱的矮化和削弱,在邏輯上的顛倒和概念上的偷換”,將會打擊無形財產擁有者交易的積極性,制約財產的流通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2.私有財產權之于人權、民主以及憲政的價值
首先,財產權的保障提供了獨立人格的發展所不可或缺的物理前提。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指出的:“離開了經濟事務中的自由,就絕不會存在……那種個人的和政治的自由”,“沒有經濟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沒有意義的”。其次,私人財產權直接推動了現代代議制民主的產生和發展。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必然會導致“未經人民同意不得征稅”的原則。而為了落實這一原則,當國家需要征稅的時候,就不得不召開某種形式的代表會議,以取得人民的同意,于是現代代議制度便誕生了。最后,“財產可以被視為一種政治權力。它減少公民對政府的依賴、給公民一種安全感……它以多種方式為自治創造前提條件。”從邏輯和法理上來說,要確立個人財產權,自然就必須對國家權力進行限制,否則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財產權。
四、呼喚回歸:以基本權利模式的構建保護私有財產權
中共一大黨綱到1946年《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進而到《共同綱領》,在根據地時期的憲法性文件中,私有財產權一般是與言論、出版、遷徙等基本權利相提并論的。直至54 憲法,才沒有將它作為基本權利加以規定。這種入憲模式使得私有財產權的保障,并不是因為其是個人享有的基本權利,而是國家政策產生的反射利益。這種認識已經不能滿足世界和社會將私人財產權視為一種重要人權的要求,無法彰顯財產權之于人權的價值,以及其對于現代民主和憲政的價值。
從廣度上講,社會經濟的發展尚處于較低階段,大力保護那些非所有意義上的財產來促進經濟的進一步騰飛,將那些非所有意義上的財產權也納入憲法的保護的范圍。從保護的深度上講,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財產權不應該僅僅與經濟制度有關,因而更多的應該以將私有財產權作為基本權利寫入憲法。總之,要回歸以基本權利的入憲模式來保護私有財產權,使之真正成為抵御國家暴力、維護個人自由的壁壘,成為憲政、民主、法治的強大推動力。
參考文獻:
[1] 劉建軍.《憲法上公民私有權問題思考》,載《政法論叢》.2004.5
[2] 王鍇:《中國憲法中財產權的理論基礎》,載《當代法學》.2005.1
[3] 托馬斯·C·格雷.《論財產權的解體》,高新軍譯,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4.5
[4] 馬俊駒,梅夏英.《財產權制度的歷史評析和現實思考》,載《中國社會科學》.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