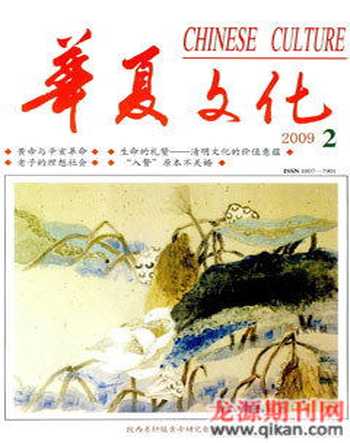生命的禮贊
趙馥潔
節日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它凝結著和展示著一個民族共同體的生存經驗和價值觀念。伽達默爾說:“節日就是共同體的經驗,就是共同體自身以其最完美的形式來表現。”(伽達默爾:《全集》,第8卷,圖賓根,1993年,第130頁)中華民族是一個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的民族,它的傳統節日蘊涵著豐富而深刻的文化內容,而其核心則是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清明節形成于唐代,它是由“清明”節氣、寒食節、上巳節三者融合而成的節日。清明節的節俗內容繁多,而貫通于其中的核心價值意蘊乃是中華民族對生命的熱愛和關懷。可以說,清明節是禮贊生命的節日。其生命價值觀的主要內涵是:
一、天人合一的生命感通意識
清明節的特色是兼有節氣與節日兩種“身份”,在二十四個節氣中,既是節氣又是節日的只有清明。清明作為節氣的名稱與此時天氣物候的特點有關。西漢時期的《淮南子·天文訓》說清明節氣:“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則清明風至。”“清明風”即清爽明凈之風。《歲時百問》則說:“萬物生長此時,皆清潔而明凈。故謂之清明。”清明節氣的氣象、氣候等自然特點是:清風和煦、春光明媚、雨水增多、嫩草茂盛、萬物復蘇、春意盎然、一派生機。
這種氣候、氣象和自然條件適宜于播種谷物,是春耕春種的大好時節。清明時節北方開始種棉花、瓜、豆、高粱,農諺說:“清明前后,點瓜種豆”、“清明后,谷雨前,又種高粱又種棉。”南方開始浸種育秧、準備養蠶。東漢崔蹇《四民月令》記載:“清明節,命蠶妾,治蠶室……”
可見,清明節氣轉化為文化節日是農業生產需要,是農業文明的產物。農業文明是人的活動與自然節令相適應的文明,它決定了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思維方式形成以后,又支配著人們的文化活動方式。包括節日的建立和節日的習俗。清明節就是中華民族天人合一思維方式在節日文化上的典型體現,它集中體現了自然生命與人類生存在生機勃發、生命涌動的春天相感應、相融通的特征。“萬物生長”乃是清明作為自然節氣與作為人文節日的相聯結的樞紐,由此而形成的自然與人的生命感通意識正是清明節的文化價值內涵的基礎。
二、寒食禁火的生命關懷意識
如果說清明節氣是清明節日的自然、生產來源的話,寒食節則是清明節的重要文化節日來源。寒食節在農歷三月,清明之前一兩天,其節俗為禁火、吃冷食。
關于寒食節禁火習俗的形成,主要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認為禁火之俗是早在周代已經形成的慣制,其來源有二說:一種歸之于上古以來特定的民間信仰。古人將周天恒星分為二十八宿,東方青龍宮的角、亢二星為“龍星”,在五行中居于木位。先秦時期,人們認為春季龍星現于東方,容易引起大火,所以在三月龍星初現之時,應該禁火。禁火之俗周代已有。禁火期間不能生火做飯,須得事先準備好食物。這種不能加熱的冷食就是“寒食”。一是認為寒食禁火源于古人鉆木取火和換取新火的制度。上古時期,人們鉆木取火,季節不同,所用木材也不同,換季時就要改火。而每次改火都要換取新火。當新火未到之時,須要禁止人們生火。后來在這一時節禁火成為習俗流傳下來。
第二種是民間廣為流傳的說法,起源于人們對著名忠臣義士介子推的紀念和祭奠。介子推是春秋時期跟隨晉公子重耳流亡的一個大臣,曾割自己腿上的肉為晉公子充饑。后者做國君(即晉文公)后要封賞介子推。介子推卻帶老母到綿山隱居,不受封賞。晉文公為逼介子推出山,就放火燒山,結果介子推被燒死在山中。晉文公便把燒山的這一天定為介子推的祭日,這一天禁火。這種紀念介子推的說法在漢代以后,傳播漸盛,在寒食節的形成和傳承過程中影響越來越大。唐人盧象《寒食》詩云:“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為一人。”
值得深思的是,寒食節無論是為防火災而禁火,還是為紀念賢士(介子推)而禁火,兩種相異的說法所包含的價值觀都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和關懷。
三、掃墓祭祖的生命承傳意識
中國古代祭祖風俗由來已久。寒食節以掃墓形式祭祖起于何時,尚未見到明確的記載。《孟子·梁惠王》有齊人郊外乞墓祭者祭馀的故事,說明戰國時就有上墳祭祖之俗。寒食上墳祭祖也可能與紀念介子推有關。北宋詩人黃庭堅的清明詩云:“人乞祭馀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公侯。”將齊人“乞祭馀驕妾婦”與介子推“甘焚死不公侯”并列,隱含著寒食清明節掃墓與紀念介子推有內在聯系的史影。
掃墓俗稱上墳,是祭祀死者的一種活動。按照舊的習俗,掃墓時,人們要攜帶酒食果品、紙錢等物品到墓地,將食物供祭在親人墓前,將紙錢壓在墳上或掛在樹上,并為墳墓培上新土,折幾枝嫩綠的新枝插在墳上,然后叩頭行禮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
掃墓是對祖先的懷念和感恩,也是對祖德的追憶和弘揚,而這種對祖先、祖德的紀念和弘揚是通過世世代代生命的延續和承傳才可能實現的。因此,從生命哲學的深層言之,清明節的掃墓祭祀活動表現的是中華民族對延續生命和承傳德業的美好愿望和價值追求。
四、踏青春游的生命歡樂意識
清明節整合的另一古代節日是上巳節。上巳節形成于春秋末期,開始日期在農歷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晉以后改為三月三日。從先秦到漢代,上巳節的習俗活動主要有三種:一是“祓楔”,到水邊舉行祭祀并在水中洗浴,以祓除過去一年中的污穢,祈求健康;二是招魂,在野外或水邊招喚親人亡魂,也召喚自己的魂魄蘇醒、回歸;三是春嬉,青年男女到野外踏青嬉戲,并自由擇偶或交合。《詩經·鄭風·溱洧》就描寫了青年男女春游示愛的場景。至春秋時期這種風俗仍很普遍。與男女春嬉相關者,民間還有“臨水浮卵”、“水上浮棗”之俗,將雞蛋或紅棗浮于水上任其漂流,撿得者可食,象征生育、求子之義。
魏晉以后,水中沐浴、招魂續魄之俗逐漸消失,臨水祓除轉為臨水酒會。與會者坐于溪流兩邊,將盛酒之杯浮于水之上漂流,漂至誰跟前,誰就飲酒賦詩,稱為“曲水流觴”。王羲之著名的《蘭亭序》寫的就是上巳節“流觴曲水”、“暢敘幽情”的文人雅集。由于上已節時間與清明鄰近,又都是在郊外的活動,至唐時,上巳節的踏青飲宴與清明掃墓后的春游娛樂后來逐漸合而為一,清明節逐漸成為一個融合了寒食節與上巳節習俗的重要民俗節日。
清明節從上巳節整合來的主要節日活動就是踏青春游,盡管隨著社會生活和文化習俗的演變,以及各民族、各地區文化特征的差異,其具體形式多種多樣,如蕩秋千、放風箏、斗百草、蹴鞠、斗雞、拔河等。這種踏青春游節俗的價值內涵是什么呢?概而言之,就是對生命的熱愛,為生命而歡樂。既包括對自然界生命的熱愛和歡樂,也包括對人的生命的熱愛和歡樂。清明節踏青游春蘊涵著生命
歡樂意識。
五、插柳植樹的生命培育意識
清明節還有插柳、戴柳、贈柳、植樹的風俗。插柳、戴柳、贈柳風俗起于何時、何因,尚須考證。其來源、含義為何,也有種種說法。有說插柳是為了紀念“教民稼穡”的農事祖師神農氏;有說插柳是用以預報天氣,古諺有“柳條青,雨蒙蒙;柳條干,晴了天”;有說戴柳條是為了留住青春,民諺有“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有說插柳、戴柳是為了辟邪、卻鬼。柳為“鬼怖木”,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說:“取柳枝著戶上,百鬼不入家。”佛教中的觀世音即以柳枝沾水濟度眾生;有說折柳贈人兼有挽留與祝愿雙重含意。因柳與“留”同音,且柳條發綠于春意萌動之際,象征“春常在”,故折柳以贈別。《詩經·小雅·采薇》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詩,李白有“年年柳色,灞陵傷別”之詞。李白還有《春夜洛城聞笛》詩云:“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清明插柳、戴柳、贈柳風俗的共同文化價值基因,就是對青春生命的關愛情感和對新生生命的培育情懷。因為楊柳有旺盛、強大的生命力,它容易栽植,易于成活。俗諺說;“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清明節值柳條發芽時節,綠條婆娑,春意盎然。于是,楊柳就成了美麗春天的標志,青春生命的象征,生命萌生的符號。楊柳象征青春生命的頑強,故插柳戴柳可以辟邪、祛鬼;楊柳象征青春生命的美好,故戴柳可以保持青春;楊柳還象征生命的隨處萌發和欣欣向榮,故贈柳可用以向離別的親人表達隨地生根發芽和“青春常在”的祝愿。由于柳樹有多方面的象征意義,于是古人借插柳戴柳贈柳以寄情便是情理中之事了。
與插柳風俗相聯系,古代還有在清明時節植樹的習慣。植樹習俗由來已久,史料記載,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西周,國家就設立了“林衡”、“山虞”等官職,掌管丈量種植、護理林木等事務。當時“列樹以表道”,說明已開始種植道樹。為了動員人們植樹,甚至作出“不樹者,無槨”(意思是說不種樹的人死后不許槨葬)的規定。中國古人重植樹,但并無植樹節,也沒有規定什么季節植樹,但從植物、樹木生長的規律和人們的習慣看,春季清明節前后無疑是植樹的最佳時節。清明前后,春陽照臨,春雨飛灑,種植樹苗成活率高,成長快。農諺說“栽樹莫要過清明,種上棒槌也發青”。
插柳、植樹的節俗形式雖然不同,但其深層次的文化價值意蘊卻是相通的,它們表達的都是中華民族珍愛生命和培育生命的美好價值愿望。
總之,生命感通意識、生命關懷意識、生命承傳意識、生命歡樂意識和生命培育意識是由清明節氣、寒食節、上巳節三源合流而形成的清明節所蘊涵和體現的價值意蘊,它集中表現著中華民族對生命的熱愛、尊重和關懷。所以,從深層次的文化價值言之,可以說清明節是禮贊生命的節日,特別是禮贊青春生命的節日。通過這一禮贊生命的節日,使儒家“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祖德崇敬意識,“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先進》)的人生志趣;使道家“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柔弱者,生之徒”(《老子》第76章)的生命哲理,“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的生命情懷;尤其是《周易》“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的價值精神,得到了生動而充分地展現。繼承和弘揚清明文化的優秀價值觀念,對于培育中華民族熱愛自然、珍愛生命、承繼祖德的民族精神和構建生態文明、和諧社會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