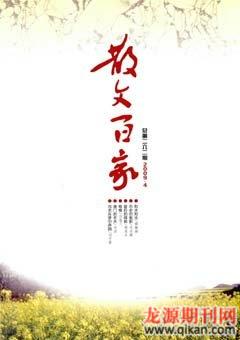思想的切片
劉五福
切片是玻片標本的一種,供光學顯微鏡或者電子顯微鏡觀察、分析動植物組織細胞的薄片。切片是分析病理的最佳、最科學的手段,是對腫瘤患者確定惡性與良性的分水嶺。
對于人類,你一旦成為切片的標本,你的生命就在生與死之間,是一個人的希望和絕望的界限,是痛苦與悲傷的深淵。
我就經歷過這種痛苦與悲傷,我手拿著玻片,在石家莊的四路公共汽車上,奔波在省四院與省二院之間。我拿著玻片標本,在四院與二院用光學顯微鏡,來證實我懷疑的診斷結果。不是我非要懷疑一家醫生給下的你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也不是我對科學不信任,那一個癌字最快地讓你聯系到的是墳墓。我在汽車上,一手攥緊扶手,一手托著玻片,兩眼含淚,面如土色,旁人都驚詫地看著我這個男人沉重的表情,滿臉流淚,人們都異樣地看著我。有誰能知道,這個小小的切片,是一個人的生命,是一個家庭的希望,是一個人的天堂和地獄呀!
生活有的時候就像做夢一樣,它讓你無意間遭遇前所未有的痛處,不得不接受許多切割的透視。另外如歷史的切片、人性的切片、道德的切片、思想的切片。我們每一個人的世界觀,每個社會分子都應該在切片的顯微鏡下透析靈魂深處的東西。
當我們把思想放在玻片上,用顯微鏡去觀察的時候,我們才發現我們的思想有那么大的差距。就像龐加萊猜想、哥德巴赫猜想一樣,盡管他們沒有任何論據支持,但猜想中的科學觀點的“發現權”永遠屬于他們。在讀《生命是什么》時,書中的科學觀點,絕大多數都有相關的論據支持,并有嚴格的論證,這就是思想的獨創性。
我想問:我們有獨創的思想嗎?
我倒覺得我們應該用切片的方式,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一次剖析。
科學研究不需要淵博的知識,稍有常識的人就可以搞科學研究,鉆進去之后就會學到許多東西,就會成為名副其實的專家,完成一篇有分量的論文,從門外漢變成內行專家。
在世界科學領域里,有如此多的例子。我們的意識形態是有問題的,關于認識世界,我們同西方是有差距的。比如:“金、木、水、火、土”我們定性為陰陽五行;而在公元前幾百年的亞里士多德則稱之為“元素”,這個元素理論主宰了化學科學幾乎兩千多年之久。這就是我們和西方的區別,一個是走上了“易經”,一個是科學的“元素”。還比如:
牛頓研究萬有引力時不是天文學家。
達爾文研究物種起源時不是生物學家。
愛因斯坦研究相對論時不是物理學家。
還有麥克斯韋、瓦特、愛迪生。愛迪生連小學都沒有上過,八歲上學,只讀了幾個月的書,就被老師斥為“低能兒”攆出了學校。可他成了舉世罕見的發明家。當初他們都是二十出頭的小伙子,甚至是外行人士,他們擁有的知識談不上淵博,可是他們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研究成果。為什么?為什么在西方總有驚人的思想出現,而我們沒有?
當我們把自己的學問,把自己的行業,自己的專業,自己的學識神化的時候,是專家和權利束縛了自由體的思想。是這些人用科學的門檻阻擋了自己思想的進化。搞科學研究最需要的是思想,只要有思想就可能在一切領域里自由馳騁。我們這個盛產“名人”的國家就是不盛產思想。只有文憑,沒有思想;只有知識,沒有思想;絕對不能發現真理,創造科學。兩年一屆的中國科技大獎發明一等獎,連續六年空缺,說明了什么?在科技隊伍中我們的封建意識,是中國科學界的悲哀。
有些以專家學者自居傲視天下的所謂學者,居高臨下,目空一切,似乎科學這個領域非專業的學者不能進入,是他們人為的設置了多個溝壑,讓專業外的人望而卻步,他們把自己神化在象牙塔尖上,高不可攀,高不可及。
古人不認為科學高不可攀,遙不可及,事實也正是這樣。
在這里我給大家講一個實例:大約在十幾年前,我們幾個同事在一次工作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新的磁場理論,我們就組織人力物力自己投資開始了這個磁場研究。眾所周知磁場是磁能的一種能量,它存在于自然界。從前專家認為磁能是一個靜態能,這是一個錯誤的觀點。磁體是看不見的能量,而且是一個自體運動的能量。其實人類早就發現了這種能的存在,并把它加以應用。在磁鐵領域里,又有了新型的強磁材料釹鐵硼,自從這個新材料問世一來,有很多有志之士在研究磁能運用。在尋找磁能能源的長河中,誰也不能逾越的是能量守恒定律,還有格磁定律。也就是說磁場的N極和S極中,推力和阻力是相等的,不論過去的弱磁場,還是現在的強磁場,其相吸和相斥是對等的。在這里就得出一個結論,多極磁場不能平衡應用,平衡應用會使一個運動的磁場變為一個靜態磁場。
而我們在十幾年的試驗中,多次實踐證明了一個新的磁場運動原理。總結為四點:一是平衡磁場;二是合理組合磁場;三是激活磁力線;四是屏蔽磁極。
這就是我們十幾年的心血,上百萬的投入,把家搞得一貧如洗。十幾年的時光,我們多次走訪過清華、北大,一談起磁能,教授就往永動機那兒想,就拿出守恒定律來唬我們。我們再三說明這不是什么高科技,這是新型的實用科學,沒有多么深奧。這與能量守恒定律不沖突,也不矛盾。這就是磁能的新利用,只不過是你怎樣的組合磁場。可人家就是不聽,我們超越不了的是專家、學者的封殺。學者在學者們的理論中僵化而狹義,他們并不知道科學的真理往往來源于生活,如果按常規的理論去分析問題永遠沒有新理論的產生。磁場也是一樣,常規磁場是靜態磁場,如果你用一種辦法打破了這種靜態,用反重力技術使磁場能量輸出做功,這種做功原理就是我們發明的排斥動能定理,也就是磁動機的成型理論。
這種用新型材料N45發明的磁動能,在我國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我國就有兩個范例新磁能發明能說明這個新的磁場是能為人類作出貢獻的。在內蒙古地區新建的風動發電,在大連發明試驗的“中華六號”就是永磁懸浮列車的證明。我們試驗的磁能動力,不是幻想,我堅信這一點。
在這里我還是再三說明,重新組合磁場,不是高科技,而是應用科學的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不是高不可攀的大事,我們就不敢涉足,這種理念本身就是錯誤的,狹隘的。我們不能在傳統科學的舊理論中一成不變。在這里還涉及到新的材料學科。科學有兩種途徑,一個是思想領域,一個是材料領域,這就是事物在進化中的演變。
歷史已經證明,發明創造不是科學家的專利,也不是學者的專利,也不是學院派的專利。我們引以為榮的“四大發明”都不是專家學者,為什么到了近代就變了呢?科學發明就一定需要一個冠冕堂皇的文憑嗎?文憑能搞發明創造的話,我們該是怎樣一個發達的國家,可我們不是。這就是我們的思想出了問題,我們的思想需要切片來做一個病理分析,需要在光學顯微鏡下看看我們是什么樣的基因。為什么這些有文化教養的學者,不去鼓勵這些不是專家的發明人,而是潑冷水,蔑視他們的創造熱情呢?我覺得我們應該用切片的方式,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一次透視。
我們應該有一個超現實的想象力,這個想象能使我們擺脫大部分常見的思維錯誤,能夠牽制輕浮的學者、狂妄的理論家、草率的思想家,能夠留下一個靈魂讓我們思考,別用有色眼鏡看事物。在哲學的理論里,沒有永恒,也沒有不變的真理。有人說現代的人不比古希臘人聰明,在兩千多年前他們就提出了原子論。也就是說只有人在猜想與假定后,才能在科學試驗中驗證它是否存在。常規地看問題,常規地下結論都是錯誤的。任何事物都有它潛在的某種能量,這個能量的存在只不過是你還沒有發現,可你不能輕率地給抹殺,任何事物是無限大的。在我們的面前有一種保守的鴻溝,而這個保守的敵意是一個無法越位的障礙。現在我拿中科院的一些年輕科學家曾經有過的抱怨話來做我的結束語:在我們這個年齡的時候,歐洲的海森伯們在做什么呢?他們整天沉醉在一些重大科學問題如基本粒子的構成中,從而引發了物理學革命,創立了量子力學。而我們呢?每天考慮的是柴米油鹽,上下班接送孩子,買便宜一點的菜和衣服,整天削尖了腦袋鉆營的是仕途。科學研究只不過是一個行走的空殼。
我們這樣一個文化悠久的民族,為什么不能把思想更進一步地開放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