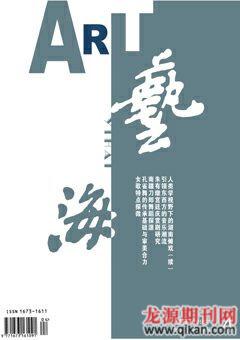柴科夫斯基第六交響曲解讀
王 瑩
論及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通常會認為是他個人全部音樂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這部作品作為作曲家音樂生涯的絕筆之作,如同“天鵝之歌”般哀傷、惋惜又彌足珍貴,另一方面是因為這部作品是柴科夫斯基用音樂書寫的淚書,是名副其實的臨終絕筆,飽含了柴科夫斯基在逆境中對無法改變的命運的無奈與嘆息,可以說是他晚年境遇的真實寫照。
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又名《悲愴》交響曲,完成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893年, “悲愴”這個別名是在作品完成之后由柴科夫斯基本人親題的。在西方浪漫主義標題音樂盛行的時代,這首《悲愴》交響曲是否理應屬于標題音樂范疇呢?
浪漫主義標題音樂,是一種相對于純音樂(即非標題音樂)而言的器樂音樂,它的特征是有一個概括性的題目,這個題目或源自于民間傳說、文學作品、繪畫作品,或是個人的親身經歷等,作曲家在統一的構思下,用音樂手段將題目表達出來。總的來說,標題音樂的音樂內容具有敘述性或描繪性等特征。相形之下,《悲愴》交響曲并非像被視為西方浪漫主義標題音樂之濫觴的柏遼茲創作的《幻想交響曲》那樣具有明確的敘述性內容,也非穆索爾斯基創作的《圖畫展覽會》那般具有明顯的描繪性特征,正如柴科夫斯基的弟弟莫德斯基透露的,這個“悲愴”的別名是作品完成之后在偶然的靈思驅動下附加的,因此并不具備標題音樂的特征。
音樂作品是否附有一個標題(或稱為別名、副標題等),并不是判定其是否屬于標題音樂的依據。例如,在柴科夫斯基與梅克夫人的通信中,第四交響曲始終被冠以情意綿綿的“我們的交響曲”,在手稿上柴科夫斯基還親筆寫下“獻給我最好的朋友”的題詞,在書信中柴科夫斯基曾向梅克夫人詳細的敘述過每個樂章描寫的內容,然而,在出版時,此曲沒有附加任何類似標題的文字和題詞。類似這樣的作品,雖然沒有本人題寫或他人追加的標題性文字,但其內容暗含著標題音樂的性質,雖不構成名副其實的標題音樂,但也可以視之為“標題式交響曲”。
因此我們可以說,柴科夫斯基的全部交響曲,特別是其中的第四、第五、第六號,雖然不具備標題音樂的明顯屬性,但都可視為潛在性“標題式交響曲”加以理解。
第四、第五交響曲大獲成功,使柴科夫斯基的盛名威震全歐,由此刺激了他創作一部偉大的交響曲的意念,第六交響曲由此誕生。整部交響曲由序奏及四個樂章構成。篇幅不長的序奏與末樂章在情緒上遙相呼應,在朦朧不清晰的和聲背景上,獨奏大管艱難地向上爬行,讓人聯想到生活的艱辛。譜例一是序奏的第一樂句,其中由前四個音符構成的動機是序奏的核心,也是第一樂章全部內容的縮影。可以說,短短18小節的序奏是整部作品的點睛之筆,讀懂了它,也便讀懂了整部《悲愴》的寓意。
譜例一:序奏的第一樂句

第一樂章B小調、4/4拍子、采用奏鳴曲式。主部主題是從容的快板,旋律由序奏中四個音符構成的動機展開而來,第一樂句由中低音弦樂器奏出,第二樂句由木管樂重復第一樂句的旋律,情緒由陰暗逐漸轉入明朗。而后,動機通過不斷的轉調模進等手法不斷發展,在層層加重的低音弦樂器低沉的伴奏下,不安與焦躁的情緒愈加明顯。相比于柴科夫斯基其它交響曲,這里的副部主題是最為著名的。副部音樂由溫和的中提琴聲部引入,旋律溫柔、抒情、情意綿綿、感人肺腑。在這里,柴科夫斯基拋開生活中一切煩惱,在充滿幻想的世界中盡情沐浴溫暖的陽光。但是現實不容逃避,生活依然要繼續。正當柴科夫斯基全情的沉浸在單簧管凄美的音樂聲中時,樂隊用一個強勁的力度奏出一個極不協和的和弦,猶如當頭一棒的把人從幻想中拉回到現實。由此音樂進入到大型的展開部。這里,呈示部與展開部連接處采用的作曲手法,把柴科夫斯基心中關于理想世紀和現實生活之間的矛盾的理解展現得淋漓盡致。
譜例二:第一樂章主部主題

按照傳統慣例,交響樂的第二樂章通常是慢板或行板,是整部作品中速度最慢、最抒情的部分,但柴科夫斯基把《悲愴》的第二樂章寫成圓舞曲風格的優雅的快板。圓舞曲作為最初來自民間作“伴舞”用的音樂體裁,以三拍子多見,但柴科夫斯基在這里獨具匠心地使用了五拍子圓舞曲,每一小節都是由前半部的兩拍和后半部的三拍構成。全曲優雅流暢,幾許淡淡憂愁全都融化在舞步的律動之中。《悲愴》的第二樂章在西方音樂史上之意義在于,柴科夫斯基把本屬于一般音樂會領域的圓舞曲帶進了交響樂的高雅殿堂,同時也豐富了交響樂的表現手段。
《悲愴》的第三樂章是非常活躍的快板,從體裁上看,是諧謔曲和進行曲的結合體。單就其第三樂章的諧謔體裁而言,是符合古典交響曲的,特別是貝多芬所構建的交響曲格局的。但是若將第三樂章置于全曲中考量,會發現這個樂章帶有明顯終曲的特性,與傳統交響曲的格局有很大差別。柴可夫斯基本人曾解釋說,整個樂章都是歡騰的,凱旋的情緒。主部主題建立在三連音音型基礎之上,有明顯的諧謔風格,弦樂器和木管樂器在連續的三連音音型中你追我趕,給人一種充滿朝氣的印象。副部主題的進行曲特征十分明顯,主題的某些因素已經提前在主部主題中登場,這種作曲技法,即副部主題在主部中先現,在西方音樂中屢見不鮮。
按照傳統,具有歡騰,凱旋性質的音樂應該出現在套曲的末樂章,擔當著表達結論的作用,是整個套曲中速度最快的部分。然而,柴科夫斯基早把具有這種性質的音樂提前安置在第三樂章,而在末樂章創作了一段極其憂傷的慢板音樂,徹底打破了古典交響樂的格局。柴科夫斯基并不是第一個敢于撼動古典交響曲格局的人,莫扎特在這條道路上走得更遠。他創作的第38號交響曲,沒有做任何調換,直接省略了本應該在第三樂章出現的宮廷舞"小步舞曲"樂章,將整部交響曲縮短至三個樂章,因此這部交響曲被稱為《缺小步舞曲的D大調交響曲》。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特別是浪漫樂派的作品,調換樂章的順序更是司空見慣的做法,然而,以慢板樂章作為終曲,這種布局確是屈指可數。柴科夫斯基之所以這樣布局,并非想向世人證明自己敢為天下先的膽識與魄力,而是基于真真切切的情感道白。我們知道,1890年,梅克夫人以財務困難,無法再資助柴科夫斯基為由,中斷了與柴科夫斯基長達13年的通信往來。雖然柴科夫斯基曾一再表示他希望得到的是友情與鼓勵,并非單純的金錢資助,但終將沒能將這種不尋常的關系延續。這件事情對柴科夫斯基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再加上與他關系最為融洽的妹妹的一個孩子,也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外甥不幸夭折,可謂是雪上加霜。
末樂章的性格正如柴科夫斯基自己說的那樣,“如同安魂曲一般”。聆聽整個樂章之后,會讓人覺得作曲家的一切精力都已經耗盡了,再也沒有力量去爭論什么,更不要說斗爭了,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死亡。聲部逐漸的消退,力度越來越弱,無奈地結束了全曲,也即將結束了作曲家的生命。
柴科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燃燒著這位憂郁的作曲家生命中最后的余暉。有人評價柴科夫斯基是俄羅斯民族之魂,更高的評價是,他的音樂已經超越了國界的藩籬,是全人類音樂寶庫中最珍貴的遺產。
(作者單位:湛江師范學院音樂學院)
責任編輯:李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