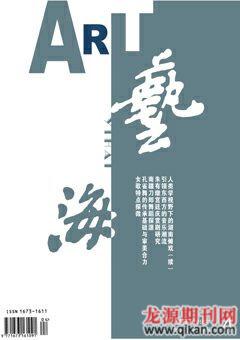唐代佛教雕塑的人物造型
馬銀芳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要在中國社會傳播發展,必須取得統治者的支持,也要能為老百姓接受,于是就有了佛教與社會交流和適應的問題。 佛教造像既是宗教的宣傳品,也是帝王權貴的意念所在。 它通過雕刻家之手把踺陀羅和摩揭陀兩個地方的造像藝術中國化,雖然這些造像的宗教氣氛非常濃郁,但其造型基礎無論如何也脫離不了現實的人,寫實的因素畢竟處于主導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社會現實的一種藝術概括,是一個封建王朝的本質與功能的形象化的表現。
1、唐代塑像人物造型
唐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加二力士的七身一鋪或九身一鋪的組合,塑像風格一改北朝時期的“秀骨清象”,面部健康豐滿,精神煥發,衣褶流暢,體態神情各不相同。
唐代雕塑最引人注目的是兩身大佛像的出現,最足以體現“國力昌盛”的大唐精神。一為武則天延載二年(公元695)完成的北大像,高33米,一為開元年間的南大像,高26米,均為“善跏座”的彌勒佛像,豐腴的面部,莊靜的神態,高大雄健的體魄,基本上保持了盛唐的原貌。
唐代的天王、力士像多是精力飽滿,身軀雄健的赳赳武夫,龍門322窟的域式天王像、194窟的力士像,外表和性格都表現出不同的特點。菩薩的形象更為豐富,天龍山205窟菩薩,雖肢體已殘,但從自然傾斜的姿態,仍顯示出一種柔姿綽態。龍門45號窟盛唐菩薩是尊極精美的杰作,她優雅地站立著,頭部斜傾微仰,身體作“S”三道彎式,鳳眼半閉,唇角帶著微笑,左臂高舉,右下垂,衣褶精細流利。這些女性化菩薩,曲眉豐頰,肢體肥胖,反映唐代“尚腴”的審美風尚。菩薩的女性化,迎合了唐代世俗化的傾向。唐代佛教雕塑人物中世俗化傾向便是較之歷代雕塑最大的不同。這種文化和藝術理想上的不同直接反映在藝術造型上。
除菩薩之外,還有僧尼造像。其形態比較雄偉,不像菩薩端秀柔弱,其程式化傾向的程度比佛像少,不如佛像那樣受西方影響,而與實際形體比較接近,面容和衣褶都很寫實。唐代佛教雕塑較之前代技法上面更加成熟,人物動作更加自如,較之前代,在造型上更強調精神,當然有主觀的人性精神,也有佛性精神上的升華。在雕塑線條的運用上,也比前代更細致入微,擺脫了粗獷古拙,而形成了集樸拙、秀靈、穩重、人性世俗為一體的唐代佛教雕塑造型特點。不再為造像而造像,走上了更加廣闊、靈動的藝術空間。
2、典型形象的對比——奉先寺
龍門佛教造像,就整體而論,不作為各雕塑家的作品來看,也沒有什么特殊的杰作,雖然刻工技法上有優劣之別,然而作品風格上大體相同,可認為是一派或一群刻匠的集體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大多應統治階級要求所作。另外,像主極多,從王公至平民,都認為造像是超度的捷徑,而爭相造像。其中的作品,大多作于高宗及武后初年,這一時期的作品,在美術的優劣上基本一致。造像身材肥碩,頭大而有力,筆法豪壯,同時又寓柔秀于強大之中,衣褶流利自然,收發自如,均能表現造像的神韻。協侍菩薩相當普及,其身材比較窈窕,有女性特征傾向。
本尊羅漢、菩薩、神王、 金剛等想象追求創造理想化的各種不同性格及氣質,這些類型雖然是唐代雕塑中常見的,如菩薩的華麗端莊而又矜持的表情,神王的碩壯有力而威武持重,金剛則全身肌肉突起,使非常暴躁強橫的神情,然而用如此巨大的尺度和體積加以雕造足以成為新的創舉。格外應該著重指出的是盧舍那大佛形象的創造。
盧舍那大佛面容莊嚴典雅,表情溫和親切,是一富于同情而又睿智明朗的理想性格。他的右手掌心向前舉在胸前,五指自然微曲,表現出內心的寧靜而又堅定,在這一形象中表現了唐代藝術家面向著充滿斗爭與變化的廣闊的生活景象時的偉大的開闊的胸懷,藝術家對于這一形象進行了自己的解釋和貫注了自己的情感。盧舍那大佛更具有完全中國化的面型和風格,無論就形式或內容上看,盧舍那大佛的面型的創造都是中國雕塑藝術史上偉大的典型之一。從盧舍那大佛的這一組佛像人物中我們可以看出,唐代佛教雕塑對社會現實的喻義性表達比前代更進了一步。在各佛像的身份、地位、神情表達上也更注重對比。盧舍那大佛群像除了集唐代佛教雕塑造型和文化之大成外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一個藝術的真諦即藝術來源于生活。
奉先寺諸像給人以深刻印象的還有神王腳下的小鬼。它承擔起神王巨大軀體的重量,它的頭、胸、臂、腹等部的筋肉以夸張地表現,因而出現小鬼無所畏懼的壓不倒的力量。在這一形象的創造中,雖然表現為踏在足下的,然而作為勇敢的對抗的力量得到贊揚。
奉先寺的幾個形象外表上是彼此孤立的,但是作為成組的群像,以本尊為中心,幾個形象具有內在的關聯,九個形象成為一完整的構圖,手法上利用簡單的隊列排列法突出主體盧舍那佛。本尊四周的背光、頂光和胸前的一環環的衣紋圍繞在本尊的面部四周,使之成為全景的中心點。把主體的中心置于明顯的幾何中心點上,收到單純而有力的效果。從內容方面看,本尊與菩薩的和善,及神王、金剛的強壯威勢等等是同一主題的不同方面,他們之間相互結合,相互補充,這一組形象反映了對于盛唐時代的封建統治體系的深刻認識,不僅歌頌了它的典雅的、華麗的、美好的一面,也揭示了它的可畏的暴力的一面。所以,盧舍那佛為中心的這一組形象是對唐代這一富有成就的偉大的時代有力的藝術概括。
3、“曹衣出水”式樣
唐代造像廣泛流行“曹衣出水樣式”,太原天龍山的唐代造像運用得特別出色。就雕刻藝術而言,天龍山的東魏、北齊作品,上承龍門余緒,極少新的突破。但唐代雕刻卻創造了人體美的典型。天龍唐雕諸像都是身體大部分裸露在外,體格勻稱豐碩,表現出筋肉的柔軟富有彈性的感覺,給人以十分艷麗的印象。其中一件白大理石雕刻的菩薩像殘軀,像高約1.5米,腰束長裙,衣薄透體,隨著肢體的轉動,衣群褶皺呈現出有規律而流暢自然的線條,表現出輕紗所特有的質地美,雖失去頭和雙臂,但無損于其體態的優美。令人想起古希臘時代那些殘缺了的雕刻名作。
甘肅炳靈寺唐代窟龕造像風格與天龍山近似,都是強調健康豐腴的美,但也有它自己的特點:面型較長,動態比較夸張,頸、腰、胯往往作明顯的轉折,雕刻刀法顯得粗獷勁利,不像天龍山、龍門諸窟的圓潤細膩。特別是51窟一佛二菩薩并災三尊像,這種配置實是一罕見例子,可以看出炳靈寺唐代造像世俗化程度有超越其它石窟之處。這三尊像雖殘,但面部造型的俊麗和軀體的合度也屬于高水平的。
唐代雕塑藝術作品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唐代雕塑藝術的成熟,表現在寫實能力提高而獲得了表現的自由,掌握了正確的人體比例及解剖知識,能處理四面觀看的圓雕,用雕塑形象反映生活的范圍更為擴大。在藝術風格上,理想的追求與手法真實 互相統一,簡單樸素的規律化的處理和生動真實的表現相統一。并且可以看出每一雕塑作品的各部分和群像的每一雕塑的統一協調和被特別強調出來的整體感。唐代的巨大雕塑的設計(無論造型或構圖)及小型雕塑品的刻劃都表現出集中了長時期的歷史經驗的唐代雕塑家的藝術才能。
(作者單位:湖南涉外經濟學院藝術設計系)
責任編輯: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