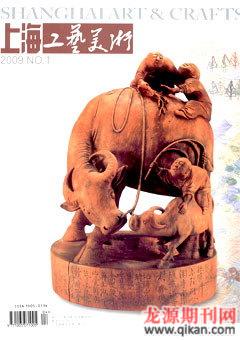春風始暖話福牛
陳燮君
牛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一種親切而溫和的動物,長達數千年的農耕社會中,它是人們親密而又善良的朋友,可與之共甘苦,同勞作,寄托著人生美好安定的向往。
我國牛的馴化,距今至少已有7000年的歷史,浙江余姚河姆渡和桐鄉羅家角二處文化遺址的水牛遺骸,證明當時中國東南濱海或沼澤地帶,野水牛已開始被馴化。根據《禮記·檀弓上》記載,當時馴牛長期的定向選擇以黃色為主,牛角也逐漸變短。商代甲骨文中有“沈牛”一詞,被釋為水牛的古稱,現陳列在美國明尼亞波里斯美術館的臥態水牛銅像,則是周代文物,而以牛首、牛角形獸面紋為裝飾的青銅器更是觸目可見。
上古時期牛最主要的用途是肉食和祭祀,由于它體量大,喂養容易,因而在當時馴化的各種家畜中最為重要,是重大祭禮中的“特牲”。在商代,牛肩胛骨是占卜用的主要材料,在流傳至今的甲骨中尤為多見,而周代祭祀時,牛羊豬三牲俱全方稱太牢,如缺少牛牲,則只能稱少牢。也正是由于牛在祭祀方面的重要作用,古代青銅器中制作最重要的彝器或制作特別精美的動物型禮器亦往往被稱作犧尊。
到了春秋戰國時,牛被用于耕田,出現了寧戚等著名相牛家。上海博物館收藏有一尊春秋晚期的溫酒器犧尊,造型寫實生動。牛鼻處設一銅環,表明此時已采用了“牽牛鼻子”馴養耕牛的方法。至漢武帝時,搜粟都尉趙過創造了輪作制——“代田法”,發明和推廣了耬車(播種器),使牛耕得到廣泛應用,取代了落后的末耜農耕,牛的地位越發重要,成為六畜之首,成了在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幫手。

牛在古代的另一主要用途是供役用。《書經》上有所謂“肇牽車牛”,《易經》上亦稱“服牛乘馬”,可見牛車是最古老的重要陸地交通工具。井田制度規定每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一頭,以備征用。相對于馬車而言,牛車的負重更大但速度較慢,最初多用于載物。但歷史上每當大戰之后,馬匹大減,牛車就應運而起,甚至有騎牛代步的。西漢初年,因國家經濟凋敝,連年戰事更令馬匹缺乏,許多將相迫不得已,只得改乘牛車,后來在馬匹大量繁衍以后,才又開始駕乘馬車了。此外,由于漢代政府規定商人不可乘坐馬車,一些大商人竟擁有成百上千輛的牛車車隊。三國以后追求舒適成為時尚,牛車因著行車的穩定性,地位大為提升。駕乘牛車更成為當時社會的流行風氣。西晉時牛車是皇帝、王公大臣、名士賢人專用的交通工具,至東晉時更成為普通士人的主要代步工具。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使原本以馬匹為尚的北方地區,也普遍地駕乘牛車。
牛在古代還被用于戰事之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戰國時齊國名將田單采用“火牛陣”突破燕軍包圍的故事。與此相聯系,“斗牛”自古就作為一種軍體活動而長期流行,我國漢朝常有雜耍斗牛表演,河南南陽出土的一塊畫象石上就有人牛激烈相斗的“角抵圖”。
由于牛在人們生產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歷代政府都對牛的使用、管理做了很多規定。為了掌管國家所有的牛在祭祀、軍用等方面的用途,周代就設有“牛人”一職,到漢朝,各級官府都設有專門養牛的機關,按牛的性別、品種、毛色和角形分成等級,隨時供祭祀盟會及食用。那時皇帝也十分尊重養牛,如有大臣因敝辭職告退,皇帝執意挽留的話,便特詔“賜其養牛”,以表誠意與期望。漢元帝時丞相匡衡,漢成帝時丞相張禹都因此受皇帝特詔“賜養牛一”,并繼續留任輔佐朝政多年。直至清朝,中國歷代法律都嚴厲禁止任意宰殺牛,規定了相應的屠宰標準和審批手續。無論是牛主(牛的所有者)還是他人,私屠亂宰牛都是犯罪行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這一制度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有足夠的耕牛以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對20世紀80年代前的中國近現代耕牛保護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漫長的歷電中,牛不僅因其在農業生產中的特殊作用而受到人民的尊重與喜愛,而且還以它堅韌不拔、開拓向前、為民造福、任勞任怨、不怕犧牲的品格受到人民的贊頌。人們把牛當成鎮妖滅邪、吉祥如意的象征。公元386年,北魏開國之主拓跋珪登代王位,就選擇在山西右玉縣牛川這塊“吉地”舉行盛大慶典。山西臨汾城在五代和明朝時曾兩次挖出鐵臥牛,當時就“以為祥”。許多易鬧水災的河邊都立有鎮水鐵牛或牛王廟,目的也是為求平安。明朝抗敵英雄于謙任河南巡撫時,就在屢遭黃河水患的開封城北鑄一頭兩米多高的鐵牛,背上鑄著“鎮御堤坊,波濤水息”字樣。
春風乍暖、萬物始新,撫古追昔、牛年話牛,愈覺充滿了美好的希望與前景。值此己丑牛年將臨之際,讓我們借用牛的堅韌不拔、開拓前進的性格和它的吉祥如意的象征,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牛勢十足,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