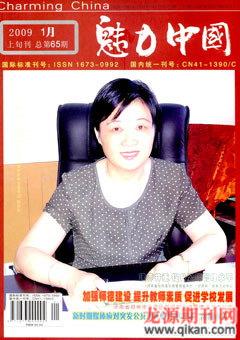司馬遷與《史記》
吳璟巍
西漢時(shí)期,中國(guó)文化史上的一部偉大的奇書(shū)問(wèn)世了。這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的《史記》是西漢時(shí)期最偉大的文化創(chuàng)造之一。
一、司馬遷生平及寫(xiě)作背景
司馬遷,字子長(zhǎng)。左馮翊夏陽(yáng)(今陜西韓城西南)人。關(guān)于司馬遷的生平有兩種說(shuō)法。一是唐人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說(shuō)他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國(guó)維《太史公行年考》、梁?jiǎn)⒊兑忸}及其讀法》等相信這一說(shuō);二是唐人司馬貞《史記索隱》,說(shuō)他生于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問(wèn)題》(《歷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贊成此說(shuō)。這是一個(gè)疑問(wèn),有爭(zhēng)論,還值得研究。程金造《關(guān)于司馬遷生卒年月四考》(“文史哲”叢刊第三輯《司馬遷與史記》)贊成前說(shuō),考證破細(xì)。一般人多同意前說(shuō)。卒年不可考。
司馬遷早年從董仲舒學(xué)《春秋》,從孔安國(guó)學(xué)《尚書(shū)》,又曾周游南北,到處考察風(fēng)俗,采集傳說(shuō)。他二十幾歲的時(shí)候,應(yīng)試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0年),大行封禪典禮,步騎十八萬(wàn),旌旗千余里。司馬談是史官,本該從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陽(yáng)不能去。司馬遷卻跟去了。回來(lái)見(jiàn)父親,父親已經(jīng)快死了。拉著他的手嗚咽著道:“我們先人從虞、夏以來(lái),世代作史官;周末棄職他去。從此我家便衰微了。我雖然恢復(fù)了世傳的職務(wù),可是不成;你看這回封禪大典,我竟不能從行,真是命該如此!再說(shuō)孔子因?yàn)檠垡?jiàn)王道缺,禮樂(lè)衰,才整理文獻(xiàn),論《詩(shī)》、《書(shū)》,作《春秋》,他的功績(jī)是不朽的。孔子到現(xiàn)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國(guó)只管爭(zhēng)戰(zhàn),史籍都散失了,這得搜求整理;漢朝一統(tǒng)天下,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也得記載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卻沒(méi)能盡職。無(wú)所論著,真是惶恐萬(wàn)分。你若能繼承先業(yè),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揚(yáng)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著我的話罷。”司馬遷聽(tīng)了父親這番遺命,低頭流淚答道:“兒子雖然不肖,定當(dāng)將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來(lái),不敢有所遺失。”司馬談便在這年死了:司馬遷這年三十六歲。父親的遺命指示了他一條偉大的路。
父親死的第三年,司馬遷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機(jī)會(huì)看到許多史籍和別的藏書(shū),便開(kāi)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時(shí)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別是漢代各地方行政報(bào)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卻忙著改歷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初歷完成,才動(dòng)手著他的書(shū)。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對(duì)匈奴的戰(zhàn)爭(zhēng)中兵敗投降,司馬遷為李陵辯護(hù),觸怒漢武帝,下獄受腐刑。腐刑又稱(chēng)富刑。是個(gè)大辱,污及先人,見(jiàn)笑親友。他灰心失望已極,只能發(fā)憤努力,在獄中專(zhuān)心致志寫(xiě)他的書(shū),希圖留個(gè)后世名。過(guò)了兩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獄,不久卻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書(shū)令,重被寵信。但他還繼續(xù)寫(xiě)他的書(shū)。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全書(shū)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wàn)六千五百字。他死后,這部書(shū)部分的流傳;到宣帝時(shí),他的外孫楊?lèi)敛艑⑷珪?shū)獻(xiàn)上朝廷去,并傳寫(xiě)公行于世。漢人稱(chēng)為《太史公書(shū)》、《太史公》、《太史公記》、《太史記》。魏、晉間才簡(jiǎn)稱(chēng)為《史記》,《史記》便成了定名。這部書(shū)流傳時(shí)頗有缺佚,經(jīng)后人補(bǔ)續(xù)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間褚少孫補(bǔ)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二、《史記》的史料來(lái)源
《史記》的史料十分豐富,其來(lái)源綜合起來(lái)可以分為四個(gè)方面:
第一個(gè)來(lái)源是書(shū)籍。凡漢代以前古書(shū),司馬遷無(wú)所不采。經(jīng)書(shū)、國(guó)語(yǔ)、國(guó)策、楚漢春秋、諸子、騷賦等都是他寫(xiě)史的重要材料來(lái)源。他在《史記》的許多篇章里都作了明確的說(shuō)明。如《六國(guó)年表》中說(shuō)“太史公讀《秦紀(jì)》至犬戎?jǐn)∮耐酢保弧段宓郾炯o(jì)》中說(shuō)“予觀《春秋》、《國(guó)語(yǔ)》”等等。這些都表明司馬遷是廣泛搜集并充分利用了當(dāng)時(shí)所能得到的書(shū)籍資料來(lái)從事著述的。
第二個(gè)來(lái)源是檔案。司馬氏世為史官,司馬談曾任太史公,后來(lái)司馬遷又繼任此職,因此,漢初檔案如詔令、記功冊(cè)等都能見(jiàn)到,并且用作寫(xiě)史的資料。這一點(diǎn),也可以在《史記》中得到證明。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說(shuō)“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傳》中說(shuō)“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xué)官之路”等等都是。
第三個(gè)來(lái)源是見(jiàn)聞。秦漢史事,對(duì)于司馬遷來(lái)說(shuō)是近代史。當(dāng)時(shí)記載有缺,因此多賴(lài)見(jiàn)聞。如《趙世家》贊中說(shuō)“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這是得于所聞的。《游俠列傳》中說(shuō)“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yǔ)不足采者”。這是得于所見(jiàn)的。《田叔列傳》中說(shuō)田叔的少子“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這是得于交游的。這些從見(jiàn)聞和交游中得來(lái)的資料,不僅增加了史料來(lái)源,而且增強(qiáng)了《史記》內(nèi)容的真實(shí)性。
第四個(gè)來(lái)源是游歷。司馬遷為了著《史記》,曾經(jīng)登涉名山大川,訪求史跡。如《河渠書(shū)》中說(shuō)。余登廬山”;《淮陰侯列傳》中說(shuō)“吾如淮陰”;《蒙恬列傳》中說(shuō)“吾適北邊……觀蒙恬所為秦筑長(zhǎng)城”等等。這些反映了他足跡所至幾乎遍及全國(guó),也說(shuō)明了他周游各地與寫(xiě)作《史記》的密切關(guān)系。
《史記》的史料來(lái)源很豐富,然而就各個(gè)歷史時(shí)期來(lái)說(shuō),史料的多少又很不平均。春秋以前間有缺略;春秋戰(zhàn)國(guó)至秦比較詳細(xì):漢建立后一百年左右的歷史。則詳盡記載,篇幅最多。也就是說(shuō),時(shí)代越近材料越多。對(duì)于上古史事,司馬遷當(dāng)時(shí)已有文獻(xiàn)不足之嘆。劉知幾在《史通·敘事》篇中稱(chēng):“觀子長(zhǎng)之?dāng)⑹乱玻灾芤淹运辉摚湮拈熉裕瑹o(wú)復(fù)體統(tǒng);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chēng)者。”這個(gè)評(píng)價(jià)是對(duì)的,但這種情況的產(chǎn)生,是因?yàn)樗抉R遷據(jù)以寫(xiě)史的資料前少后多所致,我們自然不能苛求于他。
三、對(duì)《史記》和司馬遷的評(píng)價(jià)
《史記》體例有五:十二本紀(jì),記帝王政跡,是編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記世代為主。八書(shū),記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記侯國(guó)世代存亡。七十列傳,類(lèi)記各方面人物。史家稱(chēng)為“紀(jì)傳體”,因?yàn)椤凹o(jì)傳”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斷片的雜記,便是順案年月的纂錄;自出機(jī)杼,創(chuàng)立規(guī)模,以駕馭去取各種史料的,從《史記》起始。司馬遷的確能夠貫穿經(jīng)傳,整齊百家雜語(yǔ),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齊”的必要,并知道怎樣去“整齊”:這實(shí)在是創(chuàng)作,是以述為作。他這樣將自有文化以來(lái)三千年問(wèn)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爐而治之”,卻反映著秦漢大一統(tǒng)的局勢(shì)。《春秋左氏傳》雖也可算通史,但是規(guī)模完具的通史,還得推《史記》為第一部書(shū)。班固根據(jù)他父親班彪的意見(jiàn),說(shuō)司馬遷“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shí)錄”。“直”是“簡(jiǎn)省”的意思;簡(jiǎn)省而能明確,便見(jiàn)本領(lǐng)。《史記》共一百三十篇,列傳占了全書(shū)的過(guò)半數(shù);司馬遷的史官是以人物為中心的。他最長(zhǎng)于描寫(xiě);靠了他的筆,古代許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還活現(xiàn)在紙上。
《史記》的編纂方法在當(dāng)時(shí)具有獨(dú)樹(shù)一幟的首創(chuàng)精神。司馬遷創(chuàng)造性地以本紀(jì)、表、書(shū)、世家和列傳五種不
同的體例來(lái)記載復(fù)雜的歷史事實(shí)。這種方法,便于考見(jiàn)各類(lèi)人物的活動(dòng)情況以及各類(lèi)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開(kāi)創(chuàng)了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紀(jì)傳體史書(shū)的編纂方法,成為歷代封建王朝所修“正史”的典范。
《史記》是我國(guó)古代第一部通史,據(jù)《太史公自序》中說(shuō)全書(shū)共有五十二萬(wàn)六千五百自,是古代第一部大書(shū)。也是當(dāng)時(shí)系統(tǒng)研究古史唯一的史書(shū)。它把古代歷史作了一次總結(jié),這是中國(guó)歷史上一部光輝燦爛的著作,是紀(jì)傳體史書(shū)的鼻祖,也是傳記文學(xué)的典范。魯迅先生曾譽(yù)之為“史家之絕唱,無(wú)韻之離騷”。
司馬遷是竊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時(shí)代第一個(gè)保存文獻(xiàn)的人:司馬遷是秦火以后第一個(gè)保存文獻(xiàn)的人。他們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樣。《史記自序》里記著司馬遷和上大夫壺遂討論作史的一番話。司馬遷引述他的父親稱(chēng)揚(yáng)孔子整理六經(jīng)的豐功偉業(yè),而特別著重《春秋)的著作。他們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話:“我有種種覺(jué)民救世的理想,憑空發(fā)議論,恐怕人不理會(huì);不如借歷史上現(xiàn)成的事實(shí)來(lái)表現(xiàn),可以深切著明些。”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惡、賢不肖,存亡繼絕,補(bǔ)弊起廢,作后世君臣龜鑒。
他在《報(bào)任安書(shū)》里說(shuō)他的書(shū)“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自序》里說(shuō):“罔(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jiàn)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王跡所興”,始終盛衰,便是“古今之變”,也便是“天人之際”。“天人之際”只是天道對(duì)于人事的影響:這和所謂“始終盛衰”都是陰陽(yáng)家言。陰陽(yáng)家倡“五德終始說(shuō)”,一位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勝,終始運(yùn)行,循環(huán)不息。當(dāng)運(yùn)者盛,王跡所興:運(yùn)去則衰。西漢此說(shuō)大行,與“今文經(jīng)學(xué)”合而為一。司馬遷是請(qǐng)教過(guò)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師;他也許受了董的影響。“五德終始說(shuō)”原是一種歷史哲學(xué):實(shí)際的教訓(xùn)只是讓人君順時(shí)修德。
《史記》雖然竊比《春秋》,卻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書(shū)法,只據(jù)事實(shí)錄,使善惡自見(jiàn)。書(shū)中也有議論,那不過(guò)是著者牢騷之辭,與大體是無(wú)關(guān)的。原來(lái)司馬遷自遭李陵之禍,更加努力著書(shū)。他覺(jué)得自己已經(jīng)身廢名裂,要發(fā)抒意中的郁結(jié),只有這一條通路。他在《報(bào)任安書(shū)》和《史記自序》里引了文王以下到韓非諸賢圣,都是發(fā)憤才著書(shū)的。他自己也是個(gè)發(fā)憤著書(shū)的人。天道的無(wú)常。世變的無(wú)常,引起了他的慨嘆;他悲天憫人,發(fā)為牢騷抑揚(yáng)之辭。這增加了他的書(shū)的情韻。后世論文的人推尊《史記》,一個(gè)原因便在這里。
班彪論前史得失。卻說(shuō)他“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shù)學(xué),則崇黃、老而薄五經(jīng),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論游俠,則賤守節(jié)而貴俗功”,以為“大敝傷道”;班固也說(shuō)他“是非頗謬于圣人”。其實(shí)推崇道家的是司馬談:司馬遷時(shí),儒學(xué)已成獨(dú)尊之勢(shì),他也成了一個(gè)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俠》、《貨殖》兩傳,確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時(shí)候有錢(qián)可以贖罪,他遭了李陵之禍,刑重家貧,不能自贖,所以才有“羞貧窮”的話;他在窮窘之中,交游竟沒(méi)有一個(gè)抱不平來(lái)救他的,所以才有稱(chēng)揚(yáng)游俠的話。這和《伯夷傳》里天道無(wú)常的疑問(wèn),都只是偶一借題發(fā)揮,無(wú)關(guān)全書(shū)大旨。東漢王允死看“發(fā)憤”著書(shū)一語(yǔ),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見(jiàn),便說(shuō)《史記》是“佞臣”的“謗書(shū)”,那不但誤解了《史記》,也太小看了司馬遷了。
《史記》的寶貴價(jià)值,首先體現(xiàn)于在當(dāng)時(shí)的文化基點(diǎn)上,能夠真實(shí)地、完整地描繪出社會(huì)歷史地各個(gè)層面。
司馬遷在記述政治史的同時(shí),對(duì)于經(jīng)濟(jì)史、文化史和社會(huì)生活史等,也在《史記》中進(jìn)行了生動(dòng)的記錄。與帝王將相等政治活動(dòng)家同樣。讀書(shū)的人,做買(mǎi)賣(mài)的人,算命的人-盡管在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上地位不高,他們的事跡也受到司馬遷的重視。在司馬遷筆下,游俠的俠義精神得到贊美,酷吏的殘暴行徑有所揭露,悲劇英雄項(xiàng)羽和秦始皇、漢高祖一同列入本紀(jì),農(nóng)民領(lǐng)袖陳勝和諸侯一同列入世家。司馬遷在頌揚(yáng)漢武帝的功績(jī)的同時(shí),也曾經(jīng)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長(zhǎng)生,多欲好戰(zhàn),耗費(fèi)民力的行為,在《史記·汲黯列傳》中,還責(zé)備他“內(nèi)多欲而外施仁義”。
由于堅(jiān)持了一種追求歷史真實(shí)的態(tài)度,敢于背離傳統(tǒng),富有批判精神,甚至對(duì)于當(dāng)代帝王也敢于指責(zé),《史記》曾經(jīng)被稱(chēng)為“謗書(shū)”。
司馬遷不僅是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他還是一位頗為深刻的思想者。《史記》所表現(xiàn)出的富于啟發(fā)意義的諸多思想仍然值得今天的我們不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