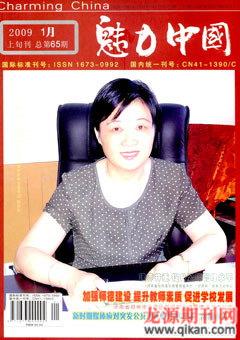法院調解的介入時機把握
文 銘
摘要:被譽為“東方經驗”的法院調解在我國的糾紛解決機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雖然關于法院調解的具體操作過程尚存在不同意見,但在構建和諧社會這個大前提下,法院調解又被賦予了新的重要意義,本文以調解雙方對審理結果的心理預期為切入點,希望從介入時機的把握方面對我國明確法院調解的具體操作有所幫助。
關鍵詞:法院調解;判決;預期;法庭辯論;成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章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根據自愿和合法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這是調解從一般的社會糾紛解決方式進入制度領域,具備法律形式的依據。從效力上來看。由于國家公權力的介入,調解結果一經確認,便具有了國家強制力。而與判決相比,它強調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合意,這使其又具備了一定的“親和力”。訴訟調解中的第三方法官游離于正式的國家法和民間法之間。顧盼左右,根據調解的進程不斷調整自己的策略,最大限度的促使當事人達成一致。
一、法院調解的價值取向
法院調解在我國有很長遠的歷史,甚至與我國古代恥訟、厭訟以及中庸之道、以和為貴等傳統觀念有一定的思想淵源。但從現代法治理念的角度來看。法院調解的主要目的還是在于節省有限的司法資源,緩和社會矛盾。如我國臺灣地區“司法院”的“民事訴訟須知”就規定:“訟則終兇,古有明訓。凡訴訟者,動輒經年累月,不但荒時廢業,且耗費金錢,縱獲勝訴,以往往得不償失。若其敗訴,所受損失更為重大。故于起訴之先,如有調解之可能。宜先行調解,即令調解不成而至起訴,在訴訟進行中,如有可以協商之機會,亦須盡力和解。”上述規定實際上表明了臺灣地區法院調解制度的立法旨意。
法院調解的價值取向是著眼于節約有限的司法資源,突出糾紛解決的效率,兼顧公平。如果法院調解的啟動時機不合理,很可能無法達成調解而必須回到判決上來,這樣反而會造成對司法資源的浪費。故對法院調解介入時機的把握,意義非凡。我們注意到,法院調解作為民訴法規定的基本原則,以前一直是貫穿于民事審判的全過程,可以在訴訟終結前任何階段適用。這是考慮到具體案件的千差萬別,從擔心貽誤調解時機的角度出發,對調解的啟動權盡量不予限制。其實,因為有當事人庭下和解制度與法院調解制度的并列存在,這種擔心顯然是多余的。而通過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絕大多數案件的調解時機是一致的,就是在經過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結束后。
二、介入時機的把握
法院的調解過程其實就是當事人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從調解成本的角度出發。任意一方訴訟當事人在參加調解的過程中都有一個可以接受的底限。在這個底限不被觸及的前提下,當事人會竭盡所能為自己爭取額外的利益。如果雙方的底限沒有產生交叉,那么達成調解的機會就會很大。否則,當事人就可能采取不調解的對策。這個底限是當事人根據審判形勢在心里逐漸形成的。這里,問題的關鍵在于,由于當事人容易導致對審判形勢做出錯誤的預期,因此往往不明確地作出了弊大于利的調解或判決選擇,由此產生的久調不決或拒不調解的成本,往往超過了采取不調解的收益。
繼續深究促使當事人做出錯誤選擇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對案件整體的信息把握不明確。他們往往太過于關注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忽視了可能敗訴的危險。借用博弈論的一個確證無疑的結論是,談判者權利愈明確,他們之間合作的可能性就愈大;而談判者的權利愈模糊,他們之間合作的可能性就愈小。即如果當事人對爭議涉及信息能夠充分掌握,其對調解與否就容易當機立斷。故調解協議往往必須在法官依法分清當事人的責任的條件下,才能有效達成。因為通過法庭調查和辯論后再由法庭主持當事人進行調解,當事人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有關判決可能產生結果的信息,他們對判決結果的估計越來越集中,從而使當事人開始認識到各自的權利和義務的位置。這種位置的明確有助于當事人對判決得出正確的預期,并通過比較預期與對方提出的條件,決定是否接受調解。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影響調解結案與判決結案選擇,主要是受到當事人對案件結果的樂觀或悲觀的不同預期。而這個不同的預期很明顯取決于當事人對信息的把握與控制。伴隨任何訴訟的提起,當事人都會對案件的狀態有一定判斷,并產生一定的預期。但是由于各方當事人考慮的角度不同,掌握的信息也不一樣,很可能根據片面的信息對形勢作出錯誤的判斷,進而產生錯誤的預期。又由于先八為主的觀念,錯誤預期的一方往往在與對方接觸中會通過尋求各種理由來強化自己的感覺和理由,同時憑借自己對法律的感覺和理解在訴訟中采取一定的行為。但是無論怎樣,之前的對法律的認識很容易讓他走上心理捷徑,從單一的角度出發來解決糾紛。而不考慮對方當事人的理由。
對信息的掌握的不對稱是導致當事人雙方產生錯誤預期的原因,錯誤的預期的又會帶來兩種結果:一是對審理結果預期的差別將使當事人無法達成調解協議,而使調解以失敗告終。二是即使基于錯誤的預期,雙方當事人之間達成了調解協議,但是不充分的信息對當事人的合意來說,可能會造成欺騙性后果,從而引起調解協議的不公。
立法者將啟動法院調解的時間規定在法庭辯論終結后的苦心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通過訴訟過程中雙方當事人的平行對話,可以降低當事人的盲目樂觀預期,使其從新認識眼前形勢。制度經濟學家證明,如果當事人雙方對判決結果的預期都是相對悲觀,即認為判決結果超過自身預期,當然他們會更愿意選擇調解。而通過庭審前后信息交換,至少可告訴當事人。持相對樂觀主義的雙方當事人,至少有一方的信息是錯誤的,從而糾正或降低當事人的相對樂觀主義預期,從而促進調解。
三、對不同聲音的回答
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釋《關于民事、經濟審判發不過是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1998)14號第19條,將調解明確設置在法庭辯論終結后。于是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樣安排不利于實現當事人的自愿調解,擔心法官的先入為主可能對調解雙方形成來自國家公權力的壓力。不可否認,我國法官的總體素質還有待提高,法院調解的過程中法官“以威壓調”的情況在某些地區法院時有發生。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法官素質和調解制度設置方面其實是兩個問題,雖然法院調解的最后適用結果可能要受到多方面的影響,但是不同的問題必須通過其自有的途徑得到解決。再完善的制度設置面對完全不稱職的適用者都是蒼白無力的,再稱職的法官面在不合理的制度面前也是無能為力的。要想完全通過完善的制度設置來彌補整個法官職業素質不高的缺陷,這種想法也是不切實際的。
或許會有人認為,通過民事訴訟訴前證據交換的過程,雙方當事人都可以比較充分的了解到對方所依據的理由。不必非得在辯論終結后才能啟動調解程序。但是我們知道,庭前的證據交換只是簡單地交換證據的一些概況,當事人之間缺乏直接的、在水平方向上的對話這一合意形成所需要的相互作用過程,相關的信息不能在雙方之間得到充分的消化與吸收。調解發生在民事訴訟程序中,而程序本身就具有為雙方當事人提供對話機會的功能。雙方當事人之間進行真正而充分的對話,才有可能表達他們對本案事實及法律問題的真實想法,當事人也需要通過反復多次的協商形成合意。另外,我們前面提到當事人容易先入為主,從自己的角度不斷尋找支持己方觀點的理由來強化自己的感覺和理由。又由于當事人雙方處在一個完全對立的立場,他們是不太可能用自己提供的信息來影響對方,改變對方的看法的。因此。由法官主持,雙方當事人全面參與的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過程對于當事人全面地掌握案件信息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還有人提出,將調解啟動置于法庭辯論結束后,會產生兩個問題。第一,在經過了民事訴訟的主要階段——審判過程后,調解已經消耗的司法資源和判決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最后結論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法院調解節約資源,控制成本的價值追求沒有能得到實現。其實我們應該注意到,調解的一調終結,不許上訴,避免了當事人因不滿一審判決而上訴或提起再審的情況。同時,調解對受到損害的社會關系的修補效果,明顯好于判決的作用。與此相對應的是,生效的調解結果由于包含了雙方當事人的合意,往往能得到自覺地執行,而面對不利判決結果,敗訴一方可能基于抵觸心理,消極地逃避執行,而來自公權力的強制執行必然又是對司法資源的浪費。
第二個問題是,在權利義務都相對明確的情況下,處于劣勢的一方自然希望通過調解多少爭取一點利益而不是坐等不利判決,但勝算較大的一方不大可能會同意調解,因為他可以從判決中看到更多的利益。首先,我們應該理清的是,上述列舉的情況,一般只會出現在那種判決屬于全是或全非的案件之中,而大多數的案件判決不會是這樣子。其次,持這種觀點的人忽略了裁判的執行成本以及如果另一方當事人選擇繼續上訴或申請再審,原審勝訴方還得繼續投入的訴訟成本。特別是考慮到我國生效裁判“執行難”的司法現狀,當事人往往也比較愿意通過調解一勞永逸地解決糾紛,免受訴累之苦。
以上分析對我國關于法院調解的介入時機規定給予理論上的支持。但是司法現狀中,關于法院調解啟動的隨意性還是屢見不鮮,這與長期以來公眾對法院調解的誤讀有關,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缺乏對調解啟動時機的不夠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