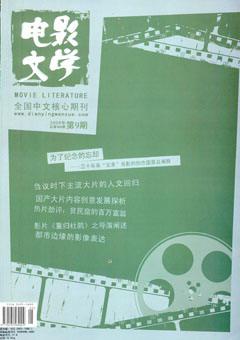解析豫劇《程嬰救孤》的舞臺藝術
王艷霞
摘要豫劇《程嬰救孤》的舞臺藝術在繼承和保留了傳統戲曲寫意性、虛擬性、程式性的古典神韻的同時,又充分發揮了現代化舞臺手段的優勢,在舞臺設計、時空轉換和表演藝術諸方面,營造了一個富有時代氣息的意象世界。
關鍵詞《程嬰救孤》;舞美設計;時空轉換;表演藝術
2003年,河南省豫劇二團推出的新編歷史劇《程嬰救孤》一經上演就獲得了空前的成功。連續獲得2004年“全國藝術節文華大獎”第一名、2006年度“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獎”榜首、2007年度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等各項殊榮,引起了觀眾的強烈反響和全國戲劇界的高度關注。《程嬰救孤》能夠成為舞臺藝術精品,不僅僅是因為其在思想闡釋方面展示出改編傳統題材的現代理念和當代思維,而且在舞臺藝術方面也顯現了創作者繼承藝術遺產而又勇于創新的時代精神。
一、舞美設計
舞臺布景的有力參與,為本劇提供了具有厚重歷史感的典型環境和調度自如的表演空間。舞臺布景兼有時間藝術和空間藝術的性質,是四維時空交錯的藝術,具有很強的技術性和對物質條件的依賴性。
中國傳統戲曲舞臺布景很少,大體是一個空空的物理空間。在演員上場之前,這個空間不表示任何地方。舞臺設計并不體現戲劇行動發生的時間、地點、歷史氛圍和文化特色,不提供行動發生發展的環境因素甚至是行動的暗示、行動意蘊的渲染等舞臺物質形象。雖然只有簡單的一桌二椅,卻可以表示故事發生的任何一個場景,演員通過無實物表演來表現一些事物的存在。《程嬰救孤》在美學原則上并未打破戲曲舞臺的虛擬性,它仍然非常鮮明地體現著景隨身變、移步換景的審美范式,隨演員的唱,念、做、打賦予同一場景以不同的審美空間。《程嬰救孤》以體現春秋文化的青銅器色彩作舞臺背景的底色,用氣勢恢弘而又深沉凝重的宮廷大門作為舞臺的主體裝置,并通過城樓的架構,實現了表演空間的分割,以城墻前兩座可移動的臺階為演員提供了豐富的動作支點。其整體設計古樸、威嚴而簡單,但此城墻和城樓卻隨著劇情的進展不斷地變換著其所指的空間:宮內、宮門、程宅、屠岸府、太平莊,都由演員的上下場和戲劇情境的轉變而各有所指。這在美學原則上與傳統戲曲是一致的。但《程嬰救孤》的布景設計既有文化積淀的歷史厚重感,又不乏鮮明的時代特色。古樸威嚴的城墻借鑒了現代話劇的寫實風格,作為一種權力的象征,營造出陰森、凝重的氣氛,帶給人凄涼、壓抑的感受。舞臺多支點的使用和多空間的分割,使得舞臺調度靈活自如,形象造型具有立體感和雕塑感。
當今的舞臺劇作為視、聽綜合體,首先是滿足于視覺,其他因素的拓展是以視覺為核心發散開來。電影理論家查希里揚在論述視覺形象時寫道:“視覺對人類具有重大意義,人的腦子接受來自眼睛的信息,平均大約30倍于另一重要器官——耳朵。我們主要是靠視覺來感知周圍世界的空間關系的。”
現代化燈光的使用為一個相對沉重的主題營造了詩的意境。《程嬰救孤》借鑒了話劇甚至電影的光影技巧,富有現代氣息和時代韻味。整個舞臺的亮度用色塊構成。序幕中,先用藍色光塊照亮舞臺,同時是屠岸賈惡狠狠的念白,形成一種肅殺的氣氛,緊接著趙家滿門慘遭屠戮,藍色光塊變成猩紅,劊子手手起刀落,全場變暗。當程嬰和公孫杵臼計議保孤時,舞臺上打的是紅光,當公孫杵臼與驚哥命喪黃泉時,一束追光打在程嬰身上,程嬰發出了悲痛欲絕、痛不欲生的呼號。第四場中郊外場景用了全劇最亮的白光,代表了清明時節的春光明媚和不知真相的孤兒的天真爛漫。第五場識圖述仇時,較暗的紅色再次籠罩了舞臺。正如導演張平所說:“運用大量的色塊加強舞臺氣氛,要有幾次極強的色彩沖擊力,用色彩外化舞臺人物細致的內心情緒變化。有時可隨演員的唱腔、動作而變化,隨舞臺情緒而變化。”。
《程嬰救孤》的服裝與化妝也與傳統戲曲存在差異。傳統戲曲服飾鮮明、造型夸張,夸張的臉譜和絢麗的傳統裝是適應高臺、廣場演出而形成的歷史遺留。但《程嬰救孤》人物臉譜淡化,魏絳和屠岸賈已經基本沒有了臉譜,只是用一紅一白作為忠與奸的區別。而人物的服裝雖不是純粹話劇式的據實設計,但也不是純粹的傳統裝了,而是在傳統裝的基礎上糅以現代以來新改良戲曲的古裝,更顯人物形象之飄逸和視覺審美之靈動。
二、時空轉換
《程嬰救孤》充分發揮了戲曲時空轉換自由的藝術特性,通過人物的上下場、唱詞和念白的直接提示等方式靈活自由地轉換時空。但它又避免了傳統戲曲過場戲過多、情節拖沓、不用暗場的不便之處,在保持整體線形發展的流暢性的同時,借鑒話劇的塊狀結構和電影蒙太奇的剪輯手法,充分發揮燈光轉場的靈活性,避免了許多過程性的敘述,強化了情節性和觀賞性,使得場面集中,結構緊湊,情節進展迅速,時空轉換靈活。
序幕交代屠岸賈對趙氏滿門斬盡殺絕,此一場景表示兩個時空,臺階上的屠岸賈宣讀圣旨,臺階下和城樓上的舞蹈表演表示血腥的屠戮場面,隨著屠岸賈發出要把公主的嬰兒斬草除根的狠話,收光暗場;嬰兒的啼哭聲從黑暗中傳來,追光下。面容憔悴的公主懷抱嬰兒訴說心頭之苦,場景已經轉到內宮;程嬰臨危受命,公主含淚托孤,燈光暗轉,程嬰忐忑走來,被韓厥攔住,場景已是宮門之外;韓厥自刎,屠岸賈大怒,校尉過場,收光;燈光再次亮起,兩側臺階已撤,公孫杵臼、程嬰計議,顯然已到程嬰家中;商議已定,二人抱頭,切光過后,屠岸賈高坐堂上,撫琴低吟,地點已轉為屠岸府中;程嬰出售孤兒,彩鳳含恨而死,再次切光,臺階移至兩側,公孫杵臼把酒臨風,場景已到太平莊上;公孫杵臼與驚哥喪命,程嬰撫尸痛苦,收光,幕外音兒歌聲起,大雪紛飛,四季輪回,程嬰須發斑白,步履蹣珊,轉眼已是十六年后t春意盎然的郊外,長大成人的孤兒躍馬馳奔,邂逅公主,再生誤會,幕外音宣告魏絳回朝,這場戲是全劇惟一的亮色;切光過后,兒歌再起,程嬰提筆作畫,場景已轉到屠岸府上程嬰書房,該到識圖述恨的時刻了,元帥府中,程嬰蒙冤受刑,真相終于大白,兵發屠岸府,大仇終得報,程嬰也最終以自己的身軀再救孤兒一命。
可以看出,《程嬰救孤》一劇在保持情節發展流暢性和劇情節奏緊湊性方面處理得恰如其分。這既得力于戲曲藝術特有的境隨情遷、時由心變的“超時空觀”,又借鑒了話劇燈光切換和電影蒙太奇的手法“別具一格地創造非現實的戲曲舞臺時間與空間”,使得世人對程嬰的唾罵、孤兒對死去英烈的質詢和程嬰對已逝親友的呼喚等心理時空的內容得以在舞臺上呈現。尤其是程嬰在大雪紛飛中由壯而老以及聲聲兒歌相伴而起的場景,不僅表示時間的流逝,而且暗示了程嬰在“風刀霜劍乎”相逼,的殘酷境地中蒙冤負屈、忍辱負重、身心受到雙重折磨的苦難生活。這是戲曲舞臺上前所未有的嶄新景觀,豐富了戲曲藝術的舞臺語匯。
三、表演藝術
《程嬰救孤》有一群好演員,他們準確到位的內心化
表演,保證了全劇的藝術品位,特別是“由豫劇表演藝術家李樹建飾演的程嬰形象,應當是當今中國劇壇上最富有光彩和最具魅力的舞臺形象。”這是專家和普通觀眾給予他們的極高評價。
傳統戲曲的表演方式具有高度的虛擬性和程式性。虛擬是為了達到“無中生有”的藝術境界,在空靈的舞臺上展示各種假定的戲劇情境,而程式則是虛擬表演的必然要求。戲諺中所說的“假戲真唱”“得意妄言”“貴在似與不似之間”就是戲曲表演虛擬性和程式性的形象表述。其實,雖說戲曲表演首先是一種程式化的表演,但真正優秀的表演必然是程式與戲劇情境、人物性格的緊密結合。《程嬰救孤》在這方面堪稱典范。主演李樹建是一個藝術觀念極為開放的藝術家,他唱的是地方戲曲,演的是老生須生,可他在把握和創造人物方面,在熟練掌握行當表演技巧的前提下,積極吸納斯坦尼體系的表演精髓,全身心地體驗角色,把角色化為自己的血肉,“在角色的生活環境中,和角色完全一樣正確地、合乎邏輯地、有順序地、像活生生的人那樣去思想、希望、企求和動作。”再滿懷激情地去創造角色,力爭達到形似與神似的完美統一。他的表演是真正的“體驗基礎上的再體現”。李樹建的表演極其老到,在繼承傳統戲曲美學神韻的前提下,不拘程式,勇于借鑒,大膽創新,形成了自成一體的獨特風格。他的表演在很多情境下已經突破了傳統戲曲的固有程式,而吸納和借鑒了話劇表演的某些特點,這使得他的表演在不失戲曲神韻的前提下更加本色自然和生活化。從登場開始,他就匠心獨運地采用一種有意壓低嗓音的氣聲念白,恰當地表達了在黑暗勢力逼迫下形成的高度壓抑感。而他聲情并茂的唱腔藝術,純然是以心歌唱,讓感情化作音符、旋律,抑揚有致地流淌,給觀眾以強烈的聽覺沖擊,扣動著引發著人們的感情共鳴。
除李樹建外,《程嬰救孤》在全劇的表演處理上也有突破傳統戲曲程式的新語匯。如傳統戲曲以虛擬為美學根基的點到為止的表演方式,在《程嬰救孤》中演化為富有藝術美感的有意味的形式。如抄斬趙家滿門在此前的戲曲舞臺上都是一言帶過,而《程嬰救孤》則在猩紅的燈光下以舞蹈的形式展示了行刑過程的慘烈。再如編導對劇中“死”的處理,構思精巧,手法新穎,讓“死”也體現出美來。韓厥為了救孤而自刎,劍放頸上而身軀不倒,象征著精神的偉岸,公孫杵臼為救孤而死,以槍刀架在空中,喻示著壯烈和崇高;彩鳳為救孤而死,手舞紅綢,視死如歸,以優美的舞姿面對邪惡,表現出大義凜然的非凡氣度。主人公程嬰之死,則化為一尊千古不朽的雕像。這些精彩獨到的展現,把“死”化作一種美的形式,又與人物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人格融匯在一起,是一種心靈與情感的外化,是一種永恒精神的張揚。這樣的表演方式既是對新時期以來某些寫意話劇(如《桑樹坪紀事》《生死場》等)的藝術借鑒,也是該劇創作者有感于時代欣賞趣味和審美需求而進行的卓有成效的舞臺嘗試。正如導演張平所言:“戲曲古裝戲若要保持藝術的青春和永久的魅力,就必須要與現代人的審美情趣緊密結合,特別是深層次的文化含量、讓觀眾回味無窮的哲理思考和雅、細、精、深的舞臺處理。”
總之,《程嬰救孤》之所以能夠成為舞臺藝術精品不是偶然的。思想內涵的豐富深刻和形象、情感的感人至深是其藝術品味的內在支撐,而美輪美奐的古典神韻和特色鮮明的時代氣息的完美交融是其舞臺魅力的外在體現。它在舞美設計,時空轉換和表演藝術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可以成為戲曲后來者可資借鑒的藝術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