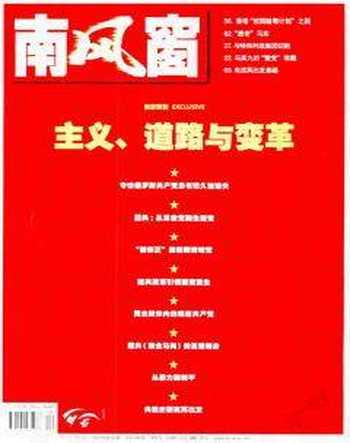亂世抉擇
劉 陽
湯姆·漢克斯主演的兩部電影《達芬奇密碼》《天使與魔鬼》,令人對梵蒂岡產生了興趣。其實,真實的歷史遠比電影驚心動魄,無須追溯太遠,即便對二戰期間梵蒂岡的角色——面對納粹這個現世魔王,面對蘇維埃這一地上天國的建設者,在云譎波詭的大國博弈中,在炮火與諜戰的間歇,教廷的亂世抉擇就一直惹得世人爭議——
當納粹肆虐之際,梵蒂岡沒有提出強烈抗議,對德國的滅猶屠殺沒有發出最嚴正的譴責,在日本轟炸珍珠港后還與其建交……這些都是人們對其不滿、失望,甚至激烈抨擊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隨著大量檔案的解密,僅以對猶太人的態度為例。人們有理由相信。時任教宗庇護十二世通過貌似中立的曖昧立場,以巨大的內心煎熬換得了行動空間,選擇少說多做甚至只做不說,直接、間接挽救了86萬猶太人的生命。
以往國內政治掛帥的“研究”,大體拷貝了前蘇聯的“成果”,將梵蒂岡放在對立面上貶損得一無是處。作為中國社科院的重大課題,學者段琦的新作《梵蒂岡的亂世抉擇(1922~1945)》卻“通過翔實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很有說服力地表明:梵蒂岡的所作所為有著雙重性”。
其實,中國在二戰前后與梵蒂岡并無直接的利益沖突。今天,蘇維埃已經解體下場,人們也該找回獨立思考的權利了。該書作為國內該領域首部系統的研究,終于表現出基本的學術誠實。
蘇聯建國后,從無神論立場出發,將宗教與酗酒、毒品視為一類,對神職人員進行宣傳丑化、征收財產,直至肉體消滅。1921年蘇聯大饑荒,梵蒂岡組織數千萬噸食品、衣物前去賑災,蘇聯報紙只字不提,反而連篇累牘報道布爾什維克救災如何有力。最終在經濟稍有好轉的時候,沒收了梵蒂岡的所有救災物資,令其兩周內離境。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說:“我們共產黨人感到必能戰勝倫敦的資本主義,但羅馬(梵蒂岡所在地)將被證明是一個更難對付的問題。”
而梵蒂岡方面,一向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區別看待,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注重改善工人階級的經濟狀況,并不企圖改造人的精神。二戰前他們之所以對納粹態度溫柔,除了與英法一樣希望以退讓換和平,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認為納粹雖壞,卻還不至于像蘇聯那樣要“把神父作為一個階級消滅掉”。
波蘭的遭遇也令梵蒂岡不能不警惕:1944年7月29日,蘇聯電臺播出波蘭共產黨呼吁華沙人民起義的聲音,7月31日,忠于波蘭流亡政府的華沙地下軍獲悉蘇軍已突破城東的德軍防線,遂決定8月1日凌晨起義。就在這時,蘇軍突然停止了進攻,電臺驟然緘默。德軍趁機集結5個師血腥鎮壓,英國要求空投物資支援,被斯大林刁難。蘇聯人眼看德軍炮火將華沙夷為平地,屠殺了60余天。耐心地等到11月之后,蘇軍才攻入華沙。借納粹之手,蘇聯大大削弱了流亡政府的支持者。1945年3月,又設下圈套邀請波蘭抵抗組織代表赴蘇談判,將這些親英美分子一網打盡。波蘭是傳統的天主教國家,梵蒂岡非常關注其命運。
聯想到德國入侵蘇聯時,曾企圖追使梵蒂岡發表支持性聲明,宣布德軍的行動是為了拯救蘇聯信仰自由的宗教戰爭。梵蒂岡拒絕了,負責談判的樞機主教直言不諱地表達了教廷的態度:“這是一個魔鬼驅趕另一個魔鬼。”
書中提到兩則錘與釘的比喻,值得拈出。其一,德國反納粹的加侖主教1941年不顧生命危險對信徒發表了著名的“鐵砧演說”:“如果你問一位鐵匠,他將告訴你,他要鍛造某物時,使其成形的不是錘子,而是靠鐵砧。鐵砧不能回擊,也不需要回擊,它需要的只是堅硬、牢固和抵抗性……它將比錘子耐用,并且會使錘子破碎。”其二。蘇聯黨內理論家盧那察爾斯基的名言:“宗教就像一顆釘子。你敲得越厲害,它就釘得越深。”
梵蒂岡與日本建交傷害了中國的感情。歷史上,梵蒂岡的對外交往原則是從不拒絕任何主動提出與其建交的國家,出發點始終是從有利于傳教考慮,認為信仰高于民族利益。作者客觀分析道:“梵蒂岡的對外政策,是天主教徒的利益先于一切,不管民族事業正確與否。”這就不免與現代民族國家的訴求產生矛盾。
梵蒂岡總是避免政治化的行為,力求以超脫的姿態做國際爭端的調節者。對于英美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梵蒂岡就公開反對,認為這會使戰敗方相信除了勝利和毀滅之外別無選擇,會使德國因絕望而拼死一搏。后來,這的確被權威人士視為盟軍的失策。
德國投降后的次日中午,教宗發表講話:“這場戰爭帶來了毆嚴重的破壞,不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今天重建世界已經成為當務之急。我們希望在等待了這么長的時間之后,能夠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看到戰俘和被扣押的公民盡快被釋放,回到他們的家鄉、親人身邊,回到和平的環境中去。”
既沒有譴責失敗者,也沒有贊頌勝利者。而是將爭端與分歧棄置一旁,敦促所有人都參與戰后重建。這就是梵蒂岡的立場。這個調調肯定有人不愛聽,但總不至于是“法西斯的同盟軍、反革命陣營的頑固派”。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研究的出發點,不是原則,而是客觀存在的歷史。原則應該服從歷史,而不是歷史服從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