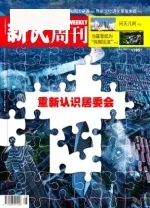不要再把老歌鑄成子彈
錢亦蕉
當年那些創作歌曲、演唱歌曲的音樂人,他們的陣營并沒有我們現在認為的分得那么清楚,不像今天我們已經人為地按上了政治烙印。
1929年,中國誕生了第一張流行音樂唱片《毛毛雨》,它的創作者是創辦“明月社”的中國流行音樂教父黎錦暉,演唱者是他的女兒黎明暉。唱片業伴隨著流行歌曲迅猛發展。

1927年,王人藝、王人美兄妹加入了“明月社”,王人藝后來成了中國第一代演奏家,他還是聶耳的小提琴老師。王人美是中國第一代流行歌手,她是“明月社”的“四大天王”之一。1934年,王人美主演蔡楚生導演的《漁光曲》并演唱主題曲,紅極一時,其中的吉他伴奏正是聶耳。
1944年,日本人將上海百代唱片廠庫房內幾千張銅質母版唱片運到日本,為了打仗造子彈,好在戰爭很快結束,還剩下一部分未進熔爐,佚散當地。無獨有偶,“文革”期間,又有一部分銅質母版唱片被當成軍需物資運往四川深山中,計劃危急之時可以做成子彈備戰,幸好最終沒有實施。
2004年,王人藝的孫子,上海音樂學院的王勇教授,重新走近這批塵封已久的老唱片,揭開祖輩的往事記憶,整理編撰《上海老歌》,歷時4年精選CD20張。2009年8月,王勇將這些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專著《上海老歌縱橫談》和簡譜版《上海老歌金曲100首》。
銅質母版差點成了子彈
《新民周刊》:一般認為上海流行音樂的源頭是1927年黎錦暉創作的《毛毛雨》,這首歌由黎明暉演唱、錄制成唱片則在1929年。為什么你編選的這套上海老歌唱片是從1931年開始的?
王勇:這個《上海老歌》圖書及CD的編輯主要是根據現有的唱片母盤來的。傳說中唱片庫里的母盤有四萬多張,確實有,但相當數量是戲曲之類的唱片,與老的流行歌曲相關的大概有七八千首。我們選擇的時候有幾個原則,第一就是要保證音質,這是首要條件。我們確實考慮過1929年出的《毛毛雨》這張唱片,但是它的母版在中唱片庫里沒有找到;本來也想過是否拿膠木唱片來補齊這首歌,但是后來我們拿到的版本音質不夠好,最終被放棄了。根據中唱片庫現有的資料考慮,我們決定從1931年開始做起。
《新民周刊》:中唱片庫里為什么有這么多老唱片?王勇:1949年前后,百代離開上海的時候,唱片的母版沒有帶走,存在倉庫里。中國唱片廠上海分公司后來接收了這些東西,還有原來“勝利”的一些唱片母版。黎錦光先生健在的時候,就把這些唱片做了個目錄。不過這些唱片是有版權的,期限50年,所以到1999年才可以重新整理出版。
“文革”的時候,有一部分銅質母版被運去四川,說萬一打仗,可以做成子彈。實際上在1944年的時候,日本人也運過幾千張銅質母版到日本,也是為了做子彈。但是只做了一小部分,戰爭就結束了,所以還剩下一部分唱片留在日本。據說這批運往日本的母版中有不少李香蘭的歌,所以這次我們整理“上海老歌”的時候,唱片庫里李香蘭的歌只找到6首,其他的母盤都已經沒有了。

《新民周刊》:中唱的片庫里,哪個歌手的唱片比較多?你們是怎么取舍的?
王勇:最多的當然是周璇,大概有一百五六十張唱片吧(一張唱片一首歌)。其實這個片庫現在經過不斷整理已經不像最早我去看的時候那么亂,現在都做了處理,把老唱片都轉成了CD,我們就在CD里面選。當然轉出來的時候沒有做任何音頻修改處理,只是原聲采出來,我們選了之后,他們再去處理制作。
我們選的時候,除了音質,還照顧到要平衡,不能一個歌手選得太多。因為要反映歷史全貌,所以也必須面面俱到。周璇是我們忍痛割愛最多的,一百五六十首歌,我們只能選二十多首。其他還有歐陽飛鶯等,歌也比較多。選一些大家知道的當年比較出名流行的歌曲,還有一些可能比較符合現代人的審美習慣,就把它留下來。
《新民周刊》:以前人們喜歡用“革命”或者“左翼”來把一些詞曲作家與另外一些音樂人對立起來,但這套唱片里并不避諱這些,把一些以前比較少放入流行音樂領域的歌曲也選入了,流行歌曲和革命歌曲,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王勇:這套專輯最后做的是整體的“上海老歌”,與最早考慮的做“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的編輯思路有些不同,我覺得應該把各種各樣的歌曲都放進去。因為當年那些創作歌曲、演唱歌曲的音樂人,他們的陣營并沒有我們現在認為的分得那么清楚,不像今天我們已經人為地按上了政治烙印。比如像賀綠汀這樣的作曲家,他有過《牧童短笛》那樣很專業的作品,也有過《天涯歌女》這樣的電影流行歌曲,后來也有像《游擊隊之歌》這樣的革命斗爭歌曲。所以我們覺得人為地把它分裂,這不符合歷史的原貌。
另一方面,我們希望能夠全面。上海老歌的組成,相當數量的一塊是所謂的“時代曲”;還有一塊是電影歌曲,分為職業歌手演唱與影星自己演唱,我們把影星唱的歌專門做了2張CD。還有一塊是“明月社”出道的歌手歌曲。最后一塊是所謂的學院派和“左翼”,這批人也唱電影歌曲,與其他的歌手們的關系也很近,所以我覺得把他們拋開是不合適的;而且這些歌曲在當時也很流行,我們不能僅從唱法或者政治因素來考慮,應該從接受度的角度來選擇,所以我們決定把能拿到的都放進去。像《義勇軍進行曲》,我們也放了進去,其實革命歌曲的流行度在當時也很強。我希望能夠多元化的展示那個時代歌曲的面貌。

“明月社”是流行歌曲搖籃
《新民周刊》:當年,除了“明月社”,還有一些歌舞團體,比如“梨花歌舞團”、“新華歌劇社”等等,這些音樂團體,對當時的流行音樂產生過怎樣的影響?
王勇:“明月社”是公認的中國流行歌曲的搖籃,它延續的時間很長,培養的人才很多,帶來的曲目很廣,當時沒有哪一個歌舞劇社可以跟它相提并論。像魏縈波辦的“梨花歌舞團”是比較早期的,規模不大,團里有龔秋霞。其他還有一些歌舞劇社,比如“新華”這樣的,大多是“明月社”的團員離開了以后自立門戶創辦的,所以源頭還是在“明月社”。書中我沒有專章介紹這些團體,因為我們現在還能知道名字的這些團體,通常都是人帶著團,而不是團帶著人,所以就放在個人的演藝生涯當中提及。像“新華”是嚴華的,“大同歌唱社”是姚敏、姚莉兄妹的。這些小團沒有體系,這些人做,團就在,不做,團就散了,不像“明月社”的影響力這么大。
《新民周刊》:當時中國比較少音樂學校,是不是“明月社”就代替了音樂學院的一些功能?
王勇:它們是兩種體系。“明月社”承襲了中國傳統的“科班”體系,所做的是流行的東西,它是以演出來帶教學,有人把它跟日本的寶塚歌舞團劃在一個類型里面。
《新民周刊》:書中提到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原來也是“明月社”的,和黎莉莉一樣是黎錦暉的養女,那時叫黎明健。后來,她去了北京,還和這班歌手朋友有來往嗎?
王勇:在北京她和他們之間還是一直有聯系,老朋友們也還在走動,雖然很多人后來都“靠邊”了、“打倒”了,但是聯系沒斷。于立群和“明月社”的王人美、黎莉莉都一直有聯系的,還有楊露茜,原來也是“明月社”的,后來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還受到過首長們的接見,這些人建國后社會地位也不低。
出唱片,讓全上海認識你
《新民周刊》:當年流行歌手,一般通過電臺、唱片、電影插曲、歌舞廳等幾種方式演唱成名,哪一種最容易出名?
王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起步方式,運氣好的直接就被唱片公司看中了,沒怎么唱就灌錄第一張唱片了。例如姚敏,當時他妹妹姚莉已經在“百代”錄音了,她推薦哥哥去,姚敏到了“百代”除了寫歌,也跟著唱,所以很快就出了唱片,也有了知名度。當然,比較多的還是走兩條路,一條是歌舞廳駐唱,一條是電臺,那個門檻低。
《新民周刊》:當時的電臺播音跟我們現在不同吧,我們的DJ只要播放錄音就行,當時要歌手到那邊親自唱的吧?聽眾打電話“點歌”,難道一排歌手等在那里“點播”?
王勇:也沒那么夸張。當時所謂的電臺比較小,就樓頂上拉根天線,發射功率低,只能波及方圓一兩公里的范圍,就像“社區電臺”,一個上海有數百家電臺吧。電臺里是有一個現場的band(樂隊),幾個人,小電臺的駐唱歌手也就一兩個人,沒有一堆歌手,聽眾可以點不同的歌讓他們唱。那時紅一點的歌手就每天跑不同的電臺,所謂“跑臺”,所以真正點“人”的其實不太多,點“曲”的比較多。
《新民周刊》:你的書中寫到過一個男歌手,叫黃飛然,他是典型的歌舞廳駐唱歌手。
王勇:不只黃飛然,有好幾個通過駐唱成名的歌手,姚莉也是一個,姚莉唱過電臺,后來主要的生活來源靠歌舞廳駐唱,一個是“仙樂斯”,一個是“揚子”。歐陽飛鶯也是一個駐唱歌手。這種駐唱歌手的好壞體現在哪里呢?就是你唱的時候,別人是在聽(歌)還是在跳(舞)。歌舞廳駐唱是相對而言比較容易找到機會的。
當然最終都是要出唱片,因為電臺小,歌舞廳駐唱也有局限,只有出唱片,才有機會讓全上海的人都認識你。
《新民周刊》:唱片公司給歌手的報酬怎么算?
王勇:按版稅支付,一般是6%。不過,創作者的報酬很少,創作人一般是買斷的,也有聘用的,像嚴華、黎錦光這樣,“百代”專門聘用來作詞作曲,但這樣的人很少。
40年代開了第一個“個唱”
《新民周刊》:據說第一個開個人演唱會的是“歌后”白虹,演唱會在當時應該是個新形式吧?
王勇:1945年的1月12日、13日,當時在“蘭心”做了白虹歌唱會,這個時候上海的流行音樂已經發展到比較成熟的階段了。以前,人們都接受“看不見”的歌手,電臺里、唱片里;要看見歌手,通常就要去歌舞廳。但是歌舞廳的欣賞取決于那些買票的人,他可以聽,也可以跳;碰到喜歡的歌手、歌曲,會安靜下來聽唱歌,但是有人在你唱歌的時候要跳舞,也不能拒絕,從某種意義上還是伴唱。所以說,有了歌唱會之后,使得歌曲成為主導,大家買票就是為了聽歌的,這對于歌手來說,一方面他地位提高了,另一方面挑戰性增加了——他完全要靠演唱來吸引觀眾買票。這是很重要、劃時代的一件事情。
那時白虹在藝術上已經很成熟了,資格也比較老,所以她第一個開,在白虹開了“個唱”之后,沒有多久周璇也開了個人演唱會。周璇當年的粉絲肯定比白虹要多,因為周璇有大批的影迷。所以,周璇開“個唱”,比白虹多開了一天,三天。白虹在“蘭心”,比較小,她就在“金都大戲院”開了演唱會,她的“金嗓子”名頭再一次流傳起來。
《新民周刊》:不過現在聽起來,周璇的唱法似乎并不是很“現代”,反倒是白虹、姚莉的歌喉與現在的流行歌手比較接近。
王勇:周璇的唱法是她本身的先天條件決定的。她嗓門不大,聲線很細,另外,在“明月社”當中,她的一些前輩——黎明暉、王人美等人,在30年代唱歌用的是本嗓,咿咿呀呀的小女孩聲音,就是魯迅講的“絞死貓”的聲音。到了40年代,大家唱歌的聲音都在做調整,白虹在年輕的時候的音色也沒有后來那么好,反差最明顯的是王人美。40年代的時候,也可能受了美國來的歌舞片的影響,對于如何運用氣息越來越精通了,很多“好聲音”也出來了。比如歐陽飛鶯,她是一個很奇怪的人才,她自學的,但她可以唱花腔,她用西洋唱法的某些技巧來演繹流行歌曲,而且唱得很好聽。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30年代的錄音技術比較差,中頻和低頻的表現力很弱,都是高頻,所以始終聽到很尖的聲音。40年代錄音設備改善了,所以聽上去比較舒服了。
《新民周刊》:上海的流行音樂在40年代有長足的發展,你也選了不少這個時期的歌曲,孤島時期的鶯歌燕舞一直是有爭議的,你怎么看?
王勇:從唱片廠的角度來看,孤島時期唱片發行多少還是受到了日本人的控制,像愛情歌曲發行就比較方便,其他的就比較難了。越是在政治等各種因素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人們內心想得到宣泄的欲望就越強烈,從這個角度講流行歌曲在當時還是頗有市場。單純把孤島時期的鶯歌燕舞說成是破壞“抗日”我覺得是不合適的。
1945年以后,原先的上海三大唱片公司——上海百代、大中華(注冊商標為“雙鸚鵡”)和上海勝利(RCA與勝利留聲機合并,是日資公司)的格局有了較大變化。“勝利”這時成了敵產,后來一直未能開工;“百代”抗戰結束后又重新經營;民族企業“雙鸚鵡”經營慘淡,奄奄一息。等于說45年以后,上海唱片業,就是“百代”一家獨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