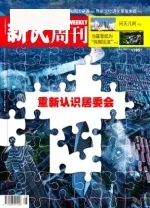杜月笙魂兮歸來
沈嘉祿
杜月笙坐船駛離高橋港時(shí),久久地站在甲板上,回望家鄉(xiāng),一直到地平線消失在滾滾濁濤中。

上周去高橋鎮(zhèn),欣慰地看到高橋鎮(zhèn)政府在改造老街的過程中搶救了一些老宅,并對(duì)鎮(zhèn)內(nèi)一百多幢老宅進(jìn)行查訪,登記掛牌,還準(zhǔn)備對(duì)殘留的600多米長一段老街進(jìn)行修整,在街上開辟幾個(gè)有地方特色的展館。
說起高橋,不少人一定會(huì)想起杜月笙。對(duì)上海史稍有了解的讀者都知道,杜月笙出生于高橋杜家宅,四歲喪母,六歲喪父,靠外祖母撫養(yǎng),落難時(shí)還吃過百家飯。杜月笙后在十六鋪“潘源盛”水果行發(fā)跡,并得到陳世昌和黃金榮的提攜,靠三鑫公司販鴉片致富,與黃金榮、張嘯林并稱上海“三大亨”。
成為72家企業(yè)董事長的杜月笙對(duì)高橋還是有感情的,1931年他在家鄉(xiāng)買地建造杜家祠堂,成為轟動(dòng)一時(shí)的新聞。杜月笙在祠堂落成之時(shí),連蔣介石也送了一塊匾:“孝思不匱”,杜還請(qǐng)各地梨園界名角演堂會(huì),空前絕后的盛況至今還是飯后茶余的談資。抗戰(zhàn)時(shí),日軍飛機(jī)轟炸高橋的德古火油公司,殃及杜家祠堂,現(xiàn)僅存藏書樓歸部隊(duì)所有。我兩次前往高橋,均無法進(jìn)入看個(gè)究竟。
杜月笙少年時(shí)得到鄉(xiāng)鄰接濟(jì),發(fā)達(dá)后對(duì)家鄉(xiāng)人是知恩圖報(bào)的。有一次,一位高橋人遇到急難,輾轉(zhuǎn)來到市區(qū)華格臬路(今寧海路)杜府,看門人見是鄉(xiāng)下人打扮,不耐煩地轟他走,正巧杜月笙送客人出門看到:“這不是高橋爺叔嗎?快快請(qǐng)進(jìn)里面坐。”并吩咐下人,以后凡有高橋爺叔來,一律請(qǐng)進(jìn),不準(zhǔn)怠慢。從此,“高橋爺叔”成了家鄉(xiāng)人的代名詞。至今高橋人遇到口角,也會(huì)息事寧人地找臺(tái)階:“算了,我不跟你多爭了,你是高橋爺叔!”
吳耀中老伯就是正宗的高橋爺叔。他的父親吳瀚章(后馬相伯為他改名為吳繡文)畢業(yè)于圣約翰大學(xué),后來在上海市中心做五金生意,在杜月笙落難時(shí)曾給予多方面的關(guān)照。后來杜先生——高橋人今天還是這么叫——發(fā)跡了,還拉他一起做過生意,自然是讓利三分了。杜先生離開大陸前往香港前,曾跟少年吳耀中作過一小時(shí)長談,最后一聲長嘆:“爺叔最對(duì)不起你的是,沒有讓你一起跟我做事體。以后你還是要好好讀書,這個(gè)社會(huì)不管啥人當(dāng)家,讀書總是要緊的。”后來,吳耀中考進(jìn)了滬江大學(xué),畢業(yè)后在上海市五金一店工作。
“高橋爺叔”吳耀中當(dāng)然是高橋的大戶人家,至今居住的至德堂是文保單位,有140年的歷史,花園里種著梅、桃、石榴和桂花。廳堂里還有如今罕見的蠣殼窗,也就是用蚌殼磨薄后嵌在花格窗框內(nèi)以透光照明。吳老先生跟我談起高橋的美食,眉飛色舞,口若懸河:“小時(shí)候我們家里吃刀魚飯,待大米飯沸滾收水時(shí),將刀魚一條條鋪在飯上,飯燜透后將魚頭一拎,龍骨當(dāng)即蛻去,魚肉與米飯拌透,加一勺豬油和少許鹽,那個(gè)香啊、鮮啊,終生難忘。”
高談間,高橋爺叔突然話頭一轉(zhuǎn):杜先生在家鄉(xiāng)大張旗鼓建造祠堂,還造了學(xué)校和醫(yī)院,今天的第七人民醫(yī)院就是由杜先生造的醫(yī)院擴(kuò)建的。杜先生到了香港,他的學(xué)生萬墨林悄悄回過上海,曾跟我父親說,杜先生坐船駛離高橋港時(shí),久久地站在甲板上,回望家鄉(xiāng),一直到地平線消失在滾滾濁濤中。臨終前,他流露出落葉歸根的想法。現(xiàn)在,杜的兒子杜維善在加拿大,另一個(gè)兒子杜維寧的女兒杜美如在約旦,杜維善前些年回上海,向上博捐了一批稀世錢幣,但不曾提出索回杜家房產(chǎn)。杜在高橋已無根苗,但高橋有一批“爺叔”很熱心,提議讓杜先生的墓遷回故里,以完成他的心愿。此事政府不便出面,杜氏后代也無授權(quán),“爺叔”們就無從下手。
今天,新樂路上的三鑫公司成了一家豪華酒店,東湖路上的杜公館在建國后是東湖賓館,現(xiàn)在卻有人在靠淮海路口利用一幢花園洋房開了一家名為大公館(諧音杜公館)的飯店,都想拉杜月笙做幌子。所以,杜月笙真的魂歸故里,說不定就會(huì)成為一個(gè)旅游景點(di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