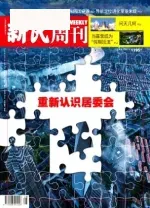“lost”在影像與文學之間
思 郁
文學經典能毀掉一部電影,而有些吊詭的是,電影有時卻能成就一部文學經典。
據說現在的好萊塢人人都有兩份工作:除了自己那份,另一份就是電影評論。這話說得有點諷刺,不過倒是讓我松了口氣:幸好我只是一個半吊子的影迷,不是所謂的電影評論家。在我看來,影迷看電影比影評人更純粹,因為只有他才能欣賞影像中無功利的美。這同樣也是我喜歡另一位資深影迷李歐梵先生寫的兩本書《看電影》(上海書店版)和《我的觀影自傳》(上海三聯書店版)的原因。

李歐梵先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狐貍型學者,從他的觀影史就知道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資深影迷了。李先生家學淵源,自幼接受藝術方面的熏陶,從中學起就開始接觸電影,閱片甚多,漸入佳境,給雜志報紙寫影評自然順理成章。不過少年時寫影評為稿酬,可以有錢看更多的電影,而現在寫影評可以是為了消遣退休后的大好時光,也可以為自己的文學研究增添些許的情趣。其實誰都會看電影,但就如一部《紅樓夢》,經學家能看見《易》,道學家能看見淫,才子能看見纏綿,流言家能看見宮闈秘事,凡此種種,可見同一個世界,不一定就有同一個夢想,同樣一部電影,大家看到的估計也不盡相同吧。像李歐梵先生這樣的學者看電影,也有其獨特的角度,從文學,從文化,乃至從人性都能洞若觀火,體察入微。簡言之,學者看電影,必然有能學習之處。
《看電影》與《我的觀影自傳》兩本書精選了李先生近些年寫的影評文字幾十篇,內容涉獵廣泛,從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歌舞片,到現在21世紀的商業大片,從好萊塢的類型電影到歐洲的一些藝術電影,從中國的經典老電影《小城之春》到現今爭議紛紛的《色·戒》,從胡金銓導演的《俠女》到張藝謀的《十面埋伏》……一會從縱向到橫向比較,一會又從細節到全局概括,點面俱全,看似雜亂繁復,無章可循,但一口氣讀下去,卻能條分縷析。
李先生頗能利用文化方面的理論解讀電影文本,比如從李安的《斷臂山》和《臥虎藏龍》中能看到文化壓抑;從伍迪·艾倫的《賽末點》中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等等,都是那些所謂的職業影評人所體會不到的。更難得的是李先生能用深入淺出的語言,避免用學究式的術語把一部部電影娓娓道來。他寫得興致盎然,我讀得也是興致盎然。
作為研究文學的學者,李先生看電影的時候自然會對文學與電影的關系做些比較,電影史上的許多經典都是根據文學中的經典改編,只是文學用的是文字,而電影用的是光影。張愛玲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的不算少數,李安也加入了這個改編行列。但是不得不承認想要改編像張愛玲這樣的天才作家的作品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大導演希區柯克有個很著名的理論,認為名著不適合改編成電影,只有那些二三流的文學才能成為電影中的經典。這是個很討巧的說法,但是的確說出了某種事實,名著在大眾心目中影響力巨大,勢必會影響導演的看法,而那些二三流的文學反而給了導演想象的空間。張愛玲的小說中,《傾城之戀》是經典,但每次改編都會引起很大的爭議。文學經典能毀掉一部電影,而有些吊詭的是,電影有時卻能成就一部文學經典。
看電影時糾纏在光與影的超現實中,讀經典時腦中浮現的是文字的芳香和溫暖。李歐梵先生在文中曾提到美國的影評家Kael寫過一本影評集,叫做I Lost It At The Movies,這個“lsot”很能代表我此刻的心境,無論是文學文本還是電影文本,都讓人沉醉乃至迷失。
《非常梅蘭芳》
電影《梅蘭芳》的喧喧嚷嚷讓已故國劇大師重歸主流焦點。梅蘭芳,從“祖師爺不賞飯”到“四大名旦”之首,其間經歷哪些坎坷?他的藝術究竟好在哪里?他同孟小冬的婚戀真相如何?在他藝術高峰期,卻為何停止演出?而“移步不換形”又為何成為他的藝術遺囑?作者翁思再在央視“百家講壇”的《梅蘭芳》講座中都給予了解答,本書是根據節目內容整理加工而成。
翁思再 著,中華書局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