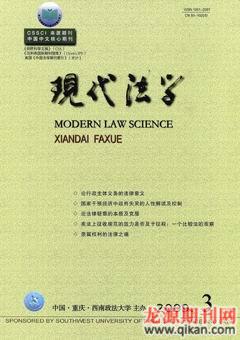論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意義
摘要:行政主體義務對行政法關系乃至于行政法治的走向起著決定性作用,它與行政法中的“權利”和“權力”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我國行政法學界歷來重視對后兩者的研究而忽視了前者,沒有給行政主體義務以科學的定位,這不能不說是行政法學理論的一大缺憾。行政主體義務的成立,必須有法律或職權上的依據,有行政法上的義務形態,有行政法上的權利主體,有完成義務的行為能力;行政主體義務在法律表現上有其獨特之處,它是一個復雜的義務鏈條,是管理義務與服務義務的統一,是積極義務與消極義務的統一,是職權義務與行為義務的統一,是法規義務與契約義務的統一;行政主體義務對行政職權定“責”,對行政法關系定“性”,對行政行為定“量”,對行政救濟定“度”有重要的法律意義。
關鍵詞: 行政主體;義務;法律意義
中圖分類號:DF31
文獻標識碼:A
“義務與權利相對待,有權利即有義務。行政法上的義務,亦即與行政法上的權利相對待的義務。”[1]可見,在行政法中,義務與權利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然而,我國學界在探討行政法問題時似乎對“權力”、“權利”等主動性概念更感興趣,而對義務的研究少之又少
(注:我國第一部全國統編的行政法教科書雖然著述了行政法關系的概念和內容,然而,在講授行政機關在行政法關系中的地位時,僅僅列舉了行政機關在行政法關系中所享有的4種權利,即形成權、命令權、處罰權、管理權,對行政機關應承擔的義務沒有任何說明。參見王珉燦行政法概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2第二部行政法統編教材根本沒有涉及到行政法關系以及行政法關系中的權利義務,在“行政主體資格”一章也只對行政主體資格的取得作了概括,沒有提到行政主體義務的概念。參見王連昌主編:《行政法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頁。第三部行政法統編教材更是提出了一個非常令人費解的概念,即認為行政主體的權利與義務是重合的,即行政主體行使的廣泛權利反過來說也就是義務,由此可見,其基本上忽略了行政主體義務的研究。參見羅豪才行政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25)。筆者認為,就行政主體以及行政權而論,義務無論在理論闡釋中,還是在實際運作中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既是因為權利不能離開義務而成為獨立的存在物,也是因為權力本身若脫離了義務便無法進一步推演。行政主體義務對于行政法關系乃至于行政法治的走向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正是基于此點,筆者將對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地位作一系統探討。
一、行政主體義務的界定
行政主體義務是指由行政法規范規定的行政主體在行政過程以及行政法關系中的職責、任務和相關的行政使命。行政主體義務作為一個范疇概念最早出現在倫理學中,“作為行政倫理重要范疇的行政主體義務是指行政主體的道德義務。”[2]就是說,在進入行政法狀態之前,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前行政法狀態”的情況下行政主體義務就已經存在,這時的義務是受行政倫理制約的義務。應當說,行政倫理范疇的行政義務為后來行政法上行政主體義務的形成起了決定性作用(注:“行政道德義務是多方面的,從忠于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機密到廉政勤政等,都是行政道德義務的要求,但其最核心、最根本的內容是忠誠并服務于國家和人民。”可見,行政管理義務對行政法上行政主體的義務內容及其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一些國家在行政法制定時,將原來屬于行政倫理義務的內容轉化為了行政主體在法律上的義務。參見朱貽庭倫理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224張載宇行政法要論[M]臺北:漢林出版社,1978:62),但行政法上的行政主體義務畢竟不同于行政倫理中的義務,其主要區別在于形成行政主體義務的規則體系有所不同;行政主體義務是以公務法人身份出現的義務,即義務主體是行政機關或者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而不是行政公職人員依《公務員法》或者《公務員服務法》(注:我國臺灣地區有專門的《公務員服務法》,它的內容是有關公務員履行職責時的義務,是歸屬于公務員個人的義務,而不是行政主體的義務。一些國家的憲法在規定行政系統的義務時,也將行政主體義務與公務員的義務予以區分。)而確定的屬于個體的義務。行政主體的義務是由行政職權派生的,與職權有著相輔相承的關系,而行政公職人員的個體義務則與作為行政權范疇的職權無直接關系;行政主體義務不同于行政行為,行政行為是行政主體在行政法上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而這種作為或者不作為是行政主體對行政職權的運用,行政主體義務則是更深層次的東西。嚴格地講它是“法律為保障特定利益而課以行政相對人以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拘束力。”[1]134就是說,行政主體義務是對行政主體作為與不作為的約束力,這是其與行政行為的本質區別。當然,行政主體義務也常常以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表現出來。上列三個方面是我們探究行政主體義務時必須首先澄清的問題。若將行政主體義務概念進一步延伸的話,其有下列本質屬性。
其一,行政主體義務是歸屬于行政主體的義務。“行政主體是依法享有國家行政職權,代表國家獨立進行管理并獨立參加行政訴訟的組織。”[3]這是關于行政主體的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定義,該定義表明行政主體與“國家”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它是代表國家行使行政職權的機關或者組織。這就牽涉到行政主體義務與國家行為或國家義務的關系,即是說,行政主體義務是否就是國家義務,或者反過來說,國家義務是否就是行政主體義務。這兩個命題的第一個命題即國家義務就是行政主體義務的說法顯然不能成立,理論界也普遍這樣認為;而第二個命題即行政主體義務就是國家義務則被理論界認同,而且這種認同并不是個別現象。如有教科書指出:“國家行政機關的權利,又稱職權,具有國家強制力,是一種國家職權。國家行政機關的義務,就是國家行政機關的職責。各級國家行政機關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其基本職能就是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決議,其義務也是一種國家義務。”[4]筆者認為,理論界的這種認識存在一定的錯誤。行政主體義務雖為國家通過法律為其確定的義務,但行政主體的義務本身并不能等同于國家義務,也就是說行政主體的義務不是國家義務,而僅僅是行政主體自己的義務。一方面,行政主體與國家是兩個主體,其與國家是一種公法上的契約關系(注:行政主體與國家雖不曾有類似于合同書的東西將二者的權利義務確定下來,但是一國的憲法和政府組織法似乎都將行政主體與國家的關系確定為服務關系,而這樣的關系就是一種類似于合同的關系。我國行政法教科書一般這樣認為:行政主體是由國家設置,代表國家行使國家職能;但不進一步指出這種代表是一種什么性質的行為。參見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92),它代表國家行使行政職權,獲得了一定的物質和精神利益,正是這種利益導致了它在法律上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另一方面,行政主體所為的是一種法律行為,而不是國家行為,國家通過法律的形式對行政主體定職定責,行政主體本身并不能將自己的行為與國家行為相等同。如果我們錯誤地將行政主體義務等同于國家義務,那么,我們便必然陷入到在控制行政主體行政行為和行政權時控制了國家行為和國家政權的泥塘中去。
其二,行政主體義務是存在于行政過程中的義務。行政主體義務究竟是一個靜態概念還是一個動態概念,這在行政法學界也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為行政主體義務是一個靜態概念,所謂靜態概念是指行政主體義務是靜止的,如果不是絕對靜止也是相對靜止,該靜止性表現在行政主體義務是在國家設立行政機關時就已經確定好的,無論行政機關如何變化義務則是相對穩定的,法律規則的穩定性決定了行政主體義務的穩定性。有學者將這種穩定性描述為一種恒定狀態:“行政法中權利——職責關系、權力——義務關系都是這一最本質的關系的展開。以權利為始點,權利——權力關系、權力——義務關系也都是為了實現權利而形成的,所以權利又是一切法律關系的歸宿。”[5]這種將權利與義務高度抽象化的思維方式便是對行政主體義務恒定性的描述。行政主體義務靜止性理論雖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其基本的思維進路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權利與義務是在復雜的法律關系運作過程中體現自身價值的。鑒于上述原因,便有了第二種關于行政主體義務認識的進路,即動態化進路。該論認為行政主體義務是動態的,處于不斷的運行之中。行政主體義務發生于行政權的運作過程中,也許,法律規則在規定行政主體義務時并沒有考慮它的動態性,然而,一旦被寫進法律規則中的行政主體義務要有實質意義的內容就必然發生于行政進程之中。“當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遭受到行政機關的不法侵害時,行政機關負有賠償其損失的義務;行政機關因執行法律或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損害了公民或法人的利益,行政機關有依法予以相應補償的義務。”[4]40這便是行政主體義務動態化的具體表現。
其三,行政主體義務是對應多個相關主體的義務。在行政法教科書中或者說在傳統的行政法學理論中有學者認為行政主體的權利義務與行政相對人的權利義務是相互對應的,即行政主體的權利就是行政相對人的義務,行政主體的義務就是行政相對人的權利,反之亦然。筆者將這種行政主體義務對應物的單一性稱之為“義務對應主體單一論”。(注: “義務對應主體單一論”的形成是由我國長期以來對于行政法關系的理解決定的,我們將行政法關系定義為在行政管理活動過程中行政主體與管理相對一方形成的關系。顯然,相對一方就是行政機關管理的一方,因此行政機關的權利是指向它的,義務也是指向它的。參見侯洵直中國行政法[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7)此論在我國行政法學界幾乎占統治地位。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理論,主要是因為我國行政法學界對行政法關系存在單一范疇的認識,即我們一般把行政法關系僅僅限定在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中,而沒有將行政法關系拓展到行政主體與其他主體的關系之中。由于行政法關系僅僅是這種單一形態,那么,便順理成章地得出行政法關系主體義務的對應一方就是行政相對人;但是,隨著我國行政法治進路的不斷多元化,行政主體義務的對應主體便不能單單理解為行政相對人。事實上,行政主體義務所對應的是多個層面的主體,如行政主體對應于立法機關的義務、行政主體對應于司法機關的義務、行政主體對應于不同層次行政機關的義務。而且,上列每一種對應主體都可以向行政主體期求這樣那樣的權利,如立法機關可以向行政機關期求質詢權,行政主體便產生了答復的義務;司法機關可以向行政主體期求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權利,行政主體便有了應訴的義務;上級行政機關可以向下級行政機關期求指揮的權利,下級行政機關便有了服從的義務,等等。行政主體義務對應主體的是否多元化既可以反映一個國家行政法治水平的高低,又能夠衡量一個國家行政權運作過程中行政主體的責任水平。(注:行政法的理論和行政法治的實踐實際上有兩個不同的類型,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講的“限權法”類型和“管理法”類型。在“限權法”理念指導下,行政法關系主要是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的關系,立法機關通過立法權約束行政權,司法機關通過司法審查約束行政權。在“限權法”理念下行政機關與被管理者的關系只是行政法關系的一種形態,而不是全部形態。在“管理法”理念指導下,行政法關系主要是行政機關與被管理者的關系,我國行政法關系單方面性的理論就是在“管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
其四,行政主體義務是強制性義務。“行政道德義務與行政法律義務的不同主要在于:前者是行政主體自覺自愿履行的義務,而后者是強制性的職責規定;行政道德義務的履行不以獲得相應的權利為前提,而行政法律義務的履行則與相應的法定職責相對應。”[2]224這是學者們對行政主體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的區分。行政主體的義務有諸多來源,如有傳統的來源,就是一個國家長期以來的行政傳統形成了行政主體無形的義務形態;還有如來源道德上的來源,它是指行政道德,即人們在法律規則以外對行政主體行為的評價等等。在行政法中,行政主體道德上的來源也罷,傳統上的來源也罷,甚或其他方面的來源也罷,都不是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定來源。換句話說,我們在行政法上所研究的行政主體的義務不包括道德義務、傳統義務等。行政法所關注的行政主體的義務僅僅是來自于憲法和法律以及其他正式的法律淵源所賦予行政主體的義務。行政法上行政主體義務的來源便決定了行政主體義務不能僅僅依靠行政主體的自主意志決定履行與否,即行政主體自愿也好,非自愿也好,一旦某一行為準則被確定為行政主體在行政法上的義務,其就具有必須予以執行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講,行政主體的義務若在行政法的范圍內論之都具有強制性,都是一種強制義務。行政主體義務之所以在行政法上具有重要地位與義務本身的強制性不可分割。(注:義務的強制作用是指“不得由義務人任意變更或免除之謂,故義務人必須履行其義務,否則為違反義務,受法律上的制裁,是為拘束力之效果。”參見涂懷瑩行政法原理[M]臺北: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3:134)
二、行政主體義務成立的法律要件
行政主體義務應當是一個規范概念,所謂規范概念是指它在行政法上應當具有獨立完整且公認的定在。一則,行政主體義務應當是一個獨立概念,具有獨立的解釋行政法問題的能力,這一點是非常關鍵的。若行政主體義務沒有這樣的能力,不能扮演解釋相關問題的角色,那么,其在行政法治和行政法理中的地位便是十分欠缺的。誠然,我國行政法學體系中很早就有了行政主體義務的概念,但是,在我國行政法治和行政法理中,行政主體義務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工具性或闡釋性概念,它常常被歸化于其他相關的概念之中,如我們常常將行政主體義務與行政法關系聯系起來,使其成為行政法關系中的一個子概念(注:如有學者認為“權利義務為相對之名詞,國家及人民,在公法關系上既享有一定的權利,自然負有相當之義務,就國家之義務而言,對于自由權,有不得違反侵害之義務,對于受益權有作為之義務,對于參政權平等權有承認其權利之義務。”還有學者認為:“行政法關系與行政關系的區別在于:后者未經法律調整,只是一種事實社會關系,而前者是依據法律發生的,或者雖非根據法律發生,但法律已對關系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作了規定,雙方關系已進法律調整之中:當事人的相應權利受到法律保護,當事人的相應義務必須履行,如違反義務,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上列兩論都將義務視為行政法關系的一個子概念,而不是一個獨立的概念范疇。參見林紀東行政法新論[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85:90姜明安行政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1),似乎離開了行政法關系,行政主體義務就不具有實質性意義。我們還常常將行政主體義務的概念與行政責任的概念相混淆,這些都使得行政主體義務失去了獨立地解釋行政法問題的能力,失去了獨立地建構行政法治體系的資格。二則,行政主體義務應當具有行政法上的定在。所謂行政法上的定在,是指其本身的內涵和外延以及法律形式上應當具有相對的確定性,而不能夠在此一場合具有這樣的意義,而在彼一場合則具有那樣的意義。筆者查閱了相關國家的憲法,有些國家在其《憲法》條文中明確規定了行政主體的義務及其范疇,有些國家則以暗含的形式規定了行政主體的義務,而絕大多數國家的憲法并無行政主體義務的獨立概念。(注:例如《古巴共和國憲法》第97條規定:“部長會議向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負責并定期報告自己的工作。”《希臘共和國憲法》第85條規定:“依照關于部長責任的法律的規定,內閣成員和副部長應對政府的總政策負集體責任,并對各自職權范圍內的活動或失職行為負個人責任。”參見蕭榕世界著名法典選編(憲法卷)[G]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183)由此可見,行政主體義務的不規范性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基于這樣的實際,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為行政主體義務確立一些法律要件。
第一,行政主體義務的成立,要求必須具有法律或職權上的依據。“公法關系是法律關系的一種,同一般法律關系一樣,其內容也是由公法關系的權利與義務,即公權與公義務構成的。關于公權與公義務,第一,私法上的權利義務是比較典型的一般性的權利和義務,將公權與公義務與之進行比較,明確不同的性質、內容和特殊性,是必要而有益的;第二,還需要明確公權、公義務與類似于個人公權的反射利益的差異;第三,應研究由于公法上的特別原因所產生的公權上的特殊權力關系。”[6]可見,作為公義務范疇的行政主體義務是受公法調整和規范的。該概念揭示了行政主體義務的第一個構成要件就是必須有法律或職權上的依據。作為法律依據是指行政主體義務由法律規范規定,任何一個屬于行政主體義務的東西都應當從憲法和相關的法律規則中找到依據。如1919年頒布的《魏瑪憲法》第88條規定:“郵政、電報、電話事業,專屬于聯邦。郵票全聯邦一律。聯邦政府得聯邦參政會之同意,得頒布交通規則及使用交通設備應納之費,并得將此權委托于聯邦郵務部。關于郵政、電報、電話之交通事務及其價目表,聯邦政府如得聯邦參政會之同意,得酌設顧問機關。關于與外國訂立交通上之條約事件,專屬聯邦。”[7]該條文對聯邦政府相關義務作了規定。當然,行政主體大多數義務應當體現在法律規則之中,尤其部門行政管理的法律規范之中。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31條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并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這一規定非常具體地規定了行政主體在行政處罰中的告知義務。在行政法治中,行政主體義務還有一部分不是或者沒有直接的法律依據,但具有職權上的依據。所謂職權上的依據就是指該義務是從行政主體所享有的行政職權推演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所規定的是行政主體的職權或權利,而這一職權或權利包含了相應的義務。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規定行政主體有征兵之職權,該職權同時隱含了行政主體諸多的義務,如照顧軍人家屬、提供撫恤金等。行政主體義務必須具有法律上的依據,也可以通過依法行政原則得到反證。按照依法行政原則,行政主體的職權或者權力必須依法取得,與之對應行政主體的義務也必須符合依法行政原則的要求,因為義務的擴大有時可能就是職權或權利的擴大。再則,行政主體一旦與國家形成行政契約關系,這種關系就應當是一種雙向約束的關系,即既約束行政主體又約束國家,義務的法律準據就是這種雙向約束的具體表現。
第二,行政主體義務的成立,要求必須有行政法上的義務形態。凱爾森認為:“相對的義務是對于某個特定人的義務;而絕對的義務是對于無定數人或一切人的義務。不殺人、不偷竊、不干涉他人的處分其財產,都是絕對的義務。債務者向其債權者還借款的義務,是相對的義務。相對的狹義權利,僅僅對待于某個特定人的義務;而絕對的權利都引起無數人的義務。典型的相對權利,是債權者對于債務者的權利;他只有向債務者要求收回貸款的權利。典型的絕對權利是所有權;所有人有要求任何人不得過問其處分財產的權利。絕對的義務,對待于絕對的權利;相對人義務,對待于相對的權利。”[8]這是對法律義務理論的一個高度概括,表明法律上的義務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有一定的外形,通過這種外形將具體的人或者具體的事套進義務的框架之內。法律的價值就是通過權利義務的具體化、人格化而體現國家意志或者抽象意志的。正如盧梭所指出的:“我說法律的對象永遠是普遍性的,我的意見是指法律只考慮臣民的共同體以及抽象的行為,而絕不考慮個別的人以及個別的行為。因此,法律很可以規定各種特權,但是它都不能指名把特赦賦予某一個。法律可以把公民劃分為若干等級,甚至于規定取得該等級的權利的種種資格,但是它卻不能指名把某某人列入某個等級之中。”[9]但法律規則的抽象性最終還是需要具體化的,對于法律規則的具體化而言,其中義務便是一個最好不過的替代物。進而言之,行政主體義務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和現實的,這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我們所講的行政主體義務的第二個要件,即行政法上的義務形態。所謂行政法上的義務形態就是指行政主體義務通過具體的要素和形式體現出來。傳統行政法理論認為,行政主體的義務形態可依各種各樣的標準進行分類,如可依行政法關系的范圍分為概括的義務、對待的義務、特定的義務。可依義務自身的內容分為執法及守法的義務、給付的義務、受理的義務、保護的義務、平等對待的義務等。(注:從上列關于行政主體義務的分類可以看出,行政主體義務并不僅僅存在于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之中,如就“概括的義務”而論,“此種義務的內涵而言,可以包括國家與政府職能的全部,亦即國家應促使政府發揮此等職能,負起增進國家安定繁榮及人民福祉的責任。”參見張家洋行政法[M]臺北:三民書局,1998:181)總之,行政主體義務必須以一定的法律形式表現出來,否則,其便不一定有實質性的內容。(注: 關于行政法關系中主體與客體的問題在行政法學界存在不同認識,有學者認為所有行政法關系的參加者都是行政法關系的主體;有學者認為主體只有行政機關,而行政相對人是客體;還有學者認為主體與客體可以互換。參見管歐中國行政法總論[M]臺北:藍星出版公司,1984:73)
第三,行政主體義務的成立,要求必須有行政法上的權利主體。“法律主體的意義一般用來是指可以成為主觀權利執掌者的分子而言(我特別盡量使用最普通的名詞)。法律主體的問題就是要明確一個分子必須具備哪些條件才能成為主觀權利的執掌者;要弄清楚是否客觀法可以任意限定這些條件,或相反地,不論客觀法上如何規定,是否有某些條件,能使一個分子成為主觀權利的執掌者,當然這些一定是不能缺少的。”[10]這一關于法律關系主體的哲理揭示表明,法律關系中的義務主體的對應物是權利主體,權利主體最為本質的特征在于它是主觀或客觀權利的執掌者。狄驥的這一論斷雖然是就法律關系的一般理論而言的,但是,它對于行政法關系同樣具有實質意義,即使說,在行政法關系中,義務主體和權利主體是一種平等和雙向式的關系形式,當行政主體具有權利時其就是權利主體,而與它對立的另一行政法關系當事人就是義務主體,行政主體所執掌的權利也正是通過另一方當事人所為的行為而化為實質內容的。反過來說,當行政法關系中的另一方當事人為權利主體時,其執掌的權利就是通過行政主體的義務而具有實質意義的。然而,這一非常簡單的對應關系原理在我國行政法學界卻被忽視了,我們在行政法中甚至將行政主體視為惟一主體,而將行政相對人視為客體,其中行政相對人的提法就將它置于了永遠的義務主體之下。我們說,行政主體義務必須有行政法上的權利主體就是說行政主體義務實際上是另一當事人執掌的權利的物質化。當然,執掌權利者就是權利主體,它們包括在具體的行政法關系中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社會組織,還包括立法機關或者司法機關。當我們在談到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時,是就某一具體的機關而言的,因為行政主體的義務是具體的。此一要件對于我們重構行政法治體系有著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因為它體現了行政法中的一種公平、平等的價值,而不是傳統行政法治中的單方面性價值。
第四,行政主體義務的成立,要求必須有完成義務的行為能力。“行為能力是指在法律上享受和行使權利或承擔義務和責任的能力,它是具有法律人格的人或實體的特質之一。”[11]在法律關系中,不論權利主體還是義務主體都必須具有法律上的行為能力。我們知道,自然人的行為能力和組織實體的行為能力是有所不同的。自然人的行為能力一般根據不同的民事法律規定在不同的政權體制之下其表現有所不同[12],由于本文主要探討行政主體義務,因此對于自然人的行為能力問題不作細述。組織或者實體的行為能力在理論界有不同認識,一般認為,只要某種組織在成立時具有法人資格其就具有當然的行為能力。然而,在行政法中問題并不是這么簡單,行政主體是否有行為能力并不是說其行使了某種職權就具有了當然的行為能力。我們知道,行政法中除了行政機關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行使行政權的組織,如通過授權而行使權力的主體,通過接受委托而行使權力者。也就是說,在行政法中不是某一組織行使權力其就具有當然的行為能力。即便是一個行政機關,也會因越權、濫用職權等變成無行為能力的主體。 (注:行政行為主體合法以及主體具備行為能力有很多標準:一則行政主體必須是一個合格的主體,即依法成立;二則,行政主體在做出行為時,有相應的職權;三則,行政決定的形成必須符合法定程序,若違反上述三者就是缺乏行為能力的行政主體。)行政主體義務的構成要件中必須把行政主體自身的行為能力考慮進去,因為對于權利主體而言獲得實惠才是最為本質的東西,這種實惠既決定于有一個行政法上的義務主體,還決定于該義務主體具有實施義務的行為能力。如果在一個行政過程中,當事人有某種執掌權利的可能從而成為權利主體,此時,便必然有一個行政主體作為義務主體與他相對應,若他在不幸的情況下對應了一個無行為能力的行政主體,那么,他實際上是一個虛幻的權利執掌者。行政系統中,行政組織的不規范、行政過程的越權、行政職權的濫用等等都可以使義務主體無行為能力。故而,規范化的行政主體義務要求行政主體本身具有行政法上的行為能力。
三、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特征
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特征是指行政主體義務在法律表現上的獨特之處,這種獨特之處將行政主體的義務與其他組織的義務區別開來,將行政主體的義務與國家義務區別開來,將行政主體義務與行政相對人的義務區別開來,等等。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特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我們要揭示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地位就必須從其法律特征入手,只有澄清了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特征,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地位才能迎刃而解。對于行政主體義務法律特征的研究必須和行政主體的法律地位結合起來。行政主體在一國的憲法和政府組織法中都作了規定。在不同的憲政體制、不同的國家政權體系之下,行政主體的地位就有所不同。在三權分立的政權體制之下,行政主體處在與立法、司法對應的地位上,同時,它們又都對公眾負有責任,行政主體與公眾直接打交道。(注: 一般認為,行政主體是主權者和公眾之間的銜接者,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出了著名的比例中項理論,即行政機關處在一個比例中項上,它的一端是主權者,另一端則是公眾,這一理論對我們研究行政主體義務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這種政權體制之下,行政主體對立法、司法的義務是一種狀態,對公眾的義務又是一種狀態,行政主體具有多重的義務主體身份。在議行合一的政權體制之下,行政主體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對上其必須對權力機關負責,他的諸多義務既從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規則中來,又同時對權力機關負有具體的法律義務。對下其必須對行政相對人和行政事態承擔義務。同時,行政主體對作為一個集合概念的國家也承擔義務。“立法者為履行義務想出了一種聰明的辦法,他將部分教育開支和絕大部分救濟開支交由本屬于他的行政體,即省、市負擔。這樣,通過義務支出制度,國家就可以直接強制省、市履行義務保證教育救濟公用事業的正常進行。”[13]可見,行政主體義務是一個復雜的義務鏈條,筆者將通過下列概括將行政主體義務法律屬性的復雜性游離出來。
之一,管理義務與服務義務相統一的特征。行政主體履行行政管理職能這是不爭的事實,行政主體的管理職能所具有的性質我們也似乎已經澄清,即行政管理職能是行政主體的一種行政職權,大多數行政法教科書在論行政主體的職權范圍時都將行政主體的管理權放在所有權力之首。(注: 如有學者認為“行政主體指能以自己的名義實施國家行政權(表現為行政管理活動),并對行為效果承擔責任的組織。……行政主體有四個特征:第一,行政主體是一種組織,而不是個人。第二,行政主體是實施國家行政權的組織。第三,行政主體是能以自己的名義實施行政管理的組織。第四,行政主體能獨立承擔自己行為所引起的效果。”參見羅豪才行政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67)在講解行政法關系時,也將行政管理權視為行政主體在行政法關系中的一個權利。該傳統認識從表層分析上看似乎是合理的,因為行政主體必然具有管理行政事務的權威性。然而,理論界在進一步的分析中卻陷入了矛盾之中,即既認為行政管理是行政主體的一項權利或權力,又認為行政主體不可以處分這樣的權利或權力。若從權利或權力單方面性的理論來講,便陷入了矛盾之中,因為權力和權利都是可以處分的,不能處分的僅僅是義務。也就是說,行政管理是一個具有雙重性質的概念,第一方面的性質就是它是行政機關的一項權利或權力,這既可以針對行政管理事態而言,又可以針對行政管理過程中涉及的人或組織而言。第二個方面的性質是它是行政機關的一項義務,就是行政機關所履行的管理職能相對于立法機關、相對于國家、相對于法律規則是一種義務,只有把它定為義務以后,只有將管理作為義務的法律特征確定以后,我們才能順理成章地得出行政主體不能放棄行政管理職責的當然結論。與管理義務相統一的是行政主體的服務義務,我們所講的服務義務并不是就行政主體的某一個義務而言的,而是將行政主體的義務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其也具有服務的屬性。對行政主體義務的服務屬性必須深刻領會。我們知道,當國家或者行政權歸屬主體設立行政機構時,已經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因為行政主體既不為一個社會從事物質資料的生產,又不為一個社會從事精神資料的生產,它所從事的是一種特殊的活動,就是將這樣和那樣的秩序予以理順的活動,該活動對于行政權歸屬主體來講是已經或者必須帶來利益的。他們以一定的經濟成本換來行政主體的正當行為,故而,行政主體就扮演著一個服務者的角色,他所履行的義務也當然具有服務屬性。正如古羅馬《民法大全》所指出的,“宵禁官負責處理火災、入室盜竊、偷竊、搶奪、詐騙等事件,但是那些涉及品行極壞的人或者非常有名望的人的案件則由城市護民官負責處理。”[14]行政主體義務的管理性與服務性相統一的特征可以推論出諸多新的行政法理論和行政法制度,對此問題還須進一步探討。 之二,積極義務與消極義務相統一的特征。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特征中,積極義務與消極義務的劃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尤其對行政主體規范作出行政行為、不超越行政職權有極大的好處。所謂積極義務是指行政主體依法律規則規定積極而主動地實施行政行為的義務。這一義務在行政法治發達的國家是得到普遍認同的。如我們都知道,依法行政原則中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行政主體必須在履行行政職責過程中主動適用法律,[15]積極地將法律規范的規定與行政事態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不能夠象司法機關處理民事案件那樣不告不理。在現代社會中,行政主體的積極義務有了諸多新的內涵,“國家(通過行政主體——筆者)必須承擔一些積極義務;而有一些法律是國家必須頒布的。即使人們不同意這些義務的范圍,也不同意這些義務存在的基礎,所有的人也都會承認它們確實存在;而現代國家,尤其是法國,卻通過近年來頒布的法律明確承認了其中的某些義務,并組織了一些公用事業來確保這些義務的實現。首先,現代國家確實有義務為所有人免費提供最低限度的教育。行政機關強加給所有人接受最低限度教育的義務并沒有超越期限。反過來國家也有義務組成中立的、免費的初等教育。……當某個人因為生病、殘疾或年邁而導致沒有收入或不可能通過勞動獲得收入時,國家應提供生計使其得到照顧并恢復健康,或者當某人患疾時應提供生計保證其維持生活。”[13]240-241總之,隨著社會福利化水平的提高,國家通過行政主體而承擔的積極義務越來越多。與積極義務對應的是行政主體的消極義務,“積極的義務意味著法律認可,而消極的義務則意味著法律沒有認可。”[13]242就是說行政主體的消極義務是指行政主體在法律對某個事態、某個行為沒有認可的情況下行政主體不得擅自為之的義務范疇。消極義務雖然我們在行政法學理論中很難找到具體的闡釋,但是,“行政權沒有法律依據不得使人類負擔義務”,“行政權沒有法律依據不得免除他人義務”,“行政權沒有法律依據不得擅自設定權利”[15]292的法治思想無疑是對行政主體消極義務從另一角度的注解。如果說積極義務是現代服務政府理念所要求的話,那么,消極義務則是現代責任政府理念的一個體現。同時,消極義務和積極義務是行政主體義務兩個相互補充的屬性,二者處于一個統一體中,不可以人為割裂。
之三,職權義務與行為義務相統一的特征。義務的最大屬性是“拘束力”問題,正如我們前面所述,義務是對行為的一種拘束。所謂拘束力“即不得由義務人任意變更或免除之謂;故義務人必須履行其義務,否則為違反義務,受法律上之制裁,是為拘束力之效果。”[1]134行政主體義務當然也不例外,也是一種對行政主體具有拘束力的法律狀態。由此我們便可進一步推論出行政主體義務具有職權義務與行為義務相統一的法律特征。職權義務是指行政主體在履行職權過程中受到拘束作用的狀態。法律規則是通過賦予行政機關職權的形式確定行政機關在行政法中之地位的,它們的職權有一部分來自于政府組織法,還有一部分來自于部門行政管理法。在一般情況下,法律在賦予行政主體職權時便為這種職權附加了義務,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第8條規定:“國家實行職業衛生監督制度。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統一負責全國職業病防治的監督管理工作。國務院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負責職業病防治的有關監督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職業病防治的監督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負責職業病防治的有關監督管理工作。”該條是對行政主體的一個賦權條款,而該法在隨后的法律責任部分附加了這一職權行使的義務,即不當履行該職權的要承擔紀律處分等義務。職權義務是從較為宏觀的角度出發的,它常常使職權與法律責任相對應。所謂行為義務就是行政主體在作出某種行政行為時受到拘束的狀態。行政行為中的作為和不作為都必須受到拘束,這樣的拘束條款一般反映在專門調整行政行為的行政法規范之中,如行政程序法等。《澳門行政程序法》第57條規定:“快捷之義務:行政機關應采取措施,使程序能迅速及有效進行,因而應拒絕作出及避免出現一切無關或拖延程序進行之情事,以及應命令與促成一切對程序之繼續進行及對作出公正與適時之決定屬必須之情事。”[16]行政主體的職權義務與行為義務在發生拘束作用方面其對象是大不相同的,前者是對職權范圍的約束,后者是對行為過程的約束。但是,二者在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意義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二者的統一性為現代行政法規范的制定提出了課題,即我們究竟制定以規制職權為核心的部門法體系,還是制定以規制行為為核心的程序法體系,還是我們能夠選擇一個折中的方法進路有機地將二者統一在一起。
之四,法規義務與契約義務相統一的特征。行政主體的法規義務是指由法律規則、政府規章等派生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將我國法律規范體系作了有序的排列,由憲法而法律,由法律而行政法規,由行政法規而地方性法規,由地方性法規而政府規章等,這樣的排列第一次使我國法律體系有了一個層級結構。每一個層級的規則都可以為行政主體設定相關的義務,我們將這些規則所設定的義務統稱為法規義務。言下之意這些義務從行政法規則中產生,以法律規范的形式表現出來。應當說明的是法規義務有時是明確的,有時是隱含的。例如,《上海市內河航道管理條例》第9條規定:“本市內河航道規則由市交通局負責組織編制,在聽取有關部門和有關區(縣)人民政府的意見,經市規劃行政管理部門綜合平衡并報市人民政府批準后,納入市總體規劃,由市交通局報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備案。”該條是一個賦權條款,但隱含了諸多義務。由于法律規范有層級之分,因此,行政主體義務的規范亦應依法規層級依次確定。(注:憲法設定的義務高于法律設定的義務,法律設定的義務高于行政法規設定的義務,行政法規設定的義務高于地方性法規和規章設定的義務。行政主體在履行其義務時必須考慮法律規范的層級,不能繞開高層級規范設定的義務而去履行低層級規范的義務,尤其當低層級義務與高層級義務沖突時更應當選擇上位規范的義務。)與法規義務對應的是行政主體的契約義務,此一義務在現代社會中是絕對不能被忽視的,這既是由公法受私法理念制約的客觀趨勢決定的,又是由公權與私權對等化的狀況決定的。行政主體隨著社會的發展行使行政職權的方式也在不斷變化,以契約的方式行使行政權就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近年來我國的農業承包合同、工程建設承攬合同等就代替了傳統的行政單方裁決手段。2002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明文規定:“政府采購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其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就是對契約義務的肯定。在政府采購和其他的行政合同行為中,合同規定的權利義務是雙向的,如《政府采購法》第43條規定:“政府采購合同適用合同法。采購人和供應商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應當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則以合同方式規定。”就是說在行政過程中,行政主體一旦與某個個人或組織簽訂了契約,契約的義務就對它有約束作用。應當指出,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受計劃經濟和政府管理權威的影響并沒有將行政主體的義務與契約義務結合起來。依筆者看,契約義務與法規義務具有同等意義的重要性,因為它是政府取信于民之根本。
四、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意義
“義務人的行為也可能是權利客體。在許多法律關系中,有權人的法律支配正是指向義務人的行為。整個債權法方面都是如此,不論因合同而產生的債(例如勞動合同、包工合同、買賣合同),還是因其他根據而產生的債(例如致成損害,在這種情況下,權利客體是致成損害的人的行為,即交納一定的款項,以及實施其他賠償所致成的損害的行為),都是如此。義務人的行為在其他許多情況下也是權利客體(例如審判員要求證人作出一定的行為的權利,警察機關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科處罰金的權利)。”[17]由此可見,主體的義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法理學問題,其在法律體系和法律運作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民事法律中是如此,在行政法律中當然也不能例外。行政主體的法律意義,主要反映行政法運作過程中諸主體之間的關系形式,(注: “在權利——義務關系中,主要是雙方身份有彼此相對:我要求——但必須;在享有特權——沒有權利關系中,為我可以——你不能;在享有權利承擔責任的關系中,為我能夠——你必須接受;在享有豁免權——無資格關系中,為我能泰然免受懲罰——你不能。”這是《牛津法律大辭典》對權利與義務形式的揭示,反過來說行政主體義務決定了上列關系形式的存在。參見[英]戴維.M.沃克:牛津法律大辭典[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774)同時,它還能夠決定行政法中其他一些重要問題。遺憾的是我國行政法學界對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意義沒有給予必要重視,導致我國行政法更像是一種政府行政命令構成的單行規則,而不像是一個具有嚴格法性價值的部門法,我們在行政法中的概念系統、規則構成等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如我們在揭示行政程序法的規范體系時就有諸多概念與行政管理學中的概念無法區分,如行政決定、行政計劃、行政指導、行政規范等等。也就是說,行政法的概念系統和規范體系還沒有進入到“法”的主流中來。換句話說,在今后一段時間內,我國行政法的理論應進入“法”的主流之中,而不是進入“行政”的主流之中。若要進入“法”的主流之中,我們就必須以“法”眼認識行政法,其中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意義,或者對行政主體義務在法律中的地位的確定就顯得不可或缺。筆者認為行政主體義務的法律意義應當從下列方面闡釋。
(一)行政主體義務對行政職權定“責”的法律意義。行政職權是由行政主體享有的權力范疇,行政主體通過行政職權完成對行政事態的管理。在一國的憲法和政府組織法中對行政主體的職權作出較為細致的規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對國務院的職權作了詳細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對地方行政機關的職權作了列舉規定。當憲法和法律對行政主體的職權作出規定時并不同時規定這些職權的法律責任,一般將法律責任規定在其他法律規范中,且每一種法律責任也都不針對具體的職權而規定。這樣便在行政權行使過程中形成了權責不對等的狀況。所謂權責不對等就是享有權力相對較大的行政主體承擔的法律責任相對較小,而職權相對較小的行政主體其承擔的法律責任則相對較大[18]。法律責任在理論上有兩種認識,一種認識是行為主體對其行為后果應當承擔的法律報應義務,如某一行政主體由于錯誤地行使了行政職權導致國家財產受損,此時,該一行政主體便應當承擔賠償或處分的責任。另一種認識是行為主體由于從法律上取得了權利,便必須根據這些權利忠實地履行職責的義務,必須把自己份內之事做好的義務。正如《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所解釋的:“責任最通常、最直接的含義是指與某個特定的職位或機構相連的職責,意味著那些公職人員因自己所擔任的職務而必須履行一定的工作和職能。責任通常意味著那些公職人員應當向其他人員或機構承擔履行一定職責的責任或義務,這些人可以要求他們作出解釋。而這些人自己又要向另外的人或人們負責。”[19]在后一種意義上責任與責任政府基本上是同一意義的概念。我們認為,行政主體的責任包含了上述兩種含義。由于在一國的行政法規范中常常不能夠也沒有必要對每一種行政職權都確定具體的對應責任,這便使行政職權和行政責任經常性的發生分離,權與責的不對等也由此而來。鑒于這種情況,近年來人們試圖尋找一種方法,通過這樣的方法將行政主體的職權與責任對應起來,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靈丹妙藥能把二者絕對地對應起來。依筆者看,我們可以通過行政主體義務將行政職權與行政責任對應起來,即我們在賦予行政主體職權的同時,以一種法律上的義務機制使每一個行政職權都有相應的行為上的約束。正如前面我們所講的義務是一個范疇概念,通過這個范疇概念,以機制化的約束力給職權定“責”,這就是行政主體義務第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意義。
(二)行政主體義務對行政法關系定“性”的法律意義。我國行政法學界關于行政法關系有一個似乎達成共識的論點,即行政法關系的特性是一種不對等關系,在該不對等關系中行政主體處于主導地位,而行政相對人處于服從地位。“行政主體參加行政法律關系,成為行政法主體是為了實現國家的行政職能,維護和分配公共利益。行政主體同相對人的關系,即使在當代法治社會,仍是一種權力和服從關系。這就是說,行政主體享有國家賦予的、以國家強制力為保障的行政權,其意思表示具有先定力。”[20]這是對行政法關系主體地位不對等性的一個描述。誠然,行政主體在行政權行使中必須享有行政權威,必須具有一定的獨立意志。然而,這種獨立意志究竟在什么樣的范圍內才能存在,在符合什么樣的條件時才能成立卻是理論界沒有給出答案或者給出了一個錯誤答案的問題。至少在行政法關系中行政主體的這種優越地位是不存在的。對此我們便可以通過行政主體義務的理論進行證明。行政主體負有法律上的義務這已經在上面得到論證,而義務與權利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即一方有義務另一方則有權利。在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形成的行政法關系中,行政相對人的權利就是行政主體的義務,此時,行政相對人就具有法律上的優越地位,如依《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行政主體在對行政相對人罰款時,行政相對人享有一個要求索取合法票證的權利,行政主體承擔提供合法票證的義務;那么,在票證索取的這一行政法關系中,行政相對人就享有優越地位,即如果行政主體不提供合法票證,行政相對人便有進一步的不繳納罰款的權利。由此便可以看出,行政相對人在行政法關系中并不是完全被支配的,并不是一個純粹的義務主體。也就是說,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在行政法關系中的地位要根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而定。由于傳統行政法學理論將行政主體視為權利主體,從這一錯誤的前提便得出了行政法關系不對等的錯誤結論。進而論之,行政主體義務對于正確為行政法關系定“性”具有極其重要的法律意義。在行政主體義務被確定以后,我們便可以毫不猶豫地說,行政法關系并沒有超越一般法律關系內涵的獨特性,在一般法律關系中由于權利義務將各主體連結在一起,因此,各主體的地位也是平等的。那么,行政法關系亦是通過主體的權利和義務連結的,因此參加行政法關系各主體的地位也當然是平等的(注: 權利和義務關系有“應然”與“實然”之分,“實然”指的是某種客觀情況,即社會現實中已存在的關系,而“應然”則是指法律關系中的理想模式。我國行政法學界認為行政法關系具有不平等性實際上是把行政過程中行政主體的“實然”權利“應然”化了。就是從行政法治理論看,行政法關系不應當是單方面性的。)。
(三)行政主體義務對行政行為定“量”的法律意義。行政行為理論在我國行政法學理論中是一個較為成熟的理論,同時我們應當看到行政行為理論的成熟性僅僅反映在行政行為的定性分析中。所謂定性分析就是從法律屬性上確定行政行為的內容,如我們把行政行為分成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內部行政行為和外部行政行為、原始行政行為和改變后的行政行為等等。定性分析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具有同等意義的價值[21]。所謂定量分析就是給行政行為盡可能作出量化指標,使每一種行政行為都能夠通過數字來說明,使每一個行政過程的單一行為都有確定的數量標準。由于我國行政行為理論中量化的淺薄,便導致我國行政法治實踐中量化之不足,如一個行政機關在作出某一行政行為時怎樣才能使該行為與行政事態、與行政相對人的權利義務達到最大化的對應,沒有一套行政法制度,甚至沒有一個行政法規則對這樣的問題作出規定。筆者認為,在目前情況下行政主體義務是為行政行為定量的一個不可取代的路徑。“義務的存在或確認通常意味著對他人權利的確認,權利人有權要求他人履行與他有關的義務或有權取得因他人不履行而造成的損失賠償,即產生義務受益人。”[11]277行政主體義務在有些情況下對應行政相對人的權利,行政相對人權利實現的滿意程度就決定了這一行政行為中的量。如法國1979年制定的《說明行政行為理由及改善行政機關與公眾關系法》第5條規定:“在明示決定應說明理由的情況下,做出的默示決定未說明理由的,并不構成違法。但是,在行政訴訟期限內,應關系人的請求,應將默示駁回的決定的理由在請求后的1個月內告知關系人。在此情況下,對該默示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的期限延長至理由通知之日起計2個月后屆滿。”[16]569這一規定將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與行政相對人權利的要求緊密結合起來,而相對人的權利要求就是行政主體的義務,就是說行政主體的義務決定了行政行為的量。行政主體義務在另一些情況下不可能對應權力機關、司法機關等的權利,這些機關對權利的滿意程度便決定了行政行為的量。總之,通過行政主體義務我們可以尋找出一個有效規范行政行為的方法,尋找出一個使行政行為能夠量化的有效途徑,而行政行為的量化是行政法治水平的一個反映。
(四)行政主體義務對行政救濟定“度”的法律意義。行政救濟是一整套行政救濟規則和行政救濟制度的總稱。目前我國行政救濟有3個法律進行調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此3個法律規范的外形是完整的,但是,我國行政救濟制度近年來卻遇到了這樣那樣的麻煩,尤其我國加入WTO以后,行政救濟究竟朝著什么樣的方向發展是人們一直關心的問題。如就行政復議而言,有強化行政復議的說法,也有將行政復議予以弱化的說法。關于行政訴訟討論最多的是受案范圍的擴大問題,而國家賠償中主要是精神賠償國家是否應承擔賠償責任的問題等等。筆者認為,上列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澄清必須建立在一個強有力的理論基礎之上。其中行政主體義務的理論就是一個能夠解決若干救濟制度和救濟規則的問題。行政救濟從實質上看是對行政主體義務履行狀況所進行的行政審查和司法審查,而目前我國建立的行政救濟制度并不是從行政主體義務履行的角度出發的,而是從行政主體職權行使的角度出發的。例如,抽象行政行為沒有被納入司法審查的范疇,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考慮到抽象行政行為是行政主體行為中最為重要、具有普遍意義的行為,似乎認為這樣的行為被司法審查的話,行政過程就無法完成等等(注:目前我國將抽象行政行為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的制度設計已經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發達國家以及世貿組織對此已經提出了要求,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中已經承諾將政府規章和行政措施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可見我國已經接受了以行政主體義務確定行政救濟的“度”,而不是以行政行為的性質確定司法審查的范圍。)。如果我們從行政主體義務履行的情況出發,我們將會建立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救濟制度,如我們不是以行為的性質,即不管是抽象行為還是具體行為,而是以義務履行的狀態確立救濟規則,只要行政主體不當履行義務或違法履行義務,或者行政主體沒有履行義務,我們就可以將這些沒有履行義務的主體及其行政過程納入司法審查之中,如果是這樣的話,行政救濟的“度”則與現在完全不同。
參考文獻:
[1]涂懷瑩.行政法原理[M].臺北: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3:134.
[2]朱貽庭.倫理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224.
[3]應松年.行政法學新論[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90.
[4]廖晃龍.新編中國行政法原理[M].大連:大連海運出版社,1990:40.
[5]張正釗,韓大元.比較行政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84.
[6]和田英夫.現代行政法[M].倪健民,潘世圣,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56.
[7]蕭榕.世界著名法典選編(憲法卷)[M].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138.
[8]漢斯.凱爾森.法律與國家[G]//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652.
[9]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50.
[10]狄驥.憲法論[G]//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629.
[11]戴維.M.沃克.牛津法律大辭典[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134.
[12]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102.
[13]萊昂?狄驥.憲法學教程[M].王文利,等,譯.沈陽:遼海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242.
[14]桑德羅.斯奇巴尼.公法[M].張禮洪,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102.
[15]王云五.云五社會科學大辭典(行政卷)[M].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292.
[16]應松年.外國行政程序法匯編[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591.
[17]羅馬什金.國家和法的理論[M].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63:480.
[18]關保英.權責對等的行政法控制研究[J].政治與法律,2002,(3):17-22.
[19]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701.
[20]葉必豐.行政法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31.
[21]關保英.論行政相對人權利的平等保護[J].中國法學,2002,(3):16-25.
The Duty of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 Perspective of Law
GUAN Bao-y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China)
Abstract:
The duty of administration agencies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laws and government in accordance with a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law, as such, its status is equal to “right” and “power” in administrative law. However, scholars in Chinas administrative law circles traditionally focus only on “right” and “power” while “duty” is ignored and unfortunately no scientific assessment has been made of it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us, the present paper holds it necessary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legal features, and legal meanings of the duty of administrative law. Formation of the duty must be based on laws or authorizations, i.e. the specific duties and agencies provided in administrative law, and the competence to perform the duties. The duty of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has its peculiar features in law that demonstrate it as a complex duty chain, an integ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 duties, a combination of active and negative duties, a union of functional and behavioral duties, and a coordination of statutory and contractual du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w, th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 in administrative law and the “quantum” of administrative behaviors are all determined by the duty of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agencies; duty; legal meaning
本文責任編輯:汪太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