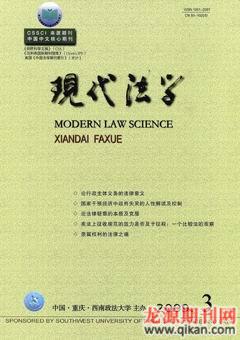有利被告的中國歷史話語
邢馨宇
摘要:在浩瀚的中國法律史籍中,不乏有利被告的話語,“罪疑惟輕”、“舉重明輕”、“處重為輕從輕法”與“格輕聽依輕法”等便是其典型代表。這些歷史話語或從程序或從實體的角度,表達了對被告有利的選擇,而且大都因源遠流長與對后世影響深遠而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組成部分。但是,關于有利被告的這些中國歷史話語,與西方有利被告的話語“貌合”而“神離”,不宜相提并論。在當下中國培植有利被告的理念,首先必需對深植于儒家中庸文化之中的有利被告的中國歷史話語予以清理。
關鍵詞: 罪疑惟輕;舉重明輕;處重為輕從輕法;格輕聽依輕法
中圖分類號:DF02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有利被告論開始受到中國學界的關注。然而,一方面,有利被告究竟僅僅適用于刑事程序法,還是可以同時適用于刑事實體法,學界爭論頗大;(注:邱興隆、時延安等主張,有利被告是同時適用于程序刑法與實體刑法的一個刑法理念。(參見:邱興隆.刑法理性導論——刑罰的正當性原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邱興隆.有利被告論探究——以實體刑法為視角[J]中國法學,2004,(6);時延安.試論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則[J].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3,(1).)張兆松等認為,有利被告只適用于刑事訴訟語境之中,而不適用于實體刑法的語境中。(張兆松.“刑法存疑時有利于被告原則”質疑——兼與邱興隆教授商榷[J].人民檢察,2005,(6)(上).))另一方面,基于有利被告系“存疑即有利被告”這一西方法諺的簡稱,中國學界曾有人認為此論乃“舶來品”,未必符合中國國情,因而對其在中國的貫徹持懷疑乃至否定態度。(注:參見:黃貽祥.應當批判辯護人的有利被告論[J].法學,1958(3).)因此,就相關的中國法律史料做一梳理,從歷史的角度弄清有利被告是否有其生存的中國土壤等問題,以澄清中國學界在有利被告論上的有關爭議,委實成了一個有待研究的課題。
一、“罪疑惟輕”
在中國歷史上,直至“民國”以前,雖無有利被告的提法,但有利被告的精神卻以特有的中國話語存在于中國歷代法律文獻與著作中。而且,歷史的脈絡清晰地顯示,早在夏、周時期,作為有利被告思想之體現的“罪疑惟輕”理念,即已成為司法的指導思想,完成了由提出到定制的演變。
據《尚書》記載,2 300年前,皋陶即在舜帝的御前會議上提出:“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注:《尚書?大禹謨》)關于“罪疑惟輕”的內涵,存在兩種解說。一說以胡適為代表,將其界定為“證據不夠,只宜從輕發落”[1]。在這里,“罪疑”被理解為有關犯罪的事實存在疑問,即難以認定。另一說源于宋代理學家蔡沈的注解,他認為,“罪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注:《書經集傳》)意即定罪之后,如果還有可以重判也可以輕判的疑問,就從輕量刑。《漢語成語詞典》沿用蔡沈的解釋,認為“罪疑惟輕”是指“罪行輕重有可疑之處,只應從輕判處”。(注:《漢語成語詞典》)至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通說認為,其意為寧可違反成規定法,也不能處死無辜之人。
盡管限于史料,無從考證在舜帝時代“罪疑惟輕”是否被貫徹于具體的法律制度之中,但從周代的“金作贖刑”制度中,則依稀可見“罪疑惟輕”被開始制度化。《周禮?秋官?職金》記載:“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注:《周禮?秋官?職金》)鄭玄注釋說:“貨,泉布也;罰,罰贖也。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值也,故曰金作贖刑。”(注:《周禮注疏?卷三十六》)賈彥之則注曰:“掌受士之金罰者,謂斷獄訟者有疑,即使出贖。既言金罰,又云貨罰者,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值。”(注:《周禮注疏?卷三十六》)綜合二人的注釋,可知周代的“金作贖刑”制度,是指在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存在疑問時,只交納“金”或“貨”,而不判處人身刑。因此,“金作贖刑”作為處理疑罪的一種手段,在周代已被實際運用,這標志著有利被告之制度化的萌芽。
不僅如此,據《呂刑》記載,“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即西周時,本承夏代的贖刑制度,制訂了《呂刑》,確立了“疑赦”制度。作為貫徹“罪疑惟輕”思想的配套設施,“疑赦”制度的問世標志著有利被告已成定制。所謂“疑赦”,是指“犯五刑之罪而有疑的,易科五罰”,即“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注:《尚書?周書?呂刑》)墨、劓、剕、宮、大辟系周代的五種重刑,“疑赦”即有疑從寬。凡是犯了五刑之罪,而事有可疑不能定罪的,即改判罰鍰。在這里,罰鍰并非實體意義上的刑罰,即不等于是最終的處理結果,而僅僅是一種變通措施。基于“疑赦”而罰鍰之后,仍然應“閱實其罪”,即應繼續查實犯罪,因此,這里所謂的罰鍰,并非今天作為刑罰方法的罰金,而更類似于今天的保釋金。“疑赦”亦非今天的赦免或者無罪釋放,實為交納一定金錢而保釋,因而類似于今天的取保候審。可見,“疑赦”作為處理疑罪的手段在周代的問世,意味著“罪疑惟輕”作為定制得到了立法與司法的認可。自周以后,“罪疑惟輕”得到了思想與制度層面的雙重承續,以至于成了中國法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根據史料的記載,“罪疑惟輕”不但自《左傳》起即被上升到了德政與仁政的高度,所謂“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注:《左傳》)而且,它還作為一項指導原則為歷代執法者所自覺遵循,甚至還作為定制而被規定于漢代以后的各代律令之中。
《冊府元龜》載曰:“漢高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系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就是說,漢高帝時,本承“罪疑惟輕”的宗旨,專門就疑罪規定了逐級呈報制度。這一制度,在漢武帝時得到了繼承。“武帝征和四年九月詔曰:諸獄疑者,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后。元年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后不當,讞者不為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注:《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一?帝王部?慎罰夫》)正是由于為人君者如此恪守“罪疑惟輕”的古訓,作為司法官員的為人臣者便更視“罪疑惟輕”為信條。所以,才有了“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注:《漢書?于定國傳》)的記載,使得“罪疑從輕”作為“罪疑惟輕”的同義詞,一并成為漢語成語。(注:《漢語成語詞典》)可見,在漢代,“罪疑惟輕”作為司法原則得到了推崇。
漢以后,南朝的陳雖系曇花一現的“短命王朝”,但這并不妨礙它對“罪疑惟輕”的重視。據《陳書》記載,陳高祖與陳世祖均將“罪疑惟輕”作為刑事司法的基本策略。《陳書?本紀第二?高祖下》載稱,陳高祖曾在永定元年三月甲午發布詔曰:“罰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輕,布在方策”。而《陳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二十七?儒林》亦載:世祖即位后,與眾臣討論立法問題。都官尚書周弘正議曰:“夫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圣王,垂此明法”。
至唐代,“罪疑惟輕”理念得到了空前的重視。從“罪疑惟輕”的理念出發,《唐律》規定:“諸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關于“疑罪”,唐律的界定是:“疑,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無證見;或傍有聞證,事非疑似之類”。就疑罪的處理,唐律還規定了專門的處置程序:“即疑獄,法官執見不同者,得為異議,議不得過三”。就此,《唐律疏儀》作了進一步的解釋:“‘疑罪,謂事有疑似,處斷難明。‘各依所犯,以贖論,謂依所疑之罪,用贖法收贖”。就《唐律》關于疑罪的界定,《唐律疏儀》的解釋如下:所謂“虛實之證等”,是指“八品以下及庶人,一人證虛,一人證實,二人以上,虛實之證其數各等,或七品以上,各據眾證定罪,亦各虛實之數等”;所謂“是非之理均”,是指“有是處,亦有非處,其理各均”;所謂“事涉疑似”,是指“贓狀涉于疑似,傍無證見三人;或傍有聞見三人,其事全非疑似”;之所以以“之類”概稱之,是因為“或行跡是,狀驗非;或聞證同,情理異。疑狀既廣,不可補論,故云‘之類”;所謂“即疑獄”,是指“獄有所疑,法官執見不同,各申己見,‘得為異議,聽作異同”;所謂“議不過三”,是指“丞相以下,通判者五人,大理卿以下五人,如此同判者多,不可各為異議,故云‘議不得過三”[2]。綜觀這些規定可以發現,《唐律》是將因證據不足而導致犯罪事實不清的案件作為疑罪。如果僅以此為據,胡適關于“罪疑惟輕”的解說是無懈可擊的。而《唐律》規定的對于疑罪的處置方式即適用贖法,自然是指不處以實質性的刑罰,而只處以贖金。但因《唐律》并未象《呂刑》一樣做出“閱實其罪”的規定,贖金究竟是對疑罪的一種處理結果,還是僅僅作為一種保釋金,難以下定論。
基于立法上對“罪疑惟輕”的認可,在唐代,“罪疑惟輕”作為一項司法原則得到了遵循。因此,在唐代,以“罪疑惟輕”作為根據的判例俯拾即是,這可以從一個側面印證“罪疑惟輕”在唐代受到了非凡的重視。例如,柳宗元就曾為一疑案上奏。被告莫誠為救其兄莫蕩,以竹子刺擊攻擊其兄的莫果的右臂,莫果在十一日死亡。按當時的律條,莫誠當以殺人論處。柳宗元奏曰:“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手方迫于深哀,周身不遑于遠慮。”他引證“罪疑惟輕”說,提出對莫誠予以免于死刑的處罰。(注:《四庫全書?集部?柳宗元集?卷三十九?奏狀》)柳宗元的這一奏折最終是否獲允,難以考證,但他以“罪疑惟輕”作為定罪量刑的指導思想,從此折中可見一斑。又如,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華州刺史蕭齡之受賄事發,唐高宗令大臣討論治罪。大多數人認為應該判處蕭齡之死刑,時任御史大夫的唐臨以“罪疑惟輕”為據,提出異議,主張對蕭齡之可以不處死刑。唐高宗采納了唐臨的意見,蕭齡之得以免死。由此可見,“罪疑惟輕”在唐代已成為君臣共守的至理。同時,鑒于上述兩案并非證據不足、事實不清,而處理結果也不是適用贖法,但都是援引“罪疑惟輕”對其做出的寬大處理,因此,可以進一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唐代,“罪疑惟輕”的意義已遠遠越出了“罪疑從贖”的立法雷池,而被擴展成為一條具有普適性的原情寬大處置的司法原則。
較之唐代,“罪疑惟輕”理念的影響在宋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就制度層面而言,《宋刑統》在《疑獄》篇中幾乎一字不差地沿襲了《唐律》關于疑罪的認定、處置程序與處置結果的規定,從而繼承了“疑罪從贖”的處置原則。
北宋大文豪蘇軾曾撰文《刑賞忠厚之至論》就“罪疑惟輕”感言道:“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3]“罪疑惟輕”在宋代的影響之深入人心,由此可窺一斑。
即使是以主張刑罰嚴厲而著稱的南宋理學家朱熹,也對“罪疑惟輕”持不排斥態度。他認為,“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他所反對的僅僅是“凡罪皆可從輕,而凡功皆可從重”[4]。朱熹的高足、同為南宋理學家的蔡沈就“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闡釋道:“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于非辜,不殺之恐失于輕縱。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圣人所不能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注:《書經集傳》)
明代法律雖無與唐、宋法律相匹比的“罪疑惟輕”制度,但這不等于說“罪疑惟輕”的理念在明代沒有得到重視。據《明太祖寶訓》記載,洪武十四年九月辛丑,明太祖敕刑部尚書胡禎等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于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輕,四兇之罪,止于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憫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為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真犯者決之如律,其余雜犯死罪,皆減死論。”(注:《明太祖寶訓?卷五?求賢》)由此可見,“罪疑惟輕”被明太祖奉為刑事司法的原則。正是如此,在《斷獄》篇之《辯明冤枉條例》與《辯明冤枉新頒條例》中,《大明律》就疑罪的處理做出了相應的規定。對于確有冤枉及情有可矜疑者,應奏請定奪;對于“各犯情可矜疑的,都饒死,發邊衛充軍。篤疾的,放了”[5]。盡管根據《明律》的這一規定,對于罪疑的死囚不再象宋代法律一樣沿襲周代的規定適用贖法,而適用充軍,但相對于死刑,充軍是生刑,體現了“惟輕”與“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基本精神,因而也不失為對“罪疑惟輕”的遵循。正因為如此,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黃宗羲才發出了“罪疑惟輕,則冥途有重返之魄”(注:《明司馬澹若張公傳》)的感嘆。
需要指出的是,《大明律》將矜、疑相組合,將“其情可憐”與“其罪可疑”(注:清代的方苞在《獄中雜記》里提到:“其情可憐,其罪可疑,秋審入矜疑。”)兩種情由相提并論,使萌發于宋代司法實踐中的將“罪疑惟輕”的適用范圍由“疑罪”擴展至“矜罪”的做法,得到了立法上的確認,從而使“罪疑惟輕”的內涵與外延已遠遠超出了胡適立足于程序的角度給其所作的界定。如果說這里的“疑罪”尚可解釋為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的話,所謂“矜罪”則是在證據充分、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對被告人所作出的犯罪情有可原的綜合評價。它構成法官量刑時所考慮的一個事由,相當于今天所說的酌定從寬處罰的情節,因而不再屬于程序問題,而是實體問題。
“罪疑惟輕”作為漢族法律文化的結晶,而與元代一樣,清朝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朝代,因此,誠如元律對“罪疑惟輕”的忽視一樣,在清代立法中,“罪疑惟輕”的理念也不如其他朝代的立法貫徹得那樣明確與具體。但是,從有關史料的記載來看,低估“罪疑惟輕”對清代司法產生的影響無疑是武斷的。至少在清代三大杰出統治者康熙、雍正與乾隆當政時期,“罪疑惟輕”的原則受到了重視。
康熙對“罪疑惟輕”的真義頗有見地,他指出:“《書》云罪疑惟輕,以其罪之情由有可疑之處而輕之也。若無可疑,則以公平為貴。”(注:《康熙起居注》)康熙不但如此說,而且也是如此做的。康熙二十年,理藩院處理了這樣一個案件:盜馬罪犯阿畢大等五人,被依律判處斬立決,家產妻子,則給失馬之人為奴。理藩院上報案情后,康熙指出:“朕念人命關系重大,每于無可寬貸之中,示以法外得生之路。《書》所謂罪疑惟輕也。阿畢大等,家產妻子,既給失馬之人,若本犯免死,給與為奴,則失馬者,得人役使,于法未為不當。嗣后著為定例”。(注:《清實錄?圣祖實錄?卷九十八》)耐人尋味的是,康熙在解釋“罪疑惟輕”時,所持的是嚴格的文理解釋立場,將“惟輕”的前提限定于“其罪之情由有可疑之處”,但在處理阿畢大盜馬案時,他對“罪疑惟輕”卻是適用的擴大解釋,即把“惟輕”的前提擴大到了“其罪有可矜的事由”。這一方面說明,前述萌發于唐代司法實踐、定制于明朝立法的將“罪疑惟輕”擴展為“矜疑從寬”的做法,得到了康熙的繼承;而另一方面則顯示,“罪疑惟輕”實際上已成為統治者的一種司法策略,即將其作為在量刑時法外用刑、寬大處理的理論根據。
雍正在其親著的《大義覺迷錄》與《圣諭廣訓》中兩度談論“罪疑惟輕”問題。在《大義覺迷錄》中,他聲稱:“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婦人之仁,弛三尺之法。但罪疑惟輕,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時疏忽,致有絲毫屈枉之情,不但重辟為然,即笞杖之刑,亦不肯加于無罪者,每日誠飭法司,及各省官吏等,以欽恤平允為先務”,(注:《清史資料?第四輯》)以此表白其基于“罪疑惟輕”的理念而慎重處理案件的心跡。而在《圣諭廣訓》中,他又指出:“康熙十五年定例,凡窩逃之正犯流徙尚陽堡,兩鄰十家長罪止杖徙。此皆我皇帝矜惜愚民,罪疑惟輕,故改從寬典也”[6],這說明“罪疑惟輕”早在康熙時期即已成為立法的指南。具有強烈對比意義的是,在《大義覺迷錄》中,雍正引用“罪疑惟輕”說明對疑罪所應有的謹慎態度;而在《圣諭廣訓》中,他引證“罪疑惟輕”所稱頌的是先帝矜惜之恩。可見,在雍正看來,“罪疑惟輕”不單適用于解決“疑罪”,而且也適用于處置“矜罪”。
乾隆根據“罪疑惟輕”處理案件的事例,文獻上也不乏記載。《嘯亭雜錄》真實記錄了乾隆著眼于“罪疑惟輕”而親歷的一個案件。乾隆南巡時,遇一鄉人圍觀,侍衛持刀驅趕之,而鄉人拒不退避。一尉官用梃杖擊打其腦袋,鄉人負痛邊叫邊跑,驚動了乾隆。乾隆將鄉人以刺客對待,命將其綁縛交順天府尹,嚴鞫論擬。府尹某廉得其情,知鄉人實非刺客,且恐興大獄,即具摺復奏,稱鄉人素患瘋疾,有鄰右切結可證。罪疑惟輕,且無例可援,鄉人某某,著永遠監禁,遇赦不赦。地方官疏于防范,著交部議處是否有當。乾隆照準。(注:《嘯亭雜錄》卷6《癸酉之變》)無獨有偶,《清史稿?李侍堯傳》所載乾隆對李侍堯受賄案的從輕發落,也是以“罪疑惟輕”為根據的。身為大學士、歷任總督的李侍堯受賄案發,乾隆驚呼“朕夢想所不到”。于是,對李奪官,逮詣京師。和珅等奏擬斬監候,奪爵以授其弟奉堯。又下大學士九卿議,改斬決。乾隆欲對其從寬發落,遂采納江蘇巡撫閔鶚元的意見下詔稱:“罪疑惟輕,朕不為已甚”,并對李改處斬監候。(注:《二十四史?清史稿?列傳?李侍堯傳》)這兩則案例,結果均為從寬處理,乾隆都是將“罪疑惟輕”作為其處理根據的。然而,實際上,這兩個案件的證據與事實均不存在疑問,嚴格說來,均不屬于疑罪。乾隆引“罪疑惟輕”作為從寬處理的根據,實際上也是將“罪疑惟輕”擴大解釋為包括“矜罪從寬”。這進一步說明,“罪疑惟輕”在清代作為一種司法策略得到了推崇。
二、“舉重以明輕”
如果說“罪疑惟輕”偏重的是程序上的有利被告,那么,形成時間相對較晚的作為刑法解釋與適用原則的“舉重以明輕”則偏重的是實體上的有利被告。刑法的解釋與適用屬于實體刑法所要解決的問題,而與程序刑法關系不大。
作為解釋與適用法律的一種方法,類推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之,至少可以回溯到周代的《呂刑》關于“上下比罪”的規定。(注:《尚書?周書?呂刑?第二十九》:“上下比罪,無僣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經由漢代的“決事比”,到晉代的“若無正文,依名例斷之”,類推在唐代以前就已成立法定制。但是,唐代以前的類推總的來說是以“入人之罪”為目的,即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時,比照法律有明文規定的罪名定罪科刑。因此,在實質上,唐代以前的類推本身即是在定罪上的一種不利被告的選擇。直至唐代,類推才發生了有利被告的裂變。(注:立法在類推問題上對有利被告的認可,當以“舉重以明輕”原則的提出為標志。而關于這一原則的起始,通說認為源于《唐律》的規定。但是,根據《通典》、《唐會要》、《舊唐書》與《新唐書》所載趙冬曦的說法,該原則雖得到了《唐律》的確認,但它并非形成于唐代,而是早在唐之前的隋代即已成型,《唐律》只不過是沿襲了《隋律》的這一規定。上述四書均載曰:“神龍元年正月,趙冬曦上書曰:‘臣聞夫今之律者,昔乃有千余條。近有隋之奸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 因此,根據趙冬曦的說法,“舉重以明輕”與“舉輕以明重”應自隋代始見于律。但因隋代法律典籍缺失,這一說法難以證實或證偽,相應地,關于“舉重以明輕”與“舉輕以明重”始見于《唐律》的通說似更為穩妥。(參見:《通典?刑法典?第一百六十七》;《唐會要?卷三十九?議刑輕重》;《舊唐書?列傳第四十九》;《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三?列傳第一百二十五?儒學下》))
《唐律》在《名例律》中設“斷罪無正條”之專條,規定了類推定罪制度,確立了“舉重以明輕”與“舉輕以明重”的限制類推原則。該條規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2]134。意思是說,在認定犯罪時,如遇法律條文中沒有相應的明文規定,應分出罪與入罪兩種情況做出不同處置:對于出罪,應舉重以明輕,即如嚴重的情形依法不認定為犯罪或者可以減輕處罰,則較之為輕的情形,即使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無罪或減輕處罰,也應認定為無罪或減輕處罰;而對于入罪,應舉輕以明重,即如依據法律,相對較輕的情形尚且被規定為犯罪或者加重處罰,那么,較之為重的情形也應認定為犯罪或者加重處罰。
盡管“舉輕以明重”本身也構成對類推的限制,即它將較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情形為輕的情形排除在類推定罪的犯罪之外,但是,鑒于“舉輕以
明重”歸根到底是將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情形解釋為犯罪,屬于對被告不利的一種選擇,因此,它與有利被告的旨趣有異,故不在本文的考察之列。而“舉重以明輕”是將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不認為是犯罪或減輕處罰的情形解釋為不是犯罪或者減輕處罰,屬于對被告有利的選擇,因而值得著重關注。
關于出罪上的“舉重以明輕”,《唐律疏議》做了很好的詮釋,所謂“‘其應出罪者,依《賊盜律》:‘夜無故入人家,主人登時殺者,勿論。假有折傷,灼然不坐。”又稱:“盜緦麻以上財物,節級減凡盜之罪。若犯詐欺及坐贓之類,在律雖無減文,盜罪尚得減科,余犯明從減法。”這是根據“舉重以明輕”原則而出罪的兩則適例。“折傷”只是給人造成傷害,而“登時殺者”則系致人死亡,既然《賊盜律》明文規定,“登時殺者”尚不追究刑責,那么對于“折傷”就更不應定罪科刑。同樣,因為盜竊緦麻以上親屬的財物在情節上遠比詐欺或因贓致罪之類的行為嚴重,而根據法律規定,盜竊緦麻以上親屬的財物相對于對普通人的盜竊尚可減輕處罰,那么,對緦麻以上親屬所為的詐欺或因贓致罪之類的犯罪,更應比照針對普通人的此類犯罪減輕處罰[2]134。
由《唐律疏議》的以上兩則解釋可以看出,“出罪”不單是指不認定為犯罪,而且還包括從輕處罰。而“舉重以明輕”包括兩種情形:針對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無罪的情形,比照情節較之嚴重但法律規定為無罪的情形認定為無罪;針對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從輕處罰的情形,比照情節較之嚴重但法律規定為從輕的情形認定為從輕。
值得一提的是,“舉重以明輕”不僅在《唐律》中做了如上概括性的規定,而且還貫徹于整個法律制度中,因而作為一項原則得到了確立與遵循。例如,《唐律疏議》解釋道:“問曰:有人本犯罪加役流,出為一年徒坐,放而還獲減一等,合得何罪?答曰:全出加役流,官司合得全罪;放而還獲減一等,合徒五年。今從加役流出于一年徒坐,計有五年剩罪;放而還獲減一等,若依法減一等,仍合四年半徒。既是剩罪,不可重于全出之坐,舉重明輕,止合三年徒罪”[2]566。
《唐律》作為中國歷史上最為發達與完備的成文法,成為后世立法的藍本。相應地,其所確立的“舉重以明輕”的刑法解釋原則,也得到了宋代法律的繼承。《宋刑統》在大量沿用《唐律》的規定的同時,在《名例篇》中設“斷罪本條別有制與例不同”條,照搬《唐律》關于“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與相應的注疏[7]。可見,與唐代一樣,“舉重明輕”作為刑法解釋的原則在宋代也得到了遵循。
至明清時期,雖然法律均設專條規定了“斷罪無正條”的處置,但其非但沒有如唐、宋法律一樣將“舉重以明輕”作為原則予以明文確認,而且規定“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條者,引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轉達刑部,議定奏聞”[8]。因此,作為限制類推原則的“舉重以明輕”在這一時期似有已被廢棄之嫌。(注:相對于《唐律》,明清刑律的這一規定因拋棄了唐律對類推的限制原則而可認為是唐代以前的類推制度的死灰復燃,是歷史的倒退。正因為如此,薛永升才稱:“唐律只言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明律增入引律比附加減定擬,由是比附者日益增多。律外有例,例外又有比引條例,案牘安得不煩耶”。(薛永升.唐明律合編[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97.))根據這一規定,對于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的案件,可以比照法律有規定的情況“定擬罪名”。在這里,只有類推入罪的主張,而無類推出罪的規定,針對類推出罪所確立的“舉重以明輕”原則自然也無適用的余地。
唐宋時期所確立的“舉重以明輕”的基本旨趣在于:通過比照法律已有的規定,對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形,通過類比做出有利于被告的出罪處理,屬于類推解釋與當然解釋的范疇。對刑法的解釋是適用刑法的前提,因而屬于實體刑法的領域;同時,“舉重以明輕”原則下的解釋是有利被告的解釋,因此,唐宋法律通過確立與貫徹“舉重以明輕”的刑法解釋原則,開創了中國法律史上純實體意義上的有利被告的先河。盡管該原則在立法層面上沒有得到明清刑律的繼承,但作為一種法律解釋方法,它對后世的影響不容低估。時至今日,刑法和民法學人論及當然解釋時,均言必引《唐律》之“舉重以明輕”為淵源,即是明證。
三、“處重為輕依輕法”
通觀唐、宋刑律還可發現,其關于“赦前斷罪不當”的規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程序意義上的有利被告的一個側面。
《唐律》設有“赦前斷罪不當”專條,而《宋刑統》也在“官司出入人罪”的名下,設專款照搬了《唐律》“赦前斷罪不當”的規定,即“赦前斷罪不當者,若處輕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輕,則依輕法”[9]。其意思是,在罪犯獲得赦免前,原判錯誤,如系將輕罪認定為重罪,應依法改判輕罪;而如系將重罪認定為輕罪,則應維持原來所做的處罰輕的判決。
從邏輯上說,既然“處輕為重”應從輕改判,與之相對應,“處重為輕”理當從重改判。惟有如此,才合“實事求是”之理。唐、宋刑律為何置如此明理于不顧,而做出了“處輕為重,則依輕法”的規定?就此,《唐律疏議》與《宋刑統》的說明是:“處斷刑名,或有出入不當本罪,其事又在恩前,恐判官執非不移,故明從輕坐之法”[9]555。這表明,之所以對處重為輕與處輕為重均做從輕的選擇,是為了防止法官堅持原來的錯判而拒不改判。在這里,法官拒不改判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固執己見的問題,它還涉及到法官的責任追究問題。按唐、宋律法的規定,法官出入人罪,斷罪不當,對法官應以反坐追究刑事責任,即應按其對被告所錯定之罪定罪科刑。因為唐、宋律法規定:“斷罪失于入”,“故入者,各以全罪論”,“斷罪失于入者,各減三等;失于出者,各減五等”[9]552-554。這樣,一旦法官的錯判被發現,其自然“在劫難逃”,為免受責任追究,其自然完全可能拒不改判。然而,對于錯判,無論是處輕為重還是處重為輕,均從輕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對法官的處罰,因而有利于其對赦免前所做的錯判予以糾正。正是由于“官司出入人罪”與“赦前斷罪不當”有著如此密切的內在關聯,《宋刑統》才將《唐律》中分列的兩條合并為一條的兩款,統歸于“官司出入人罪”名下[7]552。
關于“處重為輕,即依輕法”,《唐律疏議》與《宋刑統》以例解的方式做了注疏:“‘其處重為輕,即依輕法,假令十惡,非常赦所不免者,當時斷為輕罪及全放,并依赦前斷定”。也就是說,即使本為十惡重罪,只要不屬常赦不免的情形,如果原判認定為輕罪并處以流放,也應維持原判,而不得做出從重的“實事求是”的改判。
明、清兩代刑律,雖也設有“赦前斷罪不當”專條,但其規定與唐、宋二律有別。《大明律》規定:“凡赦前處斷刑名,罪有不當,若處輕為重者,當改正從輕;處重為輕,其常赦所不免者,依律貼斷”[5]221。《大清律例》的規定與此大同小異:“凡(官司遇赦,但經)赦前處斷刑明,罪有不當;若處輕為重(其輕本系赦所必原)者,當(依律)改正從輕(以就恩宥);(若)處重為輕,其(情本系)常赦免所不免者,(當)依律貼斷”[10]。將明、清律與唐、宋律相對比可以發現,就“處輕為重,當改正從輕”而言,各個朝代的規定一脈相承,并無二致;但就“處重為輕”而言,唐、宋律關于“處重為輕,則依輕法”的規定,在明、清律中未再出現。正是因為如此,薛永升才在其所撰的《唐明律合編》中指出:“唐律先言處輕為重、處重為輕之事,次言常赦所不免者,再次言赦書定罪從輕者,并無依律貼斷之法。明律處輕為重,與唐律同;處重為輕,與唐律異”[11]。薛氏雖然發現了明律與唐律關于處重為輕的差異,但并未揭示其原因。
那么,明、清刑律未承襲唐、宋刑律關于“處重為輕,則依輕法”的規定,其原因究竟何在?如前所述,按《唐律疏議》與《宋刑統》的說明,之所以做出“處重為輕,則依輕法”的“將錯就錯”的選擇,是為了防止法官堅持原來的錯判而拒不改判。在明、清刑律中,針對“官司出入人罪”而對法官所規定的反坐,其嚴厲性絲毫不亞于唐、宋,唐、宋統治者關于法官因恐“在劫難逃”而拒不改正原判的顧慮,明、清統治者同樣存在。但唐、宋奉行的是懷柔政策,試圖以從輕來感召法官,促成其積極改正錯判;而明、清統治者所奉行的是高壓政策,試圖以從重來重懲出入人罪的法官,以儆效尤。因此,明、清刑律拋棄唐、宋律法關于“處重為輕,則依輕法”的規定,其原因也許只能從不同朝代的統治者所奉行的不同治理策略的角度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當然,如前所述,撇開唐、宋關于“處重為輕,則依輕法”的規定出臺的特殊考慮不說,“處重為輕,則依輕法”的規定,與“處輕為重,當改正從輕”的規定所應有的邏輯對應關系相違背,明、清不采納“處輕為重,則依輕法”的規定,也盡在情理之中。
四、“格輕,聽依輕法”
與前述唐、宋律中的“處重為輕從輕法”密切相關的一個重要現象是:自《唐律》開始,中國法律史上開始關注刑法的時間效力問題。而正是自《唐律》開始,作為實體意義上之有利被告的要求,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開始得到承認。
《唐律疏議》載曰:“故令云:‘犯罪未決,逢格改者,聽依改者,格重,聽依犯時;格輕,聽依輕法。即全無罪,亦明輕法”[9]566,同樣的記載也見諸《宋刑統》中[7]555。在唐、宋時代,“格”為法律的一種,是為官者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所謂“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為官者違反“格”,應按“律”論罪科刑,即所謂“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注:《新唐書?卷五十六?刑法志》)在這一意義上,“格”構成認定為官者瀆職犯罪的根據,違“格”者,成立瀆職犯罪,未違“格”者,無瀆職犯罪可言。正是由于“格”對于認定瀆職犯罪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因此,“格”的廢、立、改直接影響到瀆職犯罪的認定。唐、宋律法中記載的上引“令”文,便是針對新“格”對于正在審判但尚未斷決的案件是否具有制約作用而頒布的。所謂“犯罪未決”,即案件正在審理、尚未判決;所謂“逢格改者”,是指遇“格”發生修改;所謂“聽依改者”,其意為適用修改后的新“格”;所謂“格重,聽依犯時”,意即如修改后頒行的新“格”較之舊“格”的處罰為重,則不適用新“格”而適用舊“格”;所謂“格輕,聽依輕法”,是指如新“格”較之舊“格”的處罰為輕,則適用新“格”而不適用舊“格”。由此可見,唐、宋律法中作為刑法的表現形式之一的“格”在時間效力上,采用的是輕法優先的原則,即對于正在審理的案件,原則上適用審理時頒行的新“格”,但如新“格”對被告的處罰重于行為時的舊“格”,則適用舊“格”。套用今天的刑法學術語,便是“從新兼從輕”。從邏輯上說,適用新“格”與適用舊“格”均有其理由,以處罰輕作為選用新“格”或舊“格”的根據,確系對被告有利的一種選擇,因此,唐、宋律法中所確立“格”的“從新兼從輕”的時間效力原則,在實體意義上體現了有利被告的理念。
唐、宋刑律所確立的“從新兼從輕”原則,不但體現在關于“格”的時間效力的上述規定中,而且也體現在關于對赦書所從輕認定的罪名不得引律比附入重的規定上。唐、宋律規定:“即赦書定罪名,合從輕者,又不得引律比附入重,違者各以故、失論”。就此,《唐律疏議》與《宋刑統》例解道:“假如貞觀九年三月十六日赦:‘大辟罪以下并免。其常赦所不免、十惡、妖言惑眾、謀叛已上道等,并不在赦例。據赦,十惡之,赦書不免;‘謀叛即當十惡,未上道者,赦特從原。叛罪雖重,赦書定罪名合從輕,不得引律科斷,若比附入重。違者,以故、失論”[9]567。根據這一規定與相關注疏,在赦書頒布后,對于赦書已確定減輕或免除處罰的案件,司法者不得比附律中的有關規定而對其做出重于赦書的處置。赦書即皇上赦免罪犯的正式文件,具有特別刑法的效力;相對于作為普通法的“律”,赦書是新法;相對于作為重法的“律”,赦書是輕法。禁止司法人員在赦書頒布后通過比附而適用“律”,實際上是強調赦書作為新法與輕法的優先效力,從而進一步強調對“從新兼從輕”原則的適用。
與前述“處重為輕依輕法”的歷史遭遇一樣,唐、宋律所確立的“從新兼從輕”原則在明代也慘遭廢棄。《大明律》雖就刑法的時間效力設專條予以規定,但誠如其條名所昭示的那樣,它所采用的是單純的“從新原則”。《大明律》在“斷罪依新頒律”名下的具體規定是:“凡律依自頒降日為始,若犯在已前者,并依新律擬斷”[10]23。這一規定雖然在“從新”上承襲了唐、宋律的精神,但因其對新、舊律的輕重不加考慮,拋棄了唐律“從新兼從輕”原則所體現的輕法優先的精神,因而背離了《唐律》在刑法的時間效力上所體現的有利被告的旨趣。因此,薛永升才寫道:“新律與舊律頗有輕重互異之處,并依新律擬斷,似亦未盡平允。”盡管根據薛永升的說法,明律后來似乎通過注解的方式就該規定做了某種改進,即“后來所添注語,較覺詳備”[11]96,但因該注語未見于《大明律》的文本,難考其詳,故不敢妄加評論。
然而,與“處重為輕依輕法”的遭遇不同,唐、宋律在刑法的時間效力上所確立的輕法優先的原則,在清代得到了發揚光大。清代的《大清律例》雖仿《大明律》設置了“斷罪依新頒律”專條,做出了與明律相同的“凡律依自頒降日為始,若犯在已前者,并依新律擬斷”的規定,但考察此條所加注文,即“如事犯在未經定制之先,仍依律極已行之例定擬。若例應輕者,照新例遵行”[10]126,可知,這與明律單純的從新原則大相徑庭。盡管“凡律依自頒降日為始,若犯在已前者,并依新律擬斷”體現的也是從新原則,但其關于“如事犯在未經定制之先,仍依律及已行之例定擬”的規定,則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從新原則。因為所謂“如事犯在未經定制之先,仍依律及已行之例定擬”,實際上是要求以行為時的舊律與先例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因而在“例”的適用上,體現了從舊原則。而所謂“若例應輕者,照新例遵行”,則是指當審判時的新例的處罰較行為時的舊律與舊例為輕時,適用新例。因此,至少在作為特別刑法的“例”的時間效力上,清律所采用的是“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即原則上適用行為時的舊律與舊例,但新例處罰輕時適用新例。由于從新與舊最終都要服從輕法,因此,至少在“例”的時間效力上,清律與唐、宋律法一樣,體現了輕法優先的有利被告理念。
前清所確立的從舊兼從輕原則,得到了晚清與“民國”刑法的繼承。晚清時由沈家本根據《大清律例》刪改而成的《大清現行刑律》完全沿用《大清律例》的規定,在“例”的時間效力上繼續采納從舊兼從輕的立場,彰顯了輕法優先之有利被告的精神[12]。
清政府于1911年1月25日公布的《欽定大清刑律》第1條的規定,一反從舊之態,而仿唐、明律采用從新的原則,規定“本律于凡犯罪在本律頒行以后者適用之;其頒行以前未經確定審判者亦同”。所謂“頒行以前未經確定審判者亦同”,是指對于正在審理但尚未判決的案件,同樣適用新法,因而體現了刑法時間效力上的從新原則。但是,該條以但書的方式,部分地堅持了輕法優先的精神,即“但頒行以前之法律不以為罪者,不在此限”,即對于正在審理但尚未判決的案件,如舊法不認為是犯罪而新法認為是犯罪的,不得適用新法作有罪宣告。鑒于該條但書只將“頒行以前之法律不以為罪者”作為適用新法的例外,而沒有將舊法處罰輕的情形也排除在適用新法的范圍之外,因此,《欽定大清刑律》對唐、宋律所倡的輕法優先的有利被告理念的貫徹是不全面的。(注:應該指出的是,該條沒有將新舊二法同時規定為犯罪但舊法處罰輕的情形也排除在適用新法的范圍之外,并非立法之疏忽,而是刻意為之,這從沈家本在1907年的刑法草案中所闡述的立法理由中可見其端倪。其內容如下:“本條定刑法效力之關于時者。第一項規定本于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與第十條規定采用律無正條不處罰之原則相輔而行,不宜偏廢也。第二項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審判在施行后,定新舊二律之中,孰當引用也。關于本題之立法例有二:一為比較新舊二法,從其輕者處斷之主義。法國刑法第四條,比國刑法第二條,德國刑法第二條,匈牙利刑法第二條,和蘭刑法第一條第二項,紐約刑法第二條,日本現行刑法第三條第二項,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條第二項,那威刑法第三條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舊二法,概從新法處斷之主義,英國用之。我國明律亦主此義。本朝雖有第一主義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并依新律擬斷之規定。議者謂被告犯罪之時,已得有受當時法律所定之刑之權利。誠如此說,應一概科以舊律之刑,不應復分新舊二律之輕重也。況人民對于國家并無所謂有受刑權利之法理也。或又謂若使新律重于舊律,而舊律時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則與舊律時代受舊律輕刑之同種犯人相較,似失其平。誠如此說,則使新律施行之后,僅此舊律時代之同犯犯人科以舊律之輕刑,彼新律時代之犯人據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較,則又失其平矣。或又謂刑失之嚴不如失之寬。從新律之輕者,所以為寬大也。然刑不得為沾恩之具,非可嚴亦非可寬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國民之程度以為損益。既經裁可頒布,即垂為一代之憲章,不宜復區別輕重寬嚴也。歐美及日本各國多數之立法例,所以采用第一主義者,蓋受法國刑法之影響。而法國刑法之規定則其時代之反動耳,于今日固無可甄擇者。我國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義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與多數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義也。第二項后來頒行以前之律例不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與前微異,蓋一則新舊二律俱屬不應為之罪惡,不過輕重之差。一則新律雖為有罪,而舊律實認許其行為,因判決在后,遽予懲罰,有傷期刻也。”進而,沈家本先生在按語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項既采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為,在新刑律雖酷似有罪之行為,不得據新律之規定而罰之。第二項指未經確定裁判者,雖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訴而變更之。凡案件具此情節,檢察官即得上訴而請求引用新律。其上訴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訴訟法為據”。(沈家本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進呈刑律草案折大清法規大全?法律部(卷11)))
北洋政府于1912年在刪改《欽定大清刑律》的基礎上,頒布了《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在刑法的時間效力上,該法完全沿用了《欽定大清刑律》的規定,有保留地貫徹了從新兼從輕的輕法優先原則。
南京國民政府于1928年頒布的《中華民國刑法》第1條將《欽定大清刑律》與《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中的從新原則改為從舊原則,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行為后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同時,該法全面突出了輕法優先的思想,以但書的方式將輕法作為適用舊法的例外,規定“但行為后之法律有利于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于行為人的法律”。就本文所研究的話題而言,《中華民國刑法》關于刑法時間效力的這一規定,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它不但使《唐律》所首倡的“輕法優先”思想在法條上得以固定,而且以“最有利于行為人”作為適用法律的標準,從而揭示了“輕法優先”與有利被告的內在關聯,使有利被告這一術語與理念首次被引入了中國實體刑法的語境之中。
五、結語
如果細究中國歷史上浩瀚的法律典籍,可以發現,關于有利被告的規定俯拾即是。(注:例如,《唐律疏議》所規定的,侄不識叔而毆打叔,仍不得加重處罰;父不識子而毆打子,仍應減輕處罰,在一定程度上也屬有利被告的規定。)前文只不過是對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一些規定的粗略考證。然而,考證雖然是粗略的,但從中得出的結論卻是重要的。因為這些結論不但是對中國歷史語境中有利被告話語的規律性總結,而且它對于厘清時下中國法律界對有利被告的某些模糊認識具有啟發性的意義。
“罪疑惟輕”的起源與傳承表明,“罪疑惟輕”中的“罪疑”主要是指證據與事實存疑,與解決疑罪相配套的諸如“赦贖”與“疑讞”之類的法律制度,也主要是程序性的。在這一意義上,如胡適所說,將“罪疑惟輕”界定為程序語境中的有利被告話語,未必不當。但不容忽視的是,在中國歷史上,經多年的流變,“罪疑”由證據與事實存疑擴展到了法律上的存疑,即由事實認定上的程序問題延伸到了法律適用上的實體問題,甚至成為統治者在不問事實與法律是否存在疑問的情況下對被告予以寬大處理以示仁政的托辭,使得“罪疑惟輕”已偏離了其原有意思
,因此,將“罪疑惟輕”如胡適所解釋的一樣簡單地視為程序上有利被告的表現,或者將其如蔡沈所注解的一樣單純地視為實體上有利被告的反映,均難免偏頗。至于“舉重明輕”與“格輕,聽依輕法”,前者屬于刑法解釋問題,后者則屬刑法的時間效力問題,兩者均屬刑法適用的范疇,因而是典型的實體刑法話語。由此可見,時下中國學界部分學者關于有利被告只適用于程序刑法而不適用于實體刑法的主張,似顯片面。
如前所述,“罪疑惟輕”、“舉重明輕”、“處輕為重依輕法”與“格輕,聽依輕法”均是針對犯罪事實或刑法適用方面出現的疑問而提出的解決辦法,而借助這些解決辦法對案件所做的處置均是對被告有利的,因此,這與“存疑即有利被告”的旨趣不謀而合。尤其發人深省的是,作為中國歷史話語中的“罪疑惟輕”、“舉重明輕”、“處輕為重依輕法”、“ 格輕,聽依輕法”,與統歸于有利被告名下的“疑罪從無”、“禁止不利被告的類推解釋”、“一事不再理”及“新法不溯及既往”等西方話語具有相當程度的相似之處。而且,正如“有利被告”與“疑罪從無”等已成西方法諺一樣,“罪疑惟輕”與“舉重明輕”等也已成中國成語。可見,中國歷史語境中的有利被告在中華法系中的影響與地位,絲毫也不遜色于西方語境中的有利被告在西方的影響與地位。因此,簡單地把有利被告視為“舶來品”,否認中國具有培植與生成這一理念的土壤,未免武斷而淺薄。
然而,有利被告的中國歷史話語與西方語境中的有利被告話語畢竟只是“貌合”,而非“神合”,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兩者之間的“神離”甚于“貌合”。
“罪疑惟輕”與“疑罪從無”雖然都要求在證據與事實存在疑問時做出對被告有利的處置,但前者的處置結果為“輕”,后者的處置結果為“無”。“輕”即從輕處罰,其前提是需要處罰,“無”的處置結果是不處罰,兩者間的“神離”是顯而易見的,在“罪疑惟輕”的支配下,雖如黃羲之所言,“冥途有歸魄”,但也難免“冥途歸魄”成為“牢中冤鬼”,即所謂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因此,胡適才一語中的地指出:“罪疑惟輕等于說‘證據不夠,只宜從寬發落。這個從寬發落的人終身不能洗刷他的冤枉,不能恢復他的名譽”[1]538。
“舉重明輕”本身雖然是對被告有利的出罪解釋,因而與“禁止不利被告的類推解釋”有“貌合”的一面。但是,在中國法律的歷史語境中,“舉重以明輕”的出罪解釋與“舉輕以明重”的入罪解釋如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兩者并行不悖,同時有效。由于“舉重以明輕”并不排斥“舉輕以明重”,而后者歸根結底是通過類推解釋而對被告做出不利的處置,這遠未達到“禁止不利被告的類推解釋”的境界,因此,兩者之間的“神離”也是顯而易見的。
“處輕為重依輕法”與“一事不再理”不但“貌合”,而且“神似”,但可惜只是存在于唐、宋二律,在明、清二代即已失傳,以致沒有形成傳統。而且,即便是在唐、宋二律中,它也只是針對赦前的錯判這一特定的問題而形成的規則,而并非如“一事不再理”一樣形成制約整個再審程序的具有普適性的一般原則。因此,中國歷史話語的“處輕為重依輕法”與西方話語中的“一事不再理”從“貌合”到“神似”都是有限的,難以相提并論。
“格輕,聽依輕法”與“新法不溯及既往”雖然因要求在新、舊法之間選用對被告有利的輕法而“貌合”,但“格輕,依聽輕法”在晚清以前是以適用新“格”為原則,以適用輕法為例外,而“新法不溯及既往”則恰恰與此相反,它以適用舊法為原則,以適用輕法為例外。兩者間的“神離”之處不言而喻:前者的基本立意是事后法可以溯及法前之事,強人所難地要求國民在行為時對行為后可能出現的對行為的禁止作出預測,而后者則免國民于此難。晚清以后的立法,雖改從新兼從輕為從舊兼從輕,從而使中國歷史語境中的“格輕,聽依輕法”發生了與西方語境中的“新法不溯及既往”相“神合”的質變,但值得重視的是,這并非中式話語的歷史發展的必然,而恰恰是晚清與民國將西方話語移植到中國語境中的結果。
中國歷史語境中的有利被告話語之所以與西方話語貌合神離,其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文化差異。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歷代統治者講求不走極端的中庸之道,崇尚中和與折中,在法律領域亦不例外。“罪疑惟輕”與“舉重以明輕”即是中庸文化在刑法領域的典型折射,在遇有“疑罪”時不走從有或從無的極端,而做出“從輕”的折中選擇,極其藝術地以“輕”在“有”與“無”之間作了折中;遇有法律規定不明,不做偏向無罪或有罪的絕對選擇,而設計出“舉重以明輕”與“舉輕以明重”的出、入罪路徑,使刑事政策以對仗的形式美凸顯出左右逢源的“中和”文化。唐、宋二代所奉行的“處重為輕依輕法”與“處輕為重依輕法”,之所以被明、清二代的“處重為輕依輕法”與隱性的“處輕為重依重法”所取代,原因就在于前者因偏重“輕”而有失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而后者只不過是一種糾偏,而這也許正是“處輕為重依輕法”不如“罪疑惟輕”那樣對后世影響深遠的原因所在。同樣,在新、舊法律并存之時,單純的從新或從舊選擇,都會因顯示出對新或舊的偏向而有失中和。因此,才有了唐、宋律的從新兼從輕,前清的律從新、例從舊兼從輕以及晚清的無罪從新、罪重從舊的折中選擇。民國初期之所以率先在刑法的時間效力上采用從舊兼從輕主義而接納了“新法不溯及既往”的有利被告立場,很難說與“從舊兼從輕”本身因折中了新、舊之法而與注重折中的中庸文化相契合沒有關聯。與此不同,秉承主權在民的思想理念,西方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重視個人權利的文化傳統,當國家與個人、權力與權利發生沖突時,所要求的是國家為個人、權力為權利讓路。這樣,當有關犯罪的事實或者相應的法律規定存在疑問時,國家做出有利于被告的選擇,便具有必然性。因此,遇有疑罪,才有了從無的抉擇;遇有法律規定不明,才有了不得類推定罪的禁忌;遇有錯判,才有了“一事不再理”原則下的有利于被告的將錯就錯;遇有新、舊法律并存,才有了“重法不得溯及既往”的鐵律。
由于有利被告的中國歷史話語與西方話語不但“神離”甚于“貌合”,而且生成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因此,斷言中國自古即有了近現代西方意義上的有利被告原則,甚至如時下臺灣地區與祖國大陸學界所流行的觀點
一樣,將“罪疑惟輕”作為“有利被告”的對譯詞,(注:參見:黃海濱.醫療刑事訴訟之舉證與無罪推定[J].臺灣醫界,2006,(3).)似顯輕率。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就中國刑事法對有利被告理念的接納而言,所面臨的既不是簡單的承接歷史話語的問題,也不是簡單的把西方話語移植到中國刑事法之中的問題。因為時下中國對有利被告理念的接納,其困難不在于如何對有利被告的西方話語的移植本身,而在于如何改良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以免作為“外來物種”移植而來的西方話語,在與作為“本土物種”林立的中國傳統話語的競爭中,因水土不服而難以生存。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中國學界曾經而且至今仍存的關于西方有利被告的話語在中國是否存在適合其生存的環境的擔心,也確非杞人憂天。
參考文獻:
[1]胡適.胡適的日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5:599.
[2]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 北京:中華書局,1988:575.
[3]傅德岷,賴云琪古文觀止鑒賞辭典[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8:466.
[4]黎靖德.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94:2711.
[5]大明律[M].懷效鋒,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40.
[6]胤禛.圣諭廣訓[M].北京:檢古齋,清光緒15年(1889)石印本.
[7]宋刑統[M].薛梅卿,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10.
[8]大明律[M].懷效鋒,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1;大清律例[M].田濤,鄭秦,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27.
[9]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566;宋刑統[M].薛梅卿,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55.
[10]大清律例[M].田濤,鄭秦,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79.
[11]薛永升.唐明律合編[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809.
[12]沈家本,俞廉三.大清現行新刑律?名例下(上)[M].長沙:長沙維新機器印刷局.
Classic Chinese Expressions in Favor of the Accused
XING Xin-yu
(Institute of Criminal Law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100086,China)Abstract:
In the literature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 one can readily find some expressions in favor of the accused, such as yizuiweiqing (in doubt, in favor of mitigation), juzhongmingqing (while punishing the accused on the analogy of a felonious provision, in favor of mitigation), chuzhongweiqingcongqingfa (the appellant cannot be imposed on more severe punishment) and geqingtingyiqingfa (while there are different laws, prefer the law that imposes milder penalty), which illustrate the alternatives in favor of the accused both from the procedural and the substantive perspectives, for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because of their everlasting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However, such Chinese expressions in favor of the accused are in essenc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similar western ones though they are seemingly in harmony. To have the notion in favor of the accused firmly entrenched in Chinese culture, one should at first study the historical expressions in favor of the accused that are imbued with the golden mean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yizuiweiqing, juzhongmingqing, chuzhongweiqingcongqingfa, geqingtingyiqingfa
本文責任編輯:梅傳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