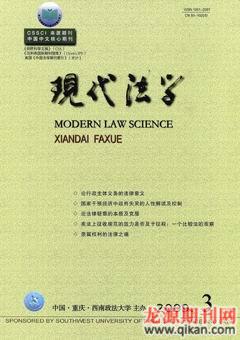親屬權利的法律之痛
俞榮根 蔣海松
摘要:中國古代“親親相隱”是一種親情倫理立法,現代東西方主要國家法律都確認由親屬身份而自然獲得的某些例外特權,這是一種親屬權利立法。我國現行法律在否定“親親相隱”的親情倫理立法以后,卻沒有確立親屬權利立法原則,這種傳統與現代的斷裂導致諸多尷尬和悲劇,“佘祥林案”中佘母的不幸遭遇即為典型。本文闡釋古代“親親相隱”親情倫理立法和現代親屬權利立法的各自特點,論述法律確認親屬權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探討古老“親親相隱”對確立我國現代親屬權利制度的正面價值及其在現代人權理念之下的創新轉化。
關鍵詞: 親親相隱;親屬權利立法;現代轉化
中圖分類號:DF04
文獻標識碼:A
美國大法官霍爾姆斯在投票贊成米蘭達無罪之判時說:“罪犯逃脫法網與官府的非法行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同樣, 維護親屬特權可能會致罪犯逃脫法網,但這與以法律的名義撕裂人性、踐踏親權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題記
引言:從佘祥林母親“包庇犯罪”說起
“佘祥林案件”(注:佘祥林,男,1966年3月7日生,京山縣雁門口鎮何場村九組人,被捕前系京山縣公安局原馬店派出所治安巡邏員。1994年1月2日,佘妻張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失蹤,張的家人懷疑張在玉被丈夫殺害。同年4月28日,佘祥林因涉嫌殺人被批捕,后被原荊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后因行政區劃變更,佘祥林一案移送京山縣公安局,經京山縣人民法院和荊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1998年9月22日,佘祥林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在佘祥林服刑11年后,即2005年3月28日,佘妻張在玉突然從山東回到京山。4月13日,京山縣人民法院經重新開庭審理,宣判佘祥林無罪。)曾引起廣泛討論,但人們的注意力多集中在“佘祥林冤案”的本身,集中在討論造成他的冤案的司法原因與怎樣避免類似冤案的發生等問題上。這當然沒有錯,但我們卻忽視了佘案背后的另一樁不正常死亡的悲劇,這個悲劇正發生在佘樣林母親楊五香身上(注:自佘祥林出事后,佘母楊五香走遍了周圍的村落尋找出走的兒媳。因為佘祥林跟她說過“我確實沒有殺她”。這個倔強而愛子的農村婦女就開始了為兒子辯污的艱辛之路。她窮困潦倒,身無分文被人接濟著四處尋找,1995年元旦前后,楊五香尋訪到了離雁門口幾十公里遠的天門市石河鎮姚嶺村,發現兒媳的線索。姚嶺村副書記倪樂平給她出一個見過張在玉的證明。這份證明后來被媒體稱為“良心證明”,如果沒有它,也許佘祥林早已作了槍下冤魂。然而,這份證明送到有關部門后,并沒有得到令佘家驚喜的結果,對方的回答是“這一套我們見得多了”。楊五香因為反復上訪和申訴被抓了起來,抓起來的原因是“包庇犯罪”、“妨礙司法公正”。9個月后,看守所通知佘家帶上3 000元錢去領人,看守人員把楊五香背了出來。“她變得又聾又瞎,不會走路。”佘祥林的父親佘樹生說。在病痛中捱了3個月后,佘母楊五香去世,死時年僅54歲。(毛立新.拿什么紀念佘祥林的母親[EB/OL] (2006-04-02)[2008-08-20].http://www.dffy.com)。她因反復上訪和申訴,被有關部門認定為“包庇犯罪”、“妨礙司法公正”,關進看守所長達9個月,身心備受折磨,回家后3個月,這位倔強而愛子心切的母親在郁郁中去世,年僅54歲。
佘祥林冤案是一個特例,佘母楊五香的悲劇可能是特例中的特例,但它極具典型意義,反映出我們法律制度上的某種缺失。
假如佘案發生在古代,楊五香不可能被關押,因為有“親親相隱”的法律明文,對自己的親生兒子,她理當“包庇”,應當“包庇”,為他辯誣,人情所然,天理所使,至大至愛,何罪之有?
假如佘案發生在現在的英、美、法、德、日等國,以及臺灣地區,佘母也不致于被拘押,因為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現行刑法和刑訴法規定,為使家屬免于刑罰處罰,即使是故意包庇或窩藏之行為,亦“不處罰”,為愛子蒙冤而奔走呼號,是其份內權利,情當力爭,理當力爭,法當力爭,何來的“妨礙司法公正”?
前者屬于中華法系的古代血緣親情倫理立法,后者屬于現代意義上基于人性的親屬權利立法。血緣親情倫理立法的宗旨是家庭本位,基于人性的親屬權利立法的宗旨在于維護人權。
佘母的悲劇在于,在我國現行法律否定了“親親相隱”的家庭本位親情倫理立法以后,尚未在立法體系上將基于人性的親屬權利立法原則貫徹到底。我們的法律既擯棄了倫理親情,又未徹底確認以人為本的基本人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發生了斷裂,因而難免發生違背人之為人基本人性及有悖情理之事,難免出現違背人之為人基本人性及有悖情理之法,難免制造出違背人之為人基本人性的有悖情理之判。如果說,“親親相隱”是一個“肯定”,它對立面“大義滅親”則是“否定”,那么,確立基于人性的家屬權利立法便是“否定之否定”。我們需要向前再邁一步,從以家庭為本的親情倫理立法到確認以人為本的家屬權利立法的“否定之否定”,實現傳統法的轉化創新。當我們把基于人性的愛護親人、庇護親人作為家屬的特定權利在法律上加以明確規定下來時,佘母之類的悲劇就能從法律制度上加以避免,天下百姓就可以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與生俱來的愛親護親權利,那樣的社會一定會更加和諧。
本文選擇從佘祥林母親楊五香的故事入手以說明古老的“親親相隱”之法律傳統的斷裂,并通過中外比較以試圖尋求這一法律傳統的現代轉化之可能。
近十幾、二十年來,學界不斷有人研究“親親相隱”問題,成績斐然。1997年,范忠信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等刊物發表《中西法律傳統中的“親親相隱”》等多篇文章,闡述如下觀點:“從古代到近現代,從西方到東方,從奴隸制法、封建制法到資本主義法甚至社會主義法,均存在著“親親相隱”之類的規定。因此,是否存在這一原則或規定,并不足以構成一個國家或法系的特色,也不足以構成一個歷史階段或一種社會制度下法律的特色。”[1]其后,哲學界圍繞“親親互隱”問題開展了一場爭論,雙方就“舜竊父而逃”是否腐敗、中外是否存在“親親相隱”之類相同的道德和法律傳統、“親親相隱”在現代社會應作如何評價等等一系列問題唇槍舌劍,激烈論爭,論題所及遠遠超過“親親相隱”本身,關涉如何對待和創新傳統等重大時代課題[2]。2007年,中山大學陳璧生博士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親親相隱:從經典、故事到傳統》。年輕新秀加入“親親相隱”研究,給學界帶來了新氣。陳文認為:“作為制度設計,‘父子相隱在歷史上經歷過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唐律到清律,在這一時期,“父子相隱”思想與三綱思想、《孝經》中的君父臣子思想相結合,體現在‘同居相為容隱的律文規定之中,其目的是以刑律的方式維護傳統的‘禮之中的親情,維護家族制度。第二個時期是在民國的《六法全書》中,‘父子相隱思想與權利觀念、平等思想相結合,體現在刑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中,其目的是以法律的形式維護現代‘法之下基于人情的權利。最后,由于階級觀念的進入,‘父子相隱思想的建制被終結了。” [3]在本文修改過程中,又有幸看到張傳璽先生發表在《中華法律文化網》上的文章《對唐律“同居相為隱”規定的再認識》。張文力主將思想層面的“父子相隱”的論述與法律制度層面的“容隱”的規定分開討論,認為,“唐律中法律層面的‘同居相為隱針對的僅是犯罪事發后藏匿罪犯、向罪人偷報消息等主動幫助罪人逃避法律制裁的行為,而與告發、舉證等行為無關。” [4]筆者從上述研究成果和其他相關論著中受到不少啟發,并從中選定了自己的思考和研究維度。
一、“親親相隱” :基于親情的傳統倫理立法
親親相隱制度又稱親屬容隱制度,是指一定范圍內的親屬之間履行互相隱瞞罪行的義務而不受法律制裁的制度。
最早提出父子應當相隱的是孔子。《論語?子路》中記載:“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注: “隱”,指“不稱揚其過失”。《禮記?檀弓》謂:“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但《論語》此章先言“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隱”系對“證”而言,“證”,《說文》釋為“告也”,可知孔子在此處所言之“隱”,具體地說就是隱瞞不告。)
孔子的這種觀點只是一種主張,或者說是一種法思想,不是法律規定。
戰國時期,秦國法律有“公室告”與“非公室告”之分。據《睡虎地秦簡》,“賊殺傷、盜它人”之類的賊盜犯罪行為是“公室告”,官府必須糾舉,知情者必須舉告;而“子盜父母,父母擅殺、刑、髡子及奴妾”之類的同居家庭內部財產、刑事糾紛屬于“非公室告”。“非公室告”的行為,家庭內部人不許舉告,第三人控告亦不受理。《法律答問》云:“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而行告,告者罪。” [5]這一規定可知,在同居家庭中,發生財物上的家內盜竊行為,不許告;發生人身方面的尊長/主人殺傷卑幼/奴妾行為,不準卑幼告尊長、奴妾告主人。這與孔子所說的子應當隱瞞父親竊他人之羊的行為有所不同,也與后世的“同居相為隱”法律有區別。秦簡中的這類規定也沒有賦予什么倫理價值,基本上屬于那種國家對家庭傳統地位和家長傳統權力的認可,并采取不干預和保護的態度。據荀子所見,戰國時的秦國“無儒”[6]。秦簡中的這類規定,不見得是受了孔子“父子相隱”主張的影響,這類規定中也從未出現一個“隱”字,這或許可以看做是對古老的民間習慣的確認。畢竟,華夏社會中的血緣家庭存在久遠,華夏傳統中維護血緣家庭的習俗習慣、倫理道德不僅歷史悠久面且積淀豐厚。順便強調一下,中華法系中以家庭為本位的親情倫理立法條款,諸如容隱、緣坐、存留等等,說到底是由血緣家庭為中心的社會情勢決定的。秦簡此舉,亦是“勢也”。
以法令形式確立親親相隱制度始于西漢。漢宣帝地節四年(公元前66年)皇帝下詔:“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7]這一詔令在中國法制史上的意義在于,第一,明確運用儒家的仁學對家庭親情的倫理價值予以高度肯定,其將家庭親情視為“天性”尤其寶貴,可視為古代以家庭為本位的血緣親情倫理立法原則的經典性立法解釋;第二,突破秦簡家內犯罪不許舉告的框框,肯定孔子關于父或子有社會犯罪行為應相互隱瞞的主張并加以最大限度地擴張。詔令規定:凡卑幼隱匿尊長,無論什么罪,皆不治罪;凡尊長隱匿卑幼,死罪以下不加追究,應入死罪者“上請”減免。自此,“親親相隱”進入古代法律制度領域。
如果說,漢代的“親親得相首匿”詔令還比較粗疏,那么,唐律“同居相為隱”條就十分詳備了。《唐律疏議?名例律》規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結合律疏,可知唐律“同居相為隱”條值得重視之處有以下五端:第一,明確相隱的范圍。一為同財共居者,不管是否同籍,即使無服,亦可相隱;二為“大功以上”服制重的血親;三為服制雖輕,但“情重”的“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但外祖父母不得擴大到曾、高外祖父母,外孫亦也不得擴大到曾、玄外孫。此外,還有兩類人可有條件適用“相隱”,一是“部曲、奴婢”等家內奴隸“為主隱”,二是“小功以下”親“相隱”。第二,明確相隱的方法。相隱范圍內的三類人履行的相隱義務是雙向的,“小功以下”親“相隱”也是雙向的,但“部曲、奴婢”等家內奴隸履行單向的“為主隱”義務,主人則不必為他們隱。第三,明確相隱的法律責任。相隱范圍內的三類人相隱,以及“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是完全的免責;服制較輕的“小功以下”親相隱則只能部分免責,即因相隱而致罪“減凡人三等”處罰,按《疏議》解釋,“減凡人三等”,即為減所隱之本罪四等。第四,明確相隱的行為。一是按照“相隱”的本義,實施“知情藏匿”犯罪事發之罪人的行為;二是實施“漏露其事”和“擿語消息”兩種向罪犯進行通風報信的行為,即通過向罪犯泄露搜捕情況及暗中傳遞消息的辦法協助其逃避官府懲罰。第五,明確不適用相隱律條的罪名。律文最后有個十分重要的“但書”:謀反、謀大逆、謀叛三項“十惡”之首的重罪,不適用“相隱”律條。據唐律,犯此三項重罪者家族“緣坐”,所以又稱緣坐重罪不得“相為隱”, 部曲、奴婢也不得“為主隱”。
唐律又對違反相為隱的行為作了處罰規定。其《斗訟》篇的“告祖父母父母”、“告期親尊長”、“告緦麻卑幼”、“部曲奴婢告主”各條和《賊盜》篇“親屬為人殺私和”條等,詳細規定了不得告發的義務和違犯的處刑標準。凡非緣坐重罪,卑幼告尊長重者可入“不孝”罪。
至此,“親親相隱”立法趨于周全,從技術上說已比較成熟。這一“同居相為隱”制度的立法格局,宋、元、明、清各朝大體維持如唐,少有改作。
古代“親親相隱”立法有三點值得重視:其一,是它的家庭倫理本位。相隱成立的前提是同財共居的家人、有服血緣的親人,以及親情特重的親人,歸結起來,無非兩類人:血親和姻親。實際上都是基于家庭的血緣親情,維護家庭的倫常秩序和利益。古代家庭中也有非血緣的成員,如奴婢、部曲之屬,他們必須單方面履行“為主隱”的義務,這仍然是為了血緣家庭的穩定。基于家庭的血緣親情、夫妻情愛是人性中最原初的感情,并由之升華為一整套“孝”、“悌”、“慈”、“順”的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誠如漢宣詔令所言,“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 “親親相隱”正是秉天性(天理)、順人情的立法。血緣家庭倫理是相隱的立法宗旨。其二,是它的義務本位。無論是血親成員之間雙向相隱,還是奴對主的單向相隱,都是履行義務。這些義務行為是由倫理道德規范加以調整和作出評價的,諸如,卑幼隱尊長是盡“孝”的義務,尊長隱卑幼是盡“慈”的義務,同輩兄弟之間相隱是“悌”,夫婦之間相隱是“義”、是“順”,奴隱主是“忠”。相隱立法則是把倫理道德義務提升為強制性的法定義務。總而言之,它是一種義務立法,與西方近代以來所提倡的“沉默權”、“不舉告權”、“不舉證權”有所不同。其三,是它的國家本位。“親親相隱”不是無界限的,危害皇權、危害國家,諸如緣坐重罪是不得相隱的。國家安全、君主利益是家庭倫理本位的“紅線”。儒家血緣親情倫理立法恰到好處地把握了相隱與不得相隱、曲法伸情與大義滅親之間的“中道”尺度。
二、法律現代化之困:傳統的斷裂
自清末修律始,中華法制走上近代化之路,相沿數千年的中華法系解體。從《大清新刑律》開始, 刑事立法取消了“干名犯義”之罪,也就是說,親屬之間相隱不再是強制性的法定義務(注:1907年10月4日,沈家本向清庭《進呈刑律草案折》,這一草案已無“親屬相為容隱”、“干犯名義”諸條。1911年1月25日頒行的《大清新刑律》維持這一狀態。)。然而,親屬是否因其身份而在訴訟、定罪量刑中享有某種免責或減免的特權,百年來經歷了肯定——否定的異常曲折的道路。
1907年沈家本主持草擬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在第十一章“關于藏匿罪人及湮滅證據之罪”中規定:“犯罪人或逃脫人之親族為犯罪人或逃脫者利益計而犯本章之罪者,免除其刑。”該草案雖因禮教派的強烈反對而收回重新草擬,但實際上已為從“親親相隱”的立法轉為因親族身份享有包庇犯罪減免刑罰特權的立法打開了大門。1910年擬定的《大清刑事訴訟律草案》,則第一次在舊中國設立了特免權制度 (注:訴訟法上的特免權一般指證人作證特免權,又稱證人特權、證人免證權、證人拒證權,是指在法定情形下,特定公民享有的拒絕作證或制止他人作證的權利。本文所謂的親屬身份特免權除親屬作證特免權外,還包括親屬藏匿犯罪人、湮滅證據減免刑罰的特權。)。盡管這部法律因為清政府的覆亡而沒有實行,但為后來的立法提供了樣本。1911年1月25日,《大清新刑律》頒行。它幾乎照搬了《新刑律草案》“關于藏匿罪人及湮滅證據之罪”一章的全部規定,親屬身份特免權由是確立。1905年北洋政府的《修正刑法草案》,在寬宥親屬藏匿犯罪人、湮滅證據問題上,基本上照搬《大清新刑律》。自1929年開始歷經16年制定的南京民國政府《六法全書》將親屬藏匿犯人、湮滅證據免罪以及拒證的權利,分別規定在《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三種主要法律中,形成一個相照應的親屬身份特免權法律體系(注:南京民國政府制定的《刑法》第九章“藏匿人犯及湮滅證據罪” 第167條規定:“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逃脫人,而犯第一百六十四條或一百六十五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刑事訴訟法》中的“人證” 第167條規定:“證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言:一現為或曾為被告人或自訴人之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二與被告人或自訴人訂有婚約者。”其《民事訴訟法》中的“人證” 第107條規定:“證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言:一正人為當事人之配偶、前配偶、未婚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系者。”)。
總起來說,從清末到民國近半個世紀,關于親屬問題上的刑罰、訴訟方面逐漸形成一個因親屬身份而獲得特免權的系列規定:為庇護親屬而藏匿人犯及湮滅證據不罰;放縱或便利親屬脫逃減輕處罰;為親屬利益而偽證及誣告免刑;為親屬頂替自首或頂替受刑不罰;為親屬銷贓匿贓得免罰;有權拒絕證明親屬有罪;對尊親屬不得提起自訴等。這在一定程度上照顧了傳統社會重視家庭倫理價值的民情。
新中國建國之初,全面廢除以“六法全書”為代表的“舊法統”,上述法條自在掃除之列。“司法改革”鋒芒所指,不論古老的“親親相隱”制度,還是“六法”中的親屬特免權規定,一概被認定為“封建流毒”而被打入徹底“肅清”之列。在“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指導下,“大義滅親”、“六親不認”、“背叛家庭”被作為革命原則或革命行動加以推崇。“文革”時期,在青少年中宣揚“老子反動兒革命”,鼓勵揭發、批判包括尊親屬在內的家庭成員的所謂“反革命”、“不革命”行為。一時間,“造反有理”的語錄被編成歌曲全國傳唱。風氣所致,1979年的《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中關于包庇罪、偽證罪以及作證義務的規定,都從根本上否定寬宥親屬間庇護犯罪嫌疑人及有權拒絕作證等內容。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修訂和1997年的《刑法》修訂,仍相沿如舊。
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第305條的“偽證罪”、第307條的“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第310條的“窩藏、包庇罪”等罪名相關條款的規定,即使是犯罪分子的近親屬為了幫助犯罪人開脫罪責、逃避國家法律制裁實施了上述條款所規定的行為,同樣構成犯罪,沒有減輕或者免除刑事處罰的規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據此規定,即使是自己的至親犯了罪,不但沒有免除作證的權利,反而必須強制履行作證的義務。這不僅與中國法律文化與法律心理的傳統完全相背,而且與人之為人的人性常情相悖,如以國家強制力來推行,難免有強人所難、撕裂人性之嫌。這樣做的后果,將導致法律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運行時國法與人情的尷尬沖突(注:《法律與生活》雜志曾討論過兩個真實案例。第一個案例是一位12歲的少年,在發現自己的親生父親有盜竊行為后,毅然向公安機關舉報。父親被捕判刑后,他的母親恨他,把他拒之門外,親戚、鄰居反感他,拒絕提供幫助,少年也同時失去了生活來源,公安部門只好與當地政府協商,由政府提供他每月的生活費直至長大 。第二個案例發生在2000年10月,湖南新化19歲村民吳靈涉嫌搶劫罪被逮捕,其母李玉蘭得知不滿18歲的人不會被判死刑后,便想用自己未滿18歲的小兒子即吳靈的弟弟和吳靈掉包。李玉蘭找村干部幫忙,在戶口本上做了手腳,司法機關查明后,李玉蘭犯包庇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前者是一個活脫脫的當代“楚之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后者之判,同樣造成這個家庭一時失去母親的困境。問題是,這看起來一反一正的兩個司法之判都不被民眾所接受。(參見:李秀平.法也容情——關于“現行法律可否‘親親相隱”研討會紀實[J],法律與生活,2001(10).))。在這樣法制背景下,佘母之類悲劇的發生就不是偶然的了。
三、東西方現代法律:確認親屬特權
中國古代“親親相隱”是一種親情倫理立法,而現代東西方主要國家法律都確認由親屬身份而自然獲得的某些例外特權,這是一種親屬權利立法。兩者存在一些類似之處,但也存在諸多根本性的差異。以下我們探討東西方主要國家的親屬特免權立法。
事實上,《大清新刑律》、《大清刑事訴訟律草案》都是參照、仿照當時的日本刑法、刑事訴訟法修定的,日本刑法學家岡田朝太郎等還直接參與《大清新刑律》的起草,所以,其“藏匿罪人及湮滅證據罪”章與當時的《日本刑法典》有同工異曲之妙。我們先從日本說起。
《日本刑法典》第七章“藏匿犯人和隱滅證據罪”第150條規定:“犯人或者脫逃人的親屬,為了犯人或者脫逃人的利益而犯前兩條之罪(藏匿犯人罪和隱滅證據罪)的,可以免除刑罰。” 第39章“贓物罪”第257條規定:“配偶之間或者直系血親、同居的親屬或者這些人的配偶之間犯前條罪(收受贓物罪)的,免除刑罰。對于非親屬的共犯,不適用前兩項的規定”。 [8]
再來看看《韓國刑法典》。其第151條(窩藏犯人、親屬間的特例)規定:“(一)窩藏犯有應處罰金以上刑罰之罪的犯人,或者協助其脫逃的,處三年以下勞役或者六十萬元以下罰金。(二)親屬、戶主或者同居家屬為人犯而犯前項之罪的,不予處罰。”第155條(湮滅證據、親屬間的特例):“(四)親屬、戶主或者同居家屬為人犯而犯本條之罪的,不予處罰。” [9]
我國的臺灣地區現行法制仍基本沿襲“六法全書”。其刑法典第162條第5項規定:“配偶、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犯第一項之便利脫逃罪者,得減輕其刑。”第167條(親屬間藏匿或頂替人犯罪)規定:“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或第165條之罪(即犯藏匿或頂替人犯罪、湮滅刑事證據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10]
我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刑法典》第328條(刑罰之特別減輕及免除)規定:“如屬下列情況,則特別減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三百二十四條及第三百二十七條所規定之刑罰或免除刑罰:…… b.作出該事實,系為避免行為人自己、配偶、收養行為人之人或行為人收養之人、行為人二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又或與行為人在類似配偶狀態下共同生活之人,在其后有受刑罰或受保守處分之危險。” [11]
上述我國臺灣、澳門地區,以及日、韓等國都在東亞地區,歷史上均屬中華法系圈內,都曾有“親親相隱”的傳統。不過,從近代以來法制的改革與法律的變遷溯源探流,這些條文卻都紹承歐洲大陸法系而來。我們只要回到大陸法系的原創地便可一目了然。
先從德國法說起。現行德國法認可親屬庇護自己犯罪的親人。《德國刑法典》第21章“包庇與窩藏犯罪”中的第258條(使刑罰無效)規定:“一、故意使他人因犯罪行為依法應受的刑罰或保安處分(第十一條第一款第八項)全部或部分無效的,處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六、為使家屬免于刑罰處罰而為上述行為的,不處罰。”[12]
《法國刑法典》第434條之一、之六規定:“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直系親屬、兄弟姐妹及他們配偶、配偶或者眾所周知同其姘居的人, 知其犯重罪不予告發或為窩藏、包庇的不處罰。” [13]
《意大利刑法典》第370條條規定:“為幫助自己的近親屬而實施為犯罪團伙、武裝團伙的人提供藏身之地、食宿的, 不予處罰。”第384條規定:“因保護自己或近親屬的自由與名譽而不得不實施包庇等犯罪的,不受處罰。”《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第169條規定:“被告人的近親屬沒有作證義務。”[14]
英美法系同樣認可親屬享有藏匿、包庇、拒證特權。在英美刑法、刑訴法中,親屬的例外特權規定主要有:親屬間相盜不能控告,尤其不許夫妻間互相指控盜竊;夫妻間相互藏匿犯罪不罰;夫妻一般不得互相證明對方有罪。不過,與大陸法系相比,其立法宗旨似乎更專注于維護夫妻雙方構成的核心家庭利益,更凸顯其個人權利觀念,因而享有這種特免權的親屬范圍小了許多,通常除了配偶,其他近親屬都被排除在外[14]3。
英國1898年《刑事證據法》規定:“在一般刑事案件中,作為被告的丈夫或妻子僅可以充當辯護證人,并只能根據被告方的申請,即不得強迫作證,不得充當控訴證人。但夫妻間互相傷害及傷害子女等案中例外。”[16]
《印度刑法典》第212條規定:“無論任何人,明知或有理由相信他人實施了犯罪,為掩護他逃避法律制裁而窩藏或隱匿:如果該人所犯罪是應處以死刑的,處可達五年的監禁,并處罰金……本條不適用于窩藏或隱匿丈夫或妻子的案件。”第216條規定:“無論何人,明知是被認定或被指控為犯有某罪而從依法被監禁的地方逃脫的人犯,或依法被命令逮捕的犯罪人,為使其免于受逮捕,而對其予以窩藏或隱匿的,按下列規定處罰……本條不適用于藏匿丈夫或妻子的案件。”[16]
綜上東西方關于親屬特免權立法,有以下兩點值得重視。其一,以權利為立法宗旨。法律認可其因親屬身份而獲得某些特免權,如藏匿犯罪親人和隱滅親人犯罪證據減免刑責之權,知親人犯罪不告發、不作證和拒絕強迫作證之權等。其二,親屬范圍較中國古代“相隱”范圍要窄小,尤其是英美法系國家,基本上狹窄到只確認夫妻間的特免權。這是由于現代西方社會家庭小型化,核心家庭普遍化所致,且即使一家人也不存在“同財共居”的財產制度。不過,日本、韓國,及我國臺灣地區在親屬特免權制度上,仍規定“同居”作為基本條件之一,體現了東方社會及儒學文化圈的某種特性。
四、修改法律:實現“親親相隱”的創新轉化
近代以降,中國社會與法律制度被迫卷入始于西方并被西方所主導的全球性現代化進程。在法律領域也表現為一個持續不斷進行西方法律移植的過程。自清末立憲修律開始,歷百有余年,基本上都是一種以西化(1949年后亦曾嘗試“蘇俄化”)為范本的“法律移植”。
在這個過程中,曾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的儒家法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沖擊,被邊緣化,甚至被妖魔化。然而,我們在大力移植、引進西方法律技術體系的同時,對于建造既富有民族特色、又有利于法律運作和實現的問題,缺乏回應與建構的能力。在我國近年來大規模立法過程中,一方面是頗具現代面貌的法律法規被成批地制定出來,另一方面卻遭遇傳統法文化類似于一種慣性的巨大沖擊與化解。中國的法治建設似乎又走到了一個歷史叉路口,仍然面臨兩種選擇,仍然聽到兩種聲音:一種聲音是主張繼續毫不手軟地摧毀傳統,其氣勢仍然很大、很牛;一種聲音是希望尊重傳統、接納傳統,充滿著文化的憂患。
問題在于,人們能否找出一個這樣的民族和文體群體,他們是由于與自己的傳統徹底決裂而實現了現代化或正在被現代化的。很遺憾,這種例子,在既不講人權也不講國權、族權的經濟殖民、資本殖民、文化殖民的歷史年代里,連老牌帝國主義者用槍炮也不曾能制造出來,在當今張揚人權和文化多元的時代則更無產生的可能。地球是平的,世界是豐富的,文化是不分優劣的。任何一個民族,歷史和傳統是其無法抹掉的印記,其文化中包含著這個民族的遺傳密碼和核心信息,不會也不能被貿然中斷或拋棄。可想而知,對于象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具有當今世界上最悠久歷史和最大族群的民族和文化體來說,何以可能輕易改變自身的文化遺傳密碼和固有的文明發展道路?
誠然,西方的一切先進文化都是我們認真學習和汲取的對象;但學習西方不是在中國復制西方。西方無法復制,也毋須復制。“全盤西化”既不正確,也不可能,是注定要碰壁的。還在100多年之前的1904年,當歐風美雨浸淫中華大地之始,有識之士就斥責這種現象為“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圣”。(注:鄧實先生之語,轉引自余英時先生著作《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參見: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M] .北京:三聯書店,2005:507.)孫中山先生也曾批判“食洋不化”之風,怒斥此等讀書人將“亂中國”:“其故在不研究中國歷史風俗民情,奉歐美為至上。他日引歐美以亂中國,其此輩賤中國書之人也。” [17]至今讀先賢之教至此,誠不免令人掩卷而扼腕三嘆!
中華法系以儒家思想為靈魂,奉行“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的治國方略,法律以家庭(家族)為本位。在古代法中,“親屬相隱”是作為維系綱常倫理的原則寫入律法,是一種恪守“孝”、“悌”義務的親情倫理立法,有違“孝”、“悌”倫理義務則入“十惡”罪加以嚴懲。到了近代,前述東西方立法,轉向以權利為本位,強調對親屬身份特免權的維護,于是而有親屬不負作證義務、減免庇護犯罪親人行為的懲罰之類法條的制定。這是基于人之為人的本性而產生的權利立法。西法東漸,清末和民國立法,“親親相隱”由是改頭換面,自覺不自覺地由體現家庭親情倫理轉為維護家庭成員因身份而自然獲得的某些特殊權利。傳統“親親相隱”的倫理立法以家庭本位為旨歸,近代以來的家屬身份特免權立法以家庭成員個人權利為基點,但兩者都承認親情本于天性,法律不能悖逆人性天理。如果說,孝親義務本于人的天性,那么,由親屬身份而獲得的沉默權、不作證權、拒絕強迫作證權、知情窩藏、隱匿犯罪親人的刑事特免權同樣本于天理。中國法律在近代化發展中,正是在家庭親情這一點上可以找到與傳統法在伸張家庭倫理上的契合點,從而融入自己的一些傳統法律元素。
現代刑法學理論告訴我們,刑法的真正目的在于通過懲罰犯罪而挽救罪犯、預防犯罪,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犯罪的社會危害。大部分罪犯在服刑期滿后,仍將回歸社會。如果法律強迫公民不分青紅皂白,必須“大義滅親”,走上法庭指控他們親人有罪的話,那么對罪犯及其親人的人性的撕裂是難以彌補的,極其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重新做人,對罪犯回歸社會、回歸家庭帶來極大的阻隔。說得更遠一點,其對人類天性可能造成根本性的傷害。從刑罰的效果看,否認親屬特免權實際上并不能預防親屬間窩藏、包庇罪的發生。我國半個多世紀來刑事司法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親屬窩藏罪、包庇罪的事實也反證親情不可違的天然合理性。對此,《漢書?宣帝紀》早就指出,“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傳統的“親親相隱”立法正是本于這一“天性”,成為儒家刑法教育預防主義的一大杰作。這是傳統親情倫理立法與現代的家屬身份特免權立法的一個契合點,即基于親情天性來強化刑法的教育預防功能。這樣做,既照顧到了民眾的倫理感情底線,又沒有對國家和社會利益造成太大損害,從而達到法律和親情的平衡,避免國家刑罰權與人類親情的直接、正面沖突。這就是傳統“親親相隱”制度提供的智慧和啟迪。
反對親屬權立法論者所持的主要理由是,可能放縱罪犯,致其逃脫法網。在公檢法實踐部門持此論者不在少數。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追查罪犯、搜集證據是國家司法機關的職責,而非一般公民的職責,不能以任何理由把國家司法機關的職責轉加于普通公民頭上,而加之到其親屬身上更是對人性的公開撕裂和對親屬權利的漠視;其二,縱算因為親屬特權而導致犯罪嫌疑人脫逃,但這種消極后果遠比存在一種撕裂人性、踐踏親權帶來的社會危害要輕。人類社會自古及今,親情無價,和諧為本,這些價值是普世的,永恒的。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爾姆斯在投票贊成宣判米蘭達無罪時留下了一句名言:“罪犯逃脫法網與官府的非法行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我們完全可以借其意而用之:為了維護親屬特權而致罪犯逃脫法網與警官和法官以法律的名義撕裂人性、踐踏親屬權利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某種意義上,法治最內在之義是對公權力濫用的防范。其三,雖然親屬享受了特權,司法機關可以要求其他人作證,這并不妨礙其搜查證據、追捕罪犯,這在操作層面完全不存在問題。
古老“親親相隱”制度對確立我國的現代親屬權利制度具有啟發,但“親親相隱”傳統的轉化創新是有所取舍的,這絕不是綱常禮教的簡單復活,而是應該建立在現代人權保障理念上的理性立法。
首先,“親屬”概念和范圍要界定清楚,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親屬身份特免權的濫用。借鑒各國立法例,結合我國立法、司法傳統和國情民意,可將我國享有拒絕作證特權的親屬限定為以下人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配偶、直系血親、兄弟姐妹、共同居住的其他親屬。
其次,借鑒古人的智慧,有必要對親屬身份特免權適用的范圍作某些限制。筆者認為,普通刑事犯罪皆可適用親屬身份特免權,但是,危及國家安全犯罪應除外,國家安全是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優于親屬權利的。此外,親屬間的犯罪,如虐待、遺棄、傷害及性侵害等,不得拒絕作證,否則有悖于該制度設立的宗旨。
第三,需要認清親屬特權的的性質。特權仍然是一種權利。權利人對自己享有的權利有處分權,既可以選擇行使權利,也可以選擇放棄權利。實踐中,當權利人選擇行使該項權利時,司法機關應當予以尊重與保護;當權利人選擇放棄該項權利時,司法機關同樣應當給予尊重,接受權利人放棄拒絕作證權利而對知曉的案件事實所作的陳述與證明。
最后,需要明確司法機關的告知程序。這一程序可借鑒“米蘭達規則”,比如對于親屬的沉默權和拒證權,司法機關向享有拒絕作證特權的親屬調查時,應當依照法定程序用明白無誤的語言告知其享有的拒絕作證的特權,該告知過程應當形成記錄,并由被告知人簽名。沒有告知,或告知程序不規范,其取得的證據為非法證據,不得作為定案根據。
由此,我們建議,我國刑法分則相關條款應作相應修改。《刑法》第105條、第107條第2款(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第310條(窩藏、包庇罪)和第312條(窩藏、轉移、收購、銷售、掩飾、隱瞞贓物罪)之后應加上“但書”條款,即“為替配偶、直系血親、兄弟姐妹、共同居住的其他親屬隱匿罪證而實施上述行為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在《刑法》分則第6章第2節“妨害司法罪”中設置一個例外性條款。該條可表述為:“配偶、直系血親、兄弟姐妹、共同居住的其他親屬為了犯罪嫌疑人、罪犯的利益,采用暴力、脅迫、賄買他人之外的手段,犯本法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零七條第二款、三百一十條、三百一十二條規定之罪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但犯危害國家安全罪除外。”同時,對現行《刑事訴訟法》亦作相應修改,確認親屬的沉默權、拒證權。只有將實體法和程序法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共同維護這一基于人性的親屬權利。
參考文獻:
[1]范忠信.中西法律傳統中的“親親相隱”[J].中國社會科學,1997,(3).
[2]郭齊勇.儒家論理爭嗚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陳璧生.親親相隱:從經典、故事到傳統(摘要)[D].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07
[4]張傳璽.對唐律“同居相為隱”規定的再認識[EB/OL].中華法律文化網(2008-07-29).http://www.ruclcc.com/article/defoudr a sp?id=230.
[5]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195-196.
[6]荀子?強國[M]
[7]漢書?宣帝紀[M]
[8]日本刑法典[M].張明楷,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2.
[9]韓國刑法典及單行刑法[M].金永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35.
[10]臺灣刑法[EB/OL]刑事審判網[2008-06-29]http://www.walaw.cn/law/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6
[11]米健,等.澳門法律[M].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7:201.
[12]德國刑法典[M].徐永生,莊敬華,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179.
[13]法國刑法典[M].羅結珍,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169.
[14]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M].黃風,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70.
[15]特納.肯尼刑法原理[M].王國慶,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571.
[16]印度刑法典[M].趙炳壽,向朝陽,杜利,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46.
[17]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1: 444.
The Plight of Kinship Privilege in Law: A Modern Transition of Qinqinxiangyin
YU Rong-gen, JIANG Hai-so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Abstract:
Qinqinxiangyin (harboring the criminal kinsperson) in ancient China is deemed a legal principle rooted in relative affections and ethics, while now in the laws of many countries both in the west and the east, certain exceptional privileges inherited in kinship are granted and the relevant laws are thus deemed legislation based on kinship right. Unfortunately, since the principle of qinqinxiangyin was denied, no legislative doctrine concerning kinship privilege has ever been accepted, which has led to .lots of sad stories and the misfortune of the defendants mother in Se Xianglin is a good example. It is in such context that the present paper observes the respective features of the ancient qinqinxiangyin based on affection and ethics and the present kinship privilege, maintains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affirmation of kinship privilege in law, and determines the affirmative values contributed by the ancient principle of qinqinxiangyi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regime of kinship privilege 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deas of modern human rights.
Key Words:qinqinxiangyin; kinship privilege; modern transformation
本文責任編輯:張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