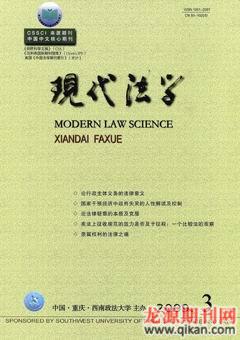論CAFTA爭端解決機制的完善
丁麗柏
摘要:若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的自身需求為依托,可以發現學界所認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許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將運用爭端解決機制的主體擴展到私主體、臨時仲裁庭的設計不合理、爭端解決機制的執行力度及懲罰措施不適當等。而該爭端解決機制在仲裁員回避、仲裁裁決形成方式及仲裁裁決的復核等方面確實存在不足,應當予以完善。
關鍵詞: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爭端解決機制;適格主體;仲裁制度;執行力度;懲罰制度
中圖分類號:DF96
文獻標識碼:A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以下簡稱《框架協議》)的簽署標志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的重大進展[1],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良好運轉不僅有利于中國與東盟各自經濟利益的提升,亦可對東亞一體化起到相當程度的推進作用[2]。為全面推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一系列配套協定得以相繼簽署。根據《框架協議》第11條之規定,有關各國于2004年11月在萬象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爭端解決機制協議》(以下簡稱《爭端解決機制協議》)便是其中之一
(注:除此之外還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政府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政府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服務貿易協議》等。)。在《爭端解決機制協議》中,中國與東盟各國約定通過磋商、調解、調停或仲裁方式解決彼此就《框架協議》及依據《框架協議》所達成的所有法律文件項下發生的爭端。
毋庸諱言,若沒有完善和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框架協議》在實施中遇到的問題便無法妥善解決,各方依據有關自由貿易協議所界定的權利和義務在未來自由貿易區運轉中亦無法得到有效保護,這勢必影響各方之間的經貿往來,并進而損及自由貿易區的前途。所以,正如WTO《關于爭端解決的規則與程序的諒解》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所發揮的作用一樣,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的制定和生效對于《框架協議》的實施有著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是《框架協議》賴以實施和發展的有力制度保障。
綜觀目前的理論與實務界,對《爭端解決機制協議》已有一定討論,其間既有宏觀的制度介紹,亦有微觀的條文闡釋。在討論過程中,除肯定《爭端解決機制協議》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積極意義外,也不乏對其所謂“缺陷”的分析及“完善”建議。筆者在此亦不揣淺陋,對諸位方家之主張試做評析。
一、關于運用爭端解決機制的適格主體問題
《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1條規定,其所稱的“起訴方”和“被訴方”分別是依據該協議第4條提出磋商請求的當事方及磋商請求所指向的當事方。從其第4條規定看,有權提出磋商請求的起訴方及磋商請求所指向的被訴方,都須為《框架協議》的締約方,而且可表達參加某一磋商愿望的主體亦須為締約方。由此可知,有權運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爭端解決機制的主體必須為協議的締約方。換言之,直接參與并承載了大量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貿易及投資活動的自然人和法人被排除在運用爭端解決機制的適格主體之外。對此,有人將其與WTO中的爭端解決機制相較,并認為自然人、法人等私主體不能利用該爭端解決機制是其“缺陷”。他們的理由在于:“在東道國與其他成員國私人發生爭端時,私人利益可能會被東道國的違法政策損害,但其所屬國政府往往基于政治風險的顧慮而不把爭端訴諸于DSB,最終導致私人投資者的利益遭受實質性的巨大損失。”[3]據此,他們主張將有權運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爭端解決機制的主體擴展到私人、企業。筆者以為,這一意見值得商榷。
首先,就當前國際貿易與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實踐看,依據《關于解決國家和其他國家國民投資爭端公約》(1965年《華盛頓公約》)所建立的“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以下簡稱ICSID)為允許私主體作為適格主體提起爭端解決請求之典型,上述學者的主張或多或少受到該公約的啟示。但我們應注意的是,關于如何解決國際貿易與投資爭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立場存在嚴重分歧:發展中國家出于維護國家經濟主權的考慮,往往傾向于通過當地救濟的方式解決國家與私主體之間的糾紛;發達國家則出于對東道國當地救濟公正性缺乏信任,更加強調通過其他方式(如某一國際機構)解決糾紛。ICSID公約所構建的爭端解決體系,正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互博弈的產物。這一體系有更側重維護主要來自于發達國家的投資者利益的傾向,從其實踐看,發展中國家在爭端解決過程中亦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片面強調私主體直接參與貿易與投資爭端的國際解決機制,不僅未必能夠確保爭端解決機制的公平正義追求,還可能不利于國家主權原則的貫徹。
其次,中國目前是僅次于美國、日本的東盟第三大貿易伙伴,并且,雙方貿易量增長勢頭迅猛[4]。可見,中國與東盟間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在此背景下,若允許私主體亦可就其主張提請爭端解決機制處理,必然極大的加重該機制的運轉負荷,這恐怕將會使那些真正需要通過爭端解決機制方可解決的中國與東盟成員國間的重大分歧的問題無法獲得及時解決,嚴重影響中國-東盟爭端解決機制的運作效率。因此,若盲目的將有權運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爭端解決機制的主體擴展到私人、企業,亦不符合爭端解決機制對效率的追求。
再次,中國與東盟成員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歷史淵源與現實聯系。目前及將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雙方雖然在經貿領域存在巨大的合作利益,但同時雙方也在政治制度、安全領域甚至國家領土主權方面留有分歧和矛盾(注: 例如,中國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文萊等東盟國家為緩和南海爭議地區的局勢,雖于2002年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重申決心鞏固和發展各國人民和政府之間業已存在的友誼與合作,以促進面向21世紀睦鄰互信伙伴關系,但事實上區內局勢并未得到根本緩解。)。在此背景下,若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一概允許私主體作為爭端解決機制的起訴方,將可能觸及某些敏感事項,在區內引發政治性問題,甚至外交摩擦。如此交惡顯然有損于來之不易的區內互信基礎,亦不利于各方經貿往來的長期穩定發展,于任意一方的核心國家利益更加相左。
最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各方均為發展中國家這一情況,決定了區內各國普遍看重注維護國家經濟主權。區內各國利益分歧仍然存在,決定了區內各國必須齊心呵護來之不易的合作局面。有鑒于此,我們理應由地區實際出發,構建合乎區內各國共同福祉的爭端解決機制。基于上述考慮,筆者并不贊同將運用爭端解決機制的適格主體擴展至私主體的主張,并認為目前將爭端解決機制的起訴方與被訴方鎖定于國家的安排是符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實際需求的。
二、對爭端解決機制中仲裁制度的爭議
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爭端解決機制所確立的磋商、調解、調停及仲裁等爭端解決方式中,尤以仲裁最為體系化、制度化。因此,仲裁制度在該爭端解決機制中居于至關重要之核心地位。關于爭端解決機制中仲裁制度,大家基于各自的分析指出了所謂的“缺陷”,并設計了若干“完善”建議。在筆者看來,這些建議中有一部分確可對爭端解決機制之完善有所助益,另一些卻不盡然。現分述之:
(一)仲裁庭的設置
根據《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7條關于“仲裁庭的組成”之規定,為解決爭議而設置的仲裁庭乃磋商無果的情況下始得成立,爭端解決完畢,此仲裁庭即自行解散。這一仲裁庭實為我們通常所稱之臨時仲裁庭。有學者對此亦有微詞,他們認為,為“便于經常性的投資、貿易糾紛得以及時有效的解決”,并使仲裁庭“變得更加富有經驗,處理問題更加高效”,應設立一個常設仲裁庭[5]。筆者對于這一建議亦不敢茍同。
首先,所謂“常設仲裁庭”這一表述的嚴謹性值得分析。根據《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7條第1款,爭端解決機制中的仲裁庭一般包括3名仲裁員。那么,這里所說的“常設仲裁庭”是否意味著由固定的3名所謂“仲裁員”來長期解決區內經貿爭端?如果是,這將與作為仲裁制度之根基的意思自治原則相悖,使爭端解決機制中的仲裁制度徒有“仲裁”之名而無“仲裁”之實。如果不是,則意味著仲裁員并不固定,而是由爭端當事方選任,既然仲裁員無法固定,又何來“常設”?還須指出的是,《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7條第1款還賦予爭端當事方約定仲裁庭中仲裁員人數的權利,既然爭端當事方可以約定仲裁庭之設置,“常設”之說更無根據。
其次,依仲裁法理,臨時仲裁通常與機構仲裁相對,據此,筆者揣測,主張設置所謂“常設仲裁庭”的學者所指的“常設”,并非“仲裁庭”的“常設”,而是希望設立一個類似于國內仲裁委員會般的“常設”仲裁機構。但即便如此,設立這樣的“常設仲裁庭”也是頗為可疑的。主張應當設立“常設仲裁庭”的學者認為這“便于經常性的投資、貿易糾紛得以及時有效的解決”,似乎是出于對仲裁效率價值的考量。但仲裁的效率價值是以仲裁員的專業性為基礎,以嚴格的期間規定為制度保障,并以“一裁終局”的裁決形式為直接體現[6]。換言之,是否采用“常設仲裁庭”的設置方式對仲裁效率優勢的體現沒有影響。在《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7條、第8條、第9條及第12條的有關規定中,都很好的考慮到了作為爭端解決機制的仲裁制度的效率性,可以說,現有的仲裁爭端解決機制在效率性方面的規定是較為成功的。如有關國家仍想進一步提高其效率的話,縮短有關程序的期間可能比設立所謂的“常設仲裁庭”更為可行。
最后,主張設置所謂“常設仲裁庭”的學者還認為這可以使仲裁庭“變得更加富有經驗”,果真有此功效嗎?仲裁作為糾紛解決方式之一,其所涉及的通常包括程序性事項與實體性事項兩大類。那么,所謂“變得更加富有經驗”,似乎就落實為對仲裁程序的更加熟練和對爭議實體問題的更加專業。但綜觀《爭端解決機制協議》中關于仲裁程序的規定,雖不能說一看便知,屬于一般經過法律訓練者可以理解的,更不用說在“法律、國際貿易、《框架協議》所涵蓋的其他事項,或者國際貿易協議爭端解決方面具有專門知識或經驗”的仲裁員的候選人了。至于爭議實體問題,從《爭端解決機制》中關于仲裁員人選的要求看,其皆為該領域的專家,既為專家,“富有經驗”當為其基本素質。如此看來,在仲裁員已經極富經驗的前提下,再談設置所謂“常設仲裁庭”以使其“更加富有經驗”似乎沒有必要。
綜上所述,設立所謂“常設仲裁庭”不僅無助于爭端解決機制的完善,反而有畫蛇添足之嫌。
(二)仲裁員的組成
《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7條第6款規定:“……此外,主席不應為任何爭端當事方的國民,且不得在任何爭端當事方的境內具有經常居住地或者為其所雇用。”該規定僅針對仲裁庭主席的選任,而不涉及仲裁庭中其他仲裁員。
筆者以為,這一規定的動機與用意頗令人費解。作為仲裁及司法這樣具有權力運用特征的第三方糾紛解決機制,其公正性至關重要,而回避制度的目的在于確保或體現仲裁及司法的公正性,歷來為制度設計者所重視。就回避的一般原理而言,凡擁有裁決權者都應屬于回避考慮之列,而《爭端解決機制協議》卻不考慮除仲裁庭主席之外的其他仲裁員的回避問題,似乎不盡合理。雖然《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7條第6款同時規定包括主席在內的各仲裁員“僅在客觀、可靠、公正和獨立的基礎上嚴格選任”,但如此單薄的制度設計可能難以消解人們因普通仲裁員回避規定的缺失而抱有的對該制度公正性的懷疑。況且,既然仲裁主席與其他仲裁員都遵循同樣的選任標準,為何又單獨提出主席的回避問題而對其他仲裁員不作規定?基于上述考慮,筆者贊同有關學者提出的“適用于仲裁庭主席的規則也應適用于其他仲裁員”的主張[3]91-98。
但這些學者提出應當編列類似于《花名冊》的所謂“合格仲裁員名單”的建議似也不可取[8]。前已述及,爭端解決機制中的仲裁庭是臨時仲裁庭,從當前仲裁實踐看,臨時仲裁對于仲裁員的選任具有非常大的自由性,只要爭端當事人認為其可公正高效地處理爭端,并且與有關回避制度不相抵牾,便可指定之。如此而言,編列所謂《仲裁員名冊》與臨時仲裁的理念背道而馳。并且,就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而言,如果將滿足專業性、獨立性和公正性要求的適格仲裁員盡數列明,其數量恐怕十分龐大,即使有某一機構不辭辛勞將如此眾多的潛在仲裁員名單編列成冊提供給爭端當事方,其功效與由爭端當事方自由選擇有何區別?其對爭端當事方又有何實際意義?質言之,這一建議既不必要,也不可行。
(三)仲裁的裁決
《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8條第5款規定:“仲裁庭應基于一致作出裁決;如果仲裁庭不能取得一致,則應依照多數意見作出裁決。”在筆者看來,這一規定可能是整個《爭端解決機制協議》中問題最嚴重的一條規定,其暗含導致仲裁裁決無法作出的邏輯缺陷。
首先,從《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7條第1款的規定看,爭端當事方可以自行約定仲裁庭中仲裁員數量。這在邏輯上意味著只要爭端當事方達成合意,仲裁庭可以由偶數仲裁員組成,這樣的仲裁庭在起草最終裁決時無法排除因“勢均力敵”而不能形成多數意見的可能。當然,偶數仲裁員的仲裁庭在仲裁實踐中不大可能出現,但不大可能出現并不等于絕對不可能出現,作為一項制度設計,理應預計到所有可能情況。
其次,退而言之,即使在仲裁庭由奇數仲裁員組成的情況下,《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8條第5款的規定亦可能導致仲裁裁決無法作出。在由奇數仲裁員組成的仲裁庭中,獨任仲裁是最簡單狀態,此時該仲裁員一人意見即為仲裁庭最終意見,上述規定不會影響裁決的作出。但在仲裁員不止一人的時候,局勢就變得復雜起來。有學者依據《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10條關于“第三方”的規定指出:在第三方介入仲裁程序的情況下,仲裁庭由于對三方責任的意見不同,可能無法依據《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8條第5款形成多數意見并作出裁決[3]91-98。這一推理是合乎邏輯的。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即使不存在“第三方”,仲裁庭組成人員同樣可能因為各自認識的不同而無法形成多數意見,這亦會使仲裁裁決不能作出。也許正基于此種擔心,國際上的仲裁實踐中如遇有仲裁庭無法形成多數意見作出裁決的情況,一般都以首席仲裁員之意見作成裁決。
最后,再退而言之,仲裁庭組成人員為在《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8條第5款的規定下仍可作出仲裁裁決,還存在采取延長討論時間以增加形成多數意見的可能。這在實踐中可暫時解決該規定所暗設之難題,但終究是治標之法,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采取延長討論時間的方式來促成多數意見是以犧牲仲裁效率為代價的,這又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爭端解決機制中仲裁制度優勢的發揮。
基于上述考慮,筆者認為爭端解決機制中仲裁裁決的作出可以參考國際上仲裁實踐的成熟經驗,在無法形成多數意見時,以首席仲裁員,即仲裁庭主席意見為準。
(四)仲裁裁決的效力
《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8條第4款規定:“仲裁庭裁決為終局,對爭端各當事方有約束力。”有學者對此亦有詬病,他們擔心會出現“因仲裁庭的組成不當或明顯超越權限,裁決賴以成立的理由不清等而使裁決不公正”,并認為應當設置裁決復核制度以審查爭端當事方依據若干理由提出的復核申請[8]。
關于這一問題,應當說,《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8條第4款賦予仲裁裁決以終局效力的規定在仲裁實踐中頗為普遍,但理論上講,作為糾紛解決制度,即使其設計的再精密,也無法完全排除不公正裁決出現的可能。倘若對這種可能缺乏相應的補救措施,將使糾紛解決制度的實效受到影響。因此,應注意的是,在仲裁實踐中同樣普遍存在針對仲裁裁決的司法監督機制以應對仲裁可能出現的不公情況。基于此,筆者贊成針對仲裁裁決設立相應的復核程序以策萬全。
但有學者認為,“裁決所依據的法律有所偏差或審理事實不清”應成為可以提請啟動復核程序的理由[5]9-13。對此筆者以為,裁決所依據的法律和對有關事實的認定已屬于仲裁庭審理過程中的實體事項,從仲裁監督機制的實踐看,實體性事項通常是排除在可監督范圍之外的。而且,從確保仲裁庭活動的獨立性考慮,也不宜對仲裁庭如何適用法律及認定事實等實體事項予以復審[6]128-156。
三、關于爭端解決機制的執行力度問題
《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12條是有關執行問題的規定。有學者認為依此規定所建構的爭端解決機制執行制度與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執行程序相比,因缺乏執行的力度而存在明顯不足。他們建議借鑒WTO的“跟隨執行監督制度”,(注:在DSM/WTO中“跟隨執行監督制度”將建議與裁決的執行自始至終地置于DSB監督之下。采取報復性措施被DSB嚴格控制,終止減讓和其他義務的范圍也被明確限定在一個數額之內,這個數額須與利益損害或喪失相符。為此,DSU還設立了救濟程序,如果認為報復措施違背了水平相當原則的,即可提請仲裁。所有這些設計既可以使建議和裁決得到執行并保障WTO的法律秩序得到實施,又可以兼顧到公平和均衡原則。)將建議或裁決的執行置于原仲裁庭的監督之下,并認為這可“使執行活動更趨透明化,形成一種強大的道義壓力,迫使敗訴方執行建議或裁決”[3]91-98。
對于爭端解決機制的執行力度問題,實際發生的案例應當最有證明力。但目前尚未有關仲裁庭裁決的執行案例見諸媒體,在此筆者只能依據《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的條文表述分析其應然的執行力度。
首先,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執行力度有目共睹,其無論在制度設計還是在實際運行層面上都得到很好體現[9]。但在邏輯上講,“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執行程序有力度”并不意味著其是最有力度的執行程序。同樣,我們也斷不可由某一爭端解決機制的執行程序與WTO爭端解決機制執行程序不一致,或缺乏與所謂WTO“跟隨執行監督制度”完全一樣的監控機制,就其缺乏執行力度。筆者以為,就執行問題而言,嚴格的期間規定有利于促使有關當事方及時的履行義務,從而避免被無故或不合理的拖延裁決,而合理的執行措施不僅有利于促成個案的爭端解決,還可有力的消解未來的潛在“爭端”。基礎上述考慮,考察某一爭端解決機制的執行程序是否有足夠力度,似乎應當以該程序對執行期間及執行措施是否存在嚴格的規定及相應的監控手段。符合此標準的執行程序,至少從制度設計而言就是一個有力度的執行程序。
其次,該機制下的執行期限也是確定根據《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12條第2款規定,如爭端各方未能在仲裁庭報告散發后的30天內就執行的合理期間達成一致,只要可能,爭端任何一方可以將此事項提交原仲裁庭審查。并且,原仲裁庭應當最遲在該事項提交其審查的45日內提交報告。可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爭端解決機制中仲裁庭的建議或裁決的執行期限問題是被置于嚴格的監督之下的,敗訴方無法毫無理由的過分拖延其執行期限。那么,就執行期限的確定性而言,爭端解決機制欠缺力度的結論?
最后,爭端解決機制中仲裁庭的建議或裁決執行的實體問題是被置于原仲裁庭的監督之下的具有確定性。《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12條第3款規定,就合理期間內是否存在為遵守仲裁庭建議所采取的措施或此類措施是否與《框架協議》相一致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只要可能,此爭端應提交原仲裁庭加以決定。并且,任何情況下,原仲裁庭都應當在不晚于該事項提交其審查的75日內提交報告。敗訴方不得拒不依據仲裁庭建議或裁決采取相應措施,亦不得采取與《框架協議》不相一致的措施。那么就執行內容的確定性而言,如何可得爭端解決機制欠缺力度之結論?
由上可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爭端解決機制的執行程序并不如某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因缺乏執行力度而存在明顯不足。我們亦無必要將該執行程序修改的與WTO爭端解決機制執行程序如出一轍而彰顯其所謂力度。
四、關于爭端解決機制的懲罰制度問題
《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13條是有關補償和中止減讓或利益喪失的規定,亦即我們通常所稱的懲罰制度。有學者認為《爭端解決機制協議》中的懲罰制度對于懲罰的措施及幅度沒有作出清晰的規定,并且該制度還可能導致懲罰權的濫用[5]9-113。筆者以為,對《爭端解決機制協議》中懲罰制度的這一詰難有失公允。
首先,補償并不是懲罰。措施在仲裁庭之建議或裁決未能在合理期限內執行的情況下,《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13條列舉了兩種可供選擇的臨時措施——補償(注:補償一般指在執行裁決的合理期限過后,這些措施仍不能修改或取消的情況下,由于該成員繼續實施這些措施而給其他受到影響的成員提供補償。補償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給其他成員更多的貿易機會,例如降低其他產品的關稅,或提供在其他方面提供更多的市場準入機會等。)和中止減讓或利益。其中,補償是承擔執行義務一方的自愿行為,而且,爭端當事方應通過談判方式確定均可接受的補償調整協議。嚴格的講,補償的自愿性表明其并不屬于懲罰措施。
其次,就懲罰的水平而言,《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13條第4款規定,中止減讓或享有利益應限于在《框架協議》項下,被認定為與《框架協議》不一致的措施符合仲裁庭建議的爭端方所享有的減讓或享有利益。這一規定雖未明確出現“懲罰與利益喪失水平相當”原則的表述,但從其措辭看,是完全符合水平相當原則之精神的。并且,該規定還對懲罰手段的范圍給予了必要的限制,以使其符合《框架協議》的宗旨和目的。由此可見,《爭端解決機制協議》中的懲罰力度上并不缺乏對懲罰幅度相當原則的考慮。
最后,關于懲罰權可能會被濫用的憂慮似乎也是多余的。前文已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爭端解決機制的懲罰制度貫徹了懲罰幅度相當原則,這樣的制度設計在很大程度上阻卻了濫用懲罰權情況的發生幾率。至于有些學者擔心的在交叉領域懲罰中可能出現的懲罰權濫用,來源于《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13條第5款第2項的規定。單就該項規定看,起訴方認為對相同部門中止減讓或享有利益不可行或無效,則可尋求中止其他部門項下的減讓或享有利益。但應注意的是,《爭端解決機制協議》中的任何規定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其他規定相互聯系而形成一緊密不可分的有機體系。因此,我們斷不可僅憑個別規定便得出結論。從《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13條第6款的規定看,懲罰措施如下:中止減讓或享有利益應是臨時性的,且只能維持至被認定為與《框架協議》不一致的措施已取消,或必須執行仲裁庭建議的締約方已經做到(該建議),或已經達成雙方滿意的解決方法。由此可見,其對于“中止減讓或享有利益”的定位主要在于彰顯這一措施的督促功能。同時,前文已述,《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13條第4款還對“中止減讓或利益”的范圍作出了明確的界定。同時,我們更應注意到《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第13條第3款規定,如在合理期限內(20天)未就補償問題達成協議,起訴方可請求原仲裁庭確定中止減讓或享有利益的適當水平。依此規定,起訴方中止減讓或享有利益的懲罰權是受到原仲裁庭監督的。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即使是在交叉領域進行懲罰,亦不會引發懲罰權的濫用。
五、結語
制定和實施《爭端解決機制協議》是落實《框架協議》的重要步驟,其對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良性發展具有戰略意義。作為一個新興的經濟合作組織,其賴以構建的各項協議不可避免的存在諸多不足,《爭端解決機制協議》亦不能外。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畢竟是一個區域性組織,其相對于其他區域性組織及WTO而言,有自身的特點和運行規律[10]。這就要求我們在探討包括爭端解決機制在內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有關制度的完善時,除以WTO及其他自由貿易區的實踐為參考外,亦應對其自身的特點和運行規律給予充分的關注,而不應處處以所謂的“國際通行原則”為準繩。因此,筆者贊同這一見解——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爭端解決的制度設計上……應當根據自身的需求來設計”[11]。基于此,筆者嘗試以其自身需求為依托,對當下關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爭端解決機制的逐步加以完善。
參考文獻:
[1] Jiangyu Wang. Two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in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Paper for Symposium 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SEAN: New Dimensions”, Singapore 3-4 Dec. 2004, pp.151-167.
[2] 韋紅.地區主義視野下的中國—東盟合作研究[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171-181,242-261.
[3] 宋錫祥,吳鵬.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爭端解決機制及其完善[J].時代法學.2006,(5):91-98.
[4] 羅林敏.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與日本—盟自由貿易區發展比較研究[J].現代商業.2006,(6):70-71.
[5] 楊麗艷,.廣西在中國—盟自由貿易區的新規則下的對策研究[J].改革與戰略.2006,2):9-13.
[6] 周江.也談仲裁第三人[J].仲裁研究.2006,4):1-8.
[7] 麻慧.中國—盟自由貿易區爭端解決機制之探討——以比較研究為視角[J].東南亞研究.2005,4):18-22.
[8] 蔡霜.WTO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爭端解決機制的比較[J].玉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7(1):73-78.
[9 David Palmeter & Petros C. Mavroidis, Dispute Settlements in WTO: Practice and Procedure,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 李榮林,等.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研究[M].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7:31-39.
[11] 沈四寶.論《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爭端解決機制協議》[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6,1):34.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SM of the CAFTA
DING Li-ba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demand of the CAFTA, one can readily find that many of the so-called “defects” detected by scholars are not defects at all, such as having not extended the disputing parties of the DSM to individuals, the design of ad hoc arbitration, or the enforcement and the punishment of the DSM. However, some flaws of the DSM can be really picked in such aspects as the challenge of the arbitrator, the formation and review of the award, which sh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DSM of the CAFTA; proper party; arbitration regime; enforcement; punishment system
本文責任編輯:徐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