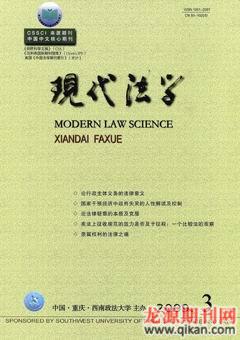“量刑規范化”解讀
摘要:何謂“量刑規范化”是研究和探索量刑規范化問題的基礎和前提,可理論上尚無明確或有價值之界定。基于對刑法現代化及量刑的實質和規律的考量,量刑規范化應是對“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規則與具體的案件
事實相結合并上升為理性與具體的過程的規范化。它表現為量刑統一化與量刑個別化的有機統一,是在尊重量刑實質和遵循量刑規律的前提下,通過設置和適用完備的程序制度,使量刑生產出公正有效及符合刑罰目的的量刑判決。
關鍵詞: 量刑規范化;量刑統一化;量刑個別化;量刑程序公正
中圖分類號:DF613
文獻標識碼:A
在2008年度中國刑法學年會上,參加“量刑規范化問題研究”專題討論的學者一致認為,對研究和探索量刑規范化的基本邏輯起點在于研究“什么是量刑規范化”問題,它也是所有關涉該主題的研究和探索必須首先回答或把握的前提性問題。然而,無論是年會專題討論,還是既有的理論著述,都缺乏對這一問題的專門探討和明確界定。(注:據充分檢索,在2008年度中國刑法學年會上有關量刑規范化問題研究的71篇論文中,沒有任何關于“什么是量刑規范化”的專門探討與明確界定。(郎勝,等2008年度中國刑法學年會論文集:刑法實踐熱點問題探索(下卷)[C]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1-558)其他報刊中題為或內容含有“量刑規范化”的文章,也基本上未對“量刑規范化”作出明確界定。)正因為對邏輯起點問題缺乏認識,各種以“量刑規范化”為名的探討,也往往有偏離或異化“量刑規范化”之嫌疑。(注:如“確定量刑基準”是否就是“量刑規范化的關鍵”?制定細密化的量刑指南是不是就是“量刑規范化”?過分擠壓量刑裁量權的所謂“電腦量刑”是否真的是“量刑規范化的現代最佳方法”?如果是,那么這些觀念和做法,實際上都具有偏離或異化量刑規范化、刑法現代化及量刑實質和規律的嫌疑。)因此,在理論上對什么是量刑規范化進行解讀,是開展量刑理論探究與實踐探索的要求使然。
一、量刑規范化是對“量刑”的規范化
“沒有規矩無以成方圓”,無論是基于“幅度過大”的法定刑立法,還是針對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自由裁量司法,沒有規范化的手段,就難以達到“方圓”的量刑目標;因此,為了公正有效地實現量刑之目標,實行量刑規范化很有必要。
至于如何實現“量刑規范化”,當前理論上和實踐中似都寄希望于量刑指南的制定和量刑基準的確定。量刑指南的制定和量刑基準的確定對量刑規范化固然是必要和重要的,但這并不是量刑規范化的全部,甚至不是量刑規范化的主體。“規范”即“標準、法式,或模范、典范”[1]和“約定俗成或明文規定的標準”[2]。所謂量刑規范化,應是使“量刑”合于約定俗成或明文規定的量刑標準。在本質上,它“不是像巴士底獄大鐘那樣的單一具體的機械實物,而是一套能生產出標準產品并更易被人接受的非人格化程序和機制” [3],即量刑規范化應是對“量刑”的規范化。作為罪刑法定原則下的司法能動活動,它應在尊重量刑實質和遵循量刑規律的前提下,通過一系列程序機制,通過“量刑”生產出公正有效及符合刑罰目的之量刑判決。
從運行規律上看,量刑并不是抽象法律規范在具體案件中的簡單對號入座,而是把抽象的法律規范與具體的案情相結合,并形成量刑判決的動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要有統一的法律規范(量刑基準及其他相關法律規范),又要有具體案件中涉及到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等問題的相關事實,還要有法官的理性、知識、良知,并通過形式邏輯(技術)和辯證邏輯(智慧)的充分論證,最終才能形成具體的量刑判決。因此,量刑在司法實質上并不是簡單的數學意義上的“刑之量化”,而應當是“刑之裁量”。這一點實際上已是我國傳統刑法理論之共識。不僅在新中國的早期刑法理論中把量刑界定為“是對犯罪分子裁量決定刑罰” [4],即使是在走向刑法現代化的今天也莫不如此,即“刑罰裁量簡稱量刑,指……”[5]。
然而,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現代化量刑似乎不再是“刑之裁量”,而是“刑之量化”。這不僅在“量刑精確制導”[6]、(注:趙廷光先生在論證“量刑精確制導”時,雖然也稱“量刑是刑之裁量”并主張量刑需要有自由裁量權,但實際上其論證均是建立在“量刑是刑之量化”的理論前提下。)“罪刑均衡實證研究”、“罪刑均衡的中國命運”等理論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而且在“層次分析法”、“數學模型法”、“定量分析法”和“電腦量刑法”等所謂現代量刑方法的探索中也有著各種嘗試。“刑之量化”與“刑之裁量”的根本不同在于,是否把量刑視為一個能動的和個別化的活動和過程。對于“刑之量化”,因作為量刑事實根據的各因素事先被數量化,而使量刑只是一個“對號入座”的、一般化的技術活動和過程,其實質是對量刑的異化;而對于“刑之裁量”,因作為量刑事實根據的各因素需針對具體案件的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判斷,從而使量刑成為一個能動的、個別化的活動和過程,這是量刑司法實質和量刑運行規律的表現。在我國立法上,《刑法》第61條就量刑的一般原則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該規定并不是把量刑視為“刑的量化”,而是“刑的裁量”。因為按照通說,該規定所蘊涵的量刑事實根據,并不只是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因素,它還包括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因素,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因素是很難事先量化的,需要根據具體案件的具體情況進行裁量。
既然量刑的司法實質是“刑之裁量”,而非“刑之量化”,那么,量刑時必須具有自由裁量權。(注:需要自由裁量權,是“刑之裁量”不同于“刑之量化”的關鍵所在。)所謂自由裁量權(Discretion),并不是“任意的裁量權”。根據國外學者的解釋,它是指酌情作出決定的權力,并且這種決定在當時情況下應是正義、公正、正確、公平和合理的[7]。據此,可以認為,自由裁量權在本質上是一種依法酌情作出決定的權力。歷史和現實均表明,在量刑與自由裁量權的關系上,一方面,量刑中沒有自由裁量權不行,那種因存在量刑不公而擠壓自由裁量權的做法,在本質上是一種專制主義的做法;(注:所謂專制主義,孟德斯鳩把它比喻為,“路易斯安納的野蠻人要果子的時候,便把樹從根柢砍倒,采摘果實”。(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M]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69))沒有自由裁量權的所謂量刑,并不是真正的量刑。那種僅以法律規范和原則為依據,而不要考慮具體案件的事實、法律原則、案件的社會影響、道德、倫理、政策等因素的所謂司法克制主義,不僅違背了量刑規律,而且帶來了量刑的實質不公,甚至給社會帶來災難;(注:“佘祥林案”、“被虐婦女殺夫被處死刑案”都是其中的典型例證。)另一方面,對自由裁量權不加限制的所謂絕對司法能動主義,也是不行的。從現實情況來看,在法官素質參差不齊的情況下,法院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控制確有必要,但并不能限制過多,因為量刑要考慮的因素是綜合性的,而且也應該鼓勵法官在量刑的過程當中能夠深入地研究法律或者去探尋可能影響量刑的各種情節;如果幅度太小,容易形成法官的一種機械選擇的弊端,對法官進一步探尋可能影響量刑情節的因素是不利的[8]。事實上,依據實質性的罪刑法定原則和量刑實質及規律,量刑的自由裁量權并非是任意的,而是必須受案件事實、法律規定(包括刑法的基本原則及內化于相關規定中的基本刑事政策、刑法的時代精神等)的限制,即它須依案件事實和相關法律能動地行使。(注:在這個意義上說,自由裁量權之“自由裁量”,并不意味著“任意裁量”,而是“能動地綜合各種相關因素判斷決定”。)
自由裁量權的立法設置源于許多方面的原因。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學者看來,設置自由裁量權主要源于如下3個原因:第一,因沒有任何法律可以預期各種具體情況,而必須設置自由裁量權以決定對具體事實情況的判斷適用怎樣的法律;第二,因法律或禁令往往過于龐雜,而必須行使自由裁量權以確定哪種規定優先適用;第三,在刑事程序中,行使職權者為了追求正義(實質),也需要自由裁量權以便在刑事程序運作中發揮個人價值的實質性作用[9]。就作為成文法的刑法典而言,自然也完全符合自由裁量權設置的3個原因,因而刑法典的適用必須有自由裁量權。那種希望“無論遇到多么復雜的情況都能在龐大的法典中像查字典一樣檢索到現成的解決方案”和“法官的作用就像機器,就如同自動售貨機投入硬幣就能出來商品一樣,將案情與法條投入法官的大腦就能產生判決結果”,只是絕對主義的思想或方法。“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只有在適用中才能對社會生活產生作用,離開了法的適用,法只是一種純粹的語言條文形態,是一種沒有生命的“死法” [10],而量刑卻能使“死法”向“活法”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不應簡單地把抽象的法律規范應用于具體個案,而應使抽象法律規范與具體案件事實相結合,形成理性具體(量刑判決)。其中,無論是“抽象法律規范與具體案件
事實相結合”還是“理性具體的形成”,都不是自動生成的,而均需通過能動地行使自由裁量權才能實現。
司法的發展歷史也表明,量刑不能沒有自由裁量權。在近現代刑法發展中,刑事古典學派主張嚴格的規則主義,否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他們認為,“當一部法典業已厘定,就應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刑事法官根本沒有解釋刑事法律的權力,因為他們不是立法者”;一個作出終極判決的司法官員,“他的判決是對具體事實做出單純的肯定或否定” [11]。法官只能宣告被告人犯了某一罪行,而對罪行的處罰,從當時制定的各種法律中就可以看到;按法律的規定宣布刑罰,法官只要用眼睛一看就夠了[12]。他們還主張,立法者“試圖對各種特殊而細微的實情開列出各種具體的、實際的解決辦法,它的最終目的是想有效地為法官提供一個完整的辦案依據,以便使法官在審理任何案件時都能得心應手地引經據典,同時又禁止法官對法律作任何解釋” [13]。然而,現實證明,這些都只是不切實際的美妙設想而已。對此,刑事近代學派對其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并主張符合刑法現代化特質的相對規則主義。其中,菲利認為,“無論從立法來看,還是從司法來看,犯罪分子不再是具體的人,而是法官可以在其背上貼刑法條文的標本。如果在其背上貼的不是407條而是404條,上訴法院則反對再進行任何數目的更改” [14],這顯然是不合適的。他主張,刑事法官必須有自由裁量權,因為,將法令適用到具體案件中去必須從心理學角度把某個抽象的條例適用于活生生的人;刑事法官不能將自己與環境和社會生活割裂開來,成為一個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機械性質的法律工具;每個刑事判決對人的靈活鑒定都取決于行為、行為人和對其作用的社會情況等,而不取決于成文法[15]。李斯特也認為,絕對確定之刑罰,只有逐步讓位于法官對刑罰的自由裁量時,才能稱得上“量刑” [16]。
既然量刑在運行規律上必須有自由裁量權,則在量刑規范化中就需要遵循量刑的這個運行規律,保留必要的自由裁量權。在歷史上,曾有過不遵循這一規律的深刻教訓,貝卡里亞設想的嚴格規則主義及以此為理論基礎制定的1791年《法國刑法典》的失敗,(注:這個試圖擠壓法官自由裁量空間的法典,不僅在現實中行不通,而且很快就被有相當裁量空間的1810年《法國刑法典》所淘汰。)就是其中的例證。那些以法官素質參差不齊、量刑不公等為由而過分擠壓量刑自由裁量權的所謂量刑規范化做法,都是違背量刑規律的,都將使“量刑”名存實亡。
二、量刑規范化并非絕對反對“同案異判”
量刑不均是世界各國司法中的一大詬病,它不僅影響法院的公信力(量刑權威),而且也有損量刑的公正和有效性。現實表明,我國存在極其嚴重的量刑不均問題,這顯然與走向現代化的我國刑事司法目標不相適應。于是,我國各級法院展開了聲勢浩大的、以解決“同案異判”問題為目標的量刑規范化改革,如制定細密化的量刑指南、構建“同案同判”的案例指導制度[17]、開發擠壓法官量刑裁量權的“電腦量刑”等。與這些
做法相一致,理論上有論者干脆就把量刑規范化等同于“同罪同罰”,認為“量刑的規范化,即同罪同罰,相同的罪行相同的情節,它的量刑結果是相同的” [18]。然而,“同案異判”是否就等同于“量刑不均”呢?例如,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房地產管理局原局長方某受賄51.6萬元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并處沒收財產3萬元;而江西省上高縣田心鎮教辦會計陳某貪污11.8萬元,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這兩個案例源于《檢察日報》2002年3月23日的報道。據此,有論者判定這就是“量刑不均”,認為這將影響法院的公信力和量刑的公正性等。
筆者認為,以上案例是否屬于“量刑不均”,還有待綜合考慮各自
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因素,包括各種法定和酌定從寬或從嚴量刑情節之后,才能作出合理判定。僅就媒體報道的有限信息來看,兩個案例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不可同日而語。就社會危害性而言,對于房地產管理局局長,其行賄者往往“腰纏千萬”,50多萬的受賄數額并不很大;而對于鎮教辦會計,其經費是老百姓的血汗錢,10多萬的貪污數額已是天文數字,這樣,后者的社會危害性似乎更大一些。(注:數額犯的量刑不能簡單地依數額而論,已是理論上和實踐中的共識。)就人身危險性而言,對于房地產管理局局長,因其地位和權力的誘因,受賄也往往具有某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社會因素;而對于鎮教辦會計,利用職務之便貪污“血汗錢”,其人身危險性可想而知。因此,這兩個案件并不能簡單地當成“量刑不均”之例證。(注:雖然“判3緩5”的量刑結果確有量刑畸輕的嫌疑。)
實際上,“同案異判”與“量刑不均”是根本不同的兩個問題。對于前者,雖然非理性的“同案異判”確屬“量刑不均”而應擯棄,但理性的“同案異判”不僅不是“量刑不均”,反而
體現了量刑的實質公正。一向注重刑法精密化的德國在長期追求“量刑統一”未果后承認,基于多種原因,不同地區間的量刑差異不僅是合理的,而且還是法律和公正所追求的目標之一[19]。(注:在德國,經驗研究表明,量刑決定確實存在著地區間和個體上的巨大差異。例如,在1985年至1986年,對于情節嚴重且有前科的盜竊犯罪人,一個州的法院科處7.9%的絕對自由刑,而相鄰的另一個州的法院科處56%的絕對自由刑。此等巨大的差異在過去被認為不僅是與公正性相矛盾的,而且引起了人們對法律關于同等對待要求的懷疑。但是,在理性地審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后,人們現在對量刑上的地區差異已經看得不那么重。) 我國近來也有不少學者發現,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各地發展不平衡,這必然影響到不同地區的法官對“相同案件”的違法性與有責性的評價,因而必然造成量刑上的差別[20]。確實,“同案不同判”關注到了一些必須重視的重要差異;相反,那種齊頭式的等同處理(劃一式的“同案同判”)有時會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差異。因為,對于“同一時空條件下的性質相同、情節相當的犯罪”,不僅社會危害性可能不同,而且人身危險性也可能不同;并且對于不同案件“適用相同的法律”只是表明這些案件的“量刑基準”相同,而不意味著它們的量刑結果也必須相同(量刑本身就是運用量刑情節對量刑基準的修改和變更)。因此,雖然量刑規范化以實現“量刑均衡”為重要目標,但它并非要絕對地消除“同案異判”和“同罪異罰”,并不等同于量刑統一化。在當前我國的量刑規范化中,把量刑規范化下的量刑均衡等同于量刑統一化,實際上是對量刑均衡的曲解和對量刑規范化的異化。
(一)量刑均衡并非絕對否定“同案異判”
所謂均衡,即平衡,是指矛盾暫時的相對統一或協調,是事物發展穩定性與有序性的標志之一[1]51。由此,所謂量刑均衡,并不是指量刑統一,而是量刑和諧。所謂和諧,并不是絕對否定或消滅差異,相反,它是以差異的存在為前提,沒有差異也就無所謂和諧,它以均衡、協調、整體發展為根本特征。所謂量刑和諧,就是指某個具體案件的量刑系統中各不同要素之間的有規律排列,也就是量刑結果依法與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具體情況(即罪和責)相適應,即量刑個別化。因此,基于量刑和諧原理,正確的做法不是不要量刑差異,而是考察這些差異是否體現了罪責刑相適應。這就意味著,對于“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只要其各事實情節能夠得到適法和適當的處理,就實現了量刑均衡。當然,并非所有差異都能構成“和諧”。差異有積極差異與消極差異之分,就量刑而言,前者指適法適當下的差異,后者指不適法不適當下的差異;前者表現為量刑和諧即量刑均衡,后者表現為量刑不和諧即量刑不均衡。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量刑均衡在本質上是一種適法適當(合法合理)下存在量刑差異(同案異判)的量刑和諧。
(二)量刑均衡是量刑統一化與量刑個別化的辯證統一
基于哲學上一般與個別的辯證關系原理,量刑規范化下的量刑均衡實際上是量刑統一化與量刑個別化的辯證統一。具體而言,從哲學上看,所謂個別,指單一事物的個體性、獨特性,它使事物彼此區別;所謂一般,指一類事物或一切事物普遍具有的共性和本質,它反映事物的普遍聯系和統一性。一般與個別是辯證統一的,一般不能脫離個別而存在,共性寓于個性之中,沒有個性就沒有共性;個性又總是同一般相聯結,個性體現出共性,并為共性所制約[2]378。因此,量刑統一化(又稱量刑一般化)與量刑個別化是一組相對的概念。所謂“量刑統一化”,是指在不考慮量刑情節的情況下,同樣的案件應當有同樣的量刑基準,即所謂的“同案同判”、“同罪同罰”;所謂“量刑個別化”,是指每個具體案件有其個體性的量刑結果,表現為量刑結果與反映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和其他方面的事實相適應。從表面上看,量刑統一化與量刑個別化似乎是矛盾和沖突的,但實際上它們是有機統一的,這表現在量刑統一化只是針對抽象個罪,而量刑個別化是針對具體個罪。這個“抽象個罪”與“具體個罪”的關系,實際上就是哲學上一般與個別的關系,這決定了量刑個別化不僅不是對量刑一般化的否定,而且還是以量刑一般化為前提的。
(三)量刑均衡是量刑基準與量刑情節共同作用的結果
量刑基準和量刑情節是實現量刑規范化的核心因素,量刑統一化與量刑個別化分別取決于量刑基準與量刑情節。就量刑基準而言,它是量刑統一化的基本表現。在本體上,量刑基準是在具體犯罪定罪中確定的特定法定刑,是直接由定罪活動為量刑活動提供(確定)的[21],因此,確定“量刑基準”的事實根據不是量刑情節,而是定罪情節。(注:理論上雖然沒有人這么說,但實際上也是在主張“確定量刑基準的事實根據不是量刑情節,而是定罪情節”,因為認為量刑基準是“在不考慮任何量刑情節的情況下僅依其構成事實所應當判處的刑罰量”,這在本質上就是認為量刑基準是在定罪活動中依定罪情節確定的相應的具體法定刑。)這意味著:在立法上,量刑基準是同類抽象個罪所需刑罰量的概括,體現了以一般社會報應觀念和社會公正觀念對犯罪行為的價值評價,并與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相均衡;在司法上,它體現著“同案同判”,是量刑統一化的基本表現。在司法實踐中,量刑一般化表現為以刑法基本原則為指導,以事實為根據,以刑事立法為準繩,即對于任何人都適用同樣的法律規范,而不是因人而異或者因事而異。因此,所謂量刑統一化及“同案同判”或“同罪同罰”,實際上不是要求具體個罪的量刑結果相同,而主要是要求“同案”、“同罪”適用同樣的量刑基準。就量刑情節而言,它決定了量刑的個別化。量刑情節是量刑中(而不是定罪中)據以決定刑罰輕重的情節(主客觀事實情況),與定罪情節不同,它對確定作為量刑基準的法定刑不起作用,而只對量刑個別化起作用。量刑個別化在本質上是將量刑基準與量刑情節及《刑法》總則的相關規定相結合,而使量刑結果與反映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和其他方面的事實相適應,它雖然要求“同案”、“同罪”的量刑基準相同,但不必然要求量刑結果“相同”或“不同”。
綜上,量刑個別化與量刑統一化都是量刑規范化的必要組成部分,量刑規范化下的量刑均衡是量刑一般化和量刑個別化的有機統一[22]。在司法實踐中,有兩種錯誤傾向:一是片面強調量刑個別化而忽視量刑一般化,表現為片面強調量刑的個人情況而忽視其罪行的危害性大小以及法律的明確規定,造成處罰過重或過輕,這是不正確理解量刑個別化的結果。二是片面強調量刑統一而忽視量刑個別化,表現為試圖以極其細密化的量刑規范擠壓法官裁量權,試圖實現劃一性的同案同判,(注:實踐中流行的“不怕不合理,就怕不一致”的說法,就是這種片面傾向的反映。)搞“一刀切”,不問犯罪人的具體情況,不問是否有利于犯罪的改造和回歸社會情況等,這同樣是誤解量刑個別化的結果。因此,在當前的量刑規范化改革中,針對實踐中存在的量刑裁量權濫用、量刑不規范、不統一等錯誤的量刑做法,正確的做法不是片面地強調量刑統一化和違背量刑規律去擠壓量刑裁量權,而應當是采取措施(設置獨立的量刑程序、完善量刑機制等)規范量刑裁量權的行使,使量刑一般化與量刑個別化的關系得以協調。案例指導制度等量刑規范化措施,其正確目標只能是為了統一量刑標準,解決法律規范層面上的“同罪不同罰”問題,而不能不加區別地要求量刑結果“同案同判”、“同罪同罰”或“基本一致”。 (注:量刑結果公正并不意味著在同一時期、同一地區以及同一法院對于具有類似情節的類似犯罪的刑事被告人的量刑結果應當基本一致,而應當是具體案件的罪責刑相適應。)
三、量刑規范化的關鍵是實現量刑程序公正
量刑公正是量刑的基本價值理念,也是量刑規范化的終極目標所在。在理論上,基于程序與實體的相對關系,量刑公正有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之分。所謂程序公正,是指對犯罪人的量刑權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人民法院必須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序行使量刑權;所謂實體公正,是指對犯罪人裁量、決定刑罰時要做到罰當其罪、罪刑相當、不偏不倚,即人民法院對犯罪人的量刑,必須根據《刑法》分則和總則的不同規定,判處最能適應犯罪的客觀危害和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的刑罰。(注:需要指出的是,實體公正不等于實質公正,程序公正不等于形式公正。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都是實質公正與形式公正的有機統一體。程序公正,除了具有保障實體公正的工具性價值外,還有其獨立價值,如程序公正具有“以公開促公正”的效果,能夠實現“看得見的正義”。)
綜合以上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理解,所謂量刑公正是指“人民法院對犯罪人裁量、決定刑罰時要做到依法進行、罰當其罪、罪刑相稱、公平裁判、不偏不倚” [23]。這是一種相對全面和深入的量刑公正觀,它應當比舊派和新派關于量刑公正的認識要全面和深刻,而且也應當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關于量刑的認識要全面和深刻。在量刑問題上,重實體輕程序已是中國傳統量刑問題的突出特點。傳統觀念認為無論程序如何,只要結論是公正的,就是司法公正。而筆者提到的以上量刑觀,表現出實體與程序并重、定罪與量刑并重、報應與預防并重等理性主義特點,能促進量刑走向現代化。顯然,量刑不能片面追求實體公正,忽視程序公正,否則,即使實體公正,也是失去理性的量刑,猶如算術沒有過程,結果對錯也就無從知曉。當然,量刑也不能片面強調程序公正而忽視實體公正,否則,即使程序公正,也是失去靈魂的量刑,猶如市場檢查只看包裝及其標識,品質如何在所不問。如果堅持這兩種片面的觀點,前者必然導致諸如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堂而皇之地在量刑中被使用;后者也定會出現“白馬非馬”的荒唐。因此,對于量刑公正的追求,正確的做法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并實現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有機統一。當然,“有機統一”并非意味著在量刑實踐中對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須予以同等程度的關注。既然量刑的實體公正必須通過公正的量刑程序才能實現,針對我國歷來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程序公正常常被認為是可有可無的東西這樣的情況,我們應當對程序公正予以更多關注。
當前,理論上和實踐中有一觀點,認為法院量刑公信力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同案不同判”。實際上,這是基于“同案同判”的片面認識而作出的不客觀判斷。如前所述,“同案同判”只能是對量刑基準的要求,不能是對量刑結果的要求;量刑結果公正并不意味著“同案同判”,而是意味著量刑結果與具體案件事實的罪責刑相適應。把量刑結果公正等同于“同案同判”的量刑規范化,只是一種表面上的形式公正,實際上追求的僅是量刑統一化,因規避量刑個別化而必然帶來實質上的量刑不公。這種表面上的公正,因當前缺乏公開、獨立的量刑程序,而使得當事人誤認為其判決是公正的,實際上這只是一種對《刑法》規定作淺層次理解的表面公正。這種所謂公正,在其實質不公的內容沒被曝光時,可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贏得量刑公信力,但在其實質不公被揭示后,不僅不會贏得公信力,反而會嚴重損害公信力,“許霆案”、“彭宇案”就是例證。因此,試圖通過“同案同判”和量刑的形式塑造所謂的“量刑公信力”,只是一種誤解;只有建立在量刑實質公正上的量刑公信力,才能經得起時間和事實的考驗。在刑法現代化中,在重視權利的時代,我們應當把重心放在保障人權的實質公正上。
實際上,量刑實質公正的實現更需要量刑程序公正予以保障。從當前的量刑實踐來看,如果說量刑形式公正是利用其“看得見的公正”來塑造量刑公信力的話,那么量刑實質公正對量刑公信力的塑造,同樣需要采用類似方式,即充分闡述量刑理由使量刑結果為當事人及民眾所理解和接受。從司法實踐來看,眾多的上訴、申訴及“輿論殺人”、媒體干預司法等現象以及由此導致的量刑公信力受損的問題,在本質上不是由于“同案不同判”,而是由于當事人、民眾、媒體等不了解、不理解、不接受量刑裁判所至;倘若法院能使當事人、民眾、媒體等了解、理解和接受量刑結果,不僅不會帶來如此眾多的問題,而且量刑公信力也不會由此受損。
通過充分闡述量刑理由使量刑結果為當事人及民眾所理解和接受,以塑造量刑公信力和實現量刑實質公正,關鍵是要設置獨立的量刑程序。目前理論上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一直以來就非常重視程序對于量刑公正的保障作用,如在二審中將存在程序違法的一審量刑認定為無效,以審判的級別管轄來控制法官量刑的最高限度,規定公開審判和不公開審判案件的量刑結果一律應當公開,設置專門的死刑復核程序以保證死刑的公正適用,建立審判監督機制和法官錯案責任追究制,保證量刑公正[24]。然而,這些制度與程序往往都只是從審前和審后兩方面對量刑公正予以保障,在量刑的核心——審判程序中則缺少程序的要素和程序進路的載體,以體現控辯雙方對量刑的程序參與等核心要素[25]。為此,設置獨立的量刑程序并使量刑階段相對獨立化,就成了實現量刑實質公正的必然選擇。由于獨立化量刑程序是量刑程序公正的司法表現和現實保障,獨立而又完備的量刑程序應達到以下要求:設置上必須基于量刑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辯證關系,體現量刑程序公正的正當化要求,賦予當事人充分參與量刑程序、徹底知情量刑理由、取得必要法律幫助、獲得完全法律救濟等方面的權利。因此,設置獨立的量刑程序,也是量刑規范化的關鍵措施。
結語綜上所述,所謂“量刑規范化”,是對“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規則與具體的案情事實相結合,將其上升到理性具體的過程以實現規范化。它是在尊重量刑實質和遵循量刑規律的前提下,通過設置和適用完備的程序制度,使量刑生產出公正有效及符合量刑目的的量刑判決。它具有如下幾個基本特征:一是它須反映和體現刑法現代化。刑法現代化語境下的量刑規范化,不能以刑事古典學派時期的絕對形式主義的原理為根據,而應與現代刑法的原則、理念和方法保持一致。二是它必須尊重“量刑”的實質,即量刑不是刑的量化,而是刑的裁量,是把抽象的法律規則與具體的案件事實相結合并上升到理性具體的過程。三是它應是量刑統一化與量刑個別化的統一,量刑因有統一的量刑基準和其他統一適用的法律而使量刑規范化表現為量刑統一化,同時,
量刑過程中需要做到量刑結果與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等相適應。四是基于量刑的實質和運行規律,量刑規范化的實現最主要的不是制定具體化的量刑指南和量刑基準,而是設置和適用完善的量刑程序制度。
參考文獻:
[1]辭海(縮印本)[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1743.
[2]現代漢語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513.
[3]胡水君.懲罰技術與現代社會——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的現代意義[J].社會學研究,2007,(3):232.
[4]高銘暄.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251.
[5]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71.
[6]趙廷光.論量刑精確制導[J].現代法學,2008,(4):89-106.
[7] 戴維?M?沃克.牛津法律大詞典[M].鄧正來,等,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261.
[8]周光權.量刑規范化:可行性與難題[J].法律適用,2004,(4):63.
[9]彼得?G?倫斯特洛姆.美國法律辭典[M].賀衛方,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157-158.
[10]陳興良.刑法的人性基礎[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6:568.
[11]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M].黃風,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3:9-13.
[12]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M].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76-77.
[13]梅里曼.大陸法系[M].顧培東,等,譯.重慶:西南政法學院編印,1983:42.
[14]菲利.實證派犯罪學[M].郭建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175-176.
[15]菲利.犯罪社會學[M].郭建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244.
[16]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M].徐久生,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63-464.
[17]劉作翔.我們為什么要實行案例指導制度[J].法律適用,2006,(8):5-8.
[18]陳興良.“電腦量刑”專家評審意見[G]//北京:淄博市淄川區人民法院.電腦輔助量刑:淄川區人民法院規范量刑探索和實踐.淄博:山東省淄博市新聞出版局準印,2006:208.
[19]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威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總論)[M].徐久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1045-1047.
[20]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433.
[21]石經海.刑法分則的司法本質與量刑基準的界定[C]// 郎勝,等.2008年度中國刑法學年會論文集:刑法實踐熱點問題探索(下卷).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123-133.
[22]石經海.量刑個別化研究[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8:89-92.
[23]沈德詠.論量刑公正[G]// 北京:中英量刑問題比較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1-28.
[24]葉青.量刑公正的訴訟程序保障機制[J].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1,(5):44-45.
[25]仇曉敏.量刑公正之程序進路[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7,(6):84-85.
Interpret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of Sentencing
SHI Jing-ha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China)Abstract:
Standardization of sentencing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condition of studying normalization of sentencing. Unfortunately, as of it has no express or significant definition in theory. Based on moderniza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the substantial norms of sentencing, standardization of sentencing should be deemed as a sentencing process where abstract legal rules apply in specific cases and yield rational principles, which embodies an organic integration of .unific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of sentencing. On the premise of respecting the substance of sentencing and observing sentencing principles, by way of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procedural system and following the procedures, a fair and legitimate sentence is expected to be made that quite meets the purpose of penalty.
Key Words:standardization of sentencing; unification of sentencing; individualization of sentencing; fairness of procedure of sentencing
本文責任編輯:梅傳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