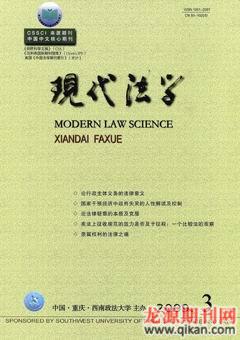憲法上征收規范的效力是否及于征稅:一個比較法的觀察
劉連泰
摘要:憲法上的征收規范一般不拘束征稅。從德國法和美國法的情形來看,憲法上的征收規范對征稅具有“弱拘束力”,只有在極端情形中,征稅可能因違反征收規范而無效。《德國基本法》上的征收規范對征稅的拘束力主要表現為“半數原則”,美國憲法上的征收規范對征稅的拘束力主要表現為“極其武斷的征稅構成沒有補償的征收”。《德國基本法》和美國憲法的規則對解釋中國憲法上的征收規范具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 征收;征稅;拘束力
中圖分類號:DF2
文獻標識碼:A
我國《憲法》第13條第3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對該規范最近幾年聚訟紛紜,但爭議多圍繞拆遷補償糾紛展開(注:近幾年爆發了一系列影響較大的拆遷補償糾紛。先后有重慶最牛的“釘子戶”案,深圳最貴的“釘子戶”案,長沙堅持時間最長的“釘子戶”案。重慶最牛 “釘子戶”案源自重慶市鶴興路片區項目改造,該改造項目由一家開發商執行。開發商和政府從2004年8月31日貼出動遷公告。該片區有住戶281戶,280戶接受安置方案,已經搬走。住戶吳蘋不接受安置方案,拒絕搬遷。法院裁定該房產應該拆遷,但吳蘋認為法院裁定書不合理,仍然決絕搬遷。于是,整個片區只有一幢房屋矗立在工地的中央。被網友稱為“最牛的釘子戶”[EB/OL]http://news.sina.com.cn/s/2007-03-09/032512468160.shtml.2008-10-10長沙堅持時間最長的“釘子戶”案源自2004年長沙市啟動的長沙南門口一帶的舊城改造。開發商和政府的拆遷公告發布后,絕大多數住戶都已搬遷。但周姓業主等三人認為補償標準過低,要求置換同地段的商鋪,或者每平方補償三十萬,否則拒絕搬遷。于是一座房屋孤零零地矗立在長沙步行街門口。至今已近4年。http://www.6318.cn/tb/jd/200711/179012.html.2008-10-10深圳最貴的“釘子戶” 案源自深圳金融一條街的建設,蔡珠祥在公告的拆遷地段有779.81房產,當初造價為120萬,2005年深圳市政府要求拆遷,蔡珠祥拒絕接受評估價。最后,政府妥協,支付給蔡珠祥人民幣1200萬元的補償。[EB/OL]http://soufun.com/news/2007-10-29/1302886.htm.2008-10-10)。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該規范中的征收是否包括征稅?如果不包括,就意味著中國憲法文本中有兩個征收的概念——“財產征收”中的“征收”,“稅款征收”中的“征收”。這又進一步延伸出這樣一個問題:“財產征收”中的“征收”與“稅款征收”中的“征收”有什么差別?也就是說,征收規范的效力能否邏輯地延伸到征稅?
征收規范與公民的財產權保障密切相關。從宏觀的角度觀察,憲政最早起源于對財產權的保障:英國《大憲章》不過是一紙限制國王征稅權的契約,憲政也不過是從“無代議士不得納稅”這一理念生發的控制國家權力的機制。但從發生學的角度理解征收規范對征稅權的限制無益于解決當下的問題。從發生學的角度看,對國家征稅權的限制是為了保障公民財產權,但其中的財產權應是自然法意義上的財產權(注: 許多學者已注意到財產和憲法的關系,有的學者甚至提出財政憲法學的概念。這些宏觀的論證路徑大多從憲法的產生開始論證,其中的公民財產權概念更接近自然法的理解。參見周剛志.公共財政與憲政國家——作為財政憲法學的一種理論前言[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3.朱孔武.財政立憲主義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6.179.當然,也有學者當然認為征收規范適用于征稅,參見錢俊文.征稅權的合憲性控制[M].法律出版社,2007:184.)。進入憲法文本的財產權已然脫胎換骨,是規范意義上的財產權。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作為財產權規范有機組成部分的征收規范是否構成對征稅的制約?
“比較法能使我們超越比利牛斯山”[1]。看看域外的情形,對我們會有諸多啟迪。從德國法和美國法上的情形觀察(注:這里不可回避的追問是:憑什么選擇德國和美國而不是別的國家?標本的選取參考了我國臺灣地區學者陳新民先生的著作,參見陳新民.法治國公法學原理與實踐(上)[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277.在論及“憲法財產權保障之體系與公益征收之概念”時,陳先生加了個副標題:“德國與美國的比較研究”;陳新民先生是留學德國的學者,德國法的知識背景毋庸質疑,在論述財產權和征收規范時,為什么要從德國法和美國法的比較中展開?另一篇美國學者的文章同樣可以給我們提供這樣的思路,美國康奈爾大學的G. S. 亞歷山大教授發表的《財產權是基礎性權利嗎?》,同樣加了副標題:以德國為比較項。參見[美]G. S. 亞歷山大.財產權是基礎性權利嗎?——以德國法為比較項 [C].鄭磊,譯載胡建淼主編.公法研究(第五輯),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413.這種不約而同的標本選取方式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信息:德國法和美國法代表了財產權和征收規范的兩種典型模式。正如陳新民先生所說:“由于德國及美國界對財產權的保障,以及涉及本問題的其他法律問題,早已進行深入之研究……”。盡管德國法、美國法,之后中國法的敘述思路落入俗套,卻屬不得已之舉。),可以看出征收規范對稅收有“弱”拘束力。
一
《德國基本法》中的征收規范位于第14條。
“一、財產權及繼承權應予保障,其內容與限制由法律規定之。
二、財產權負有義務。財產權之行使應同時有益于公共福祉。
三、財產之征收,必須為公共福祉始得為之。其執行,必須由法律或依據法律始得為之,此項法律應規定賠償之性質與范圍。賠償之決定應公平衡量公共利益與關系人之利益。賠償范圍如有爭執,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訴訟。”
1993年前,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基本立場為,《德國基本法》上財產財產權保障,對金錢給付義務的課征不適用該條[2]。也就是說,該條中的財產是指特定的財產。而納稅義務使特定人負擔特定金錢給付義務,只就該特定人總體財產減少,對具體財產權并未侵犯。這一原則最早為1954年聯邦憲法法院所主張[3]。嗣后則認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如過度,致根本上損害其財產關系或產生沒收與“絞殺”效果時,則違反《德國基本法》第14條[4](注:陳新民教授將“絞殺效果”翻譯為“勒死效果”,將產生這種效果的稅捐稱為“勒死式稅捐”,德文單詞為Erdrosselungsteuern. 該概念是由W. Weber提出的。參見W. Weber, Eigentum in der Krise, S.335.轉引自陳新民.法治國公法學原理與實踐[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287.)。但迄今為止,沒有一部稅法因這一理由而被宣告違憲。也就是說,財產權條款只有在非常極端的情況下,即過度課征時,才及于金錢給付義務。
聯邦憲法法院的這一立場經歷了來自學界和實務界的諸多批評,卻并未從根本上動搖。如何認定“過度課征”?1993年到1995年,聯邦憲法法院發展出“最適財產權課稅理論”。具體內容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一)財產稅方面(以動產、不動產以及其它財產的權利價值為征稅客體的稅收),應以財產具有收益能力為限,否則對私有財產會產生“絞殺效果”[5]。也就是說,財產稅的課征最終是以收益為對象的[6]。如果財產本身沒有收益能力,國家又對其征稅,財產本身最終會歸于消滅。
(二)對財產整體的租稅負擔,應遵從“半數原則”:收入減除成本、費用后的收益,按照類型觀察法(注:類型觀察法的基本含義是:依據一般的生活經驗,對于擬制或推定的、典型的事實關系課稅。如:當事人之間進行了房地產交易,但納稅時拒絕或提交不了交易材料,這時就按照評估價格課稅。目的是減輕稽查部門的核查負擔,簡化課稅手續。參見陳清秀.稅法上類型觀察法[J].植根雜志,2007,(11):6.),租稅的總體負擔不應超過半數。“半數原則”的規范依據是《德國基本法》第14條第2項:財產權之行使,應“同時”有利于公共福祉。也就是說,財產的私用是優先的,負擔租稅是財產權的附帶社會義務,不能喧賓奪主,超過所有人所得的一半。
(三)特別保護個人和家庭所需財產[7]。從《德國基本法》第14條可以演繹出財產權的生存權保障功能,而且,婚姻家庭受到《德國基本法》第6條的特殊保障。因此,常規或一般水準的家用財產,應免征財產稅,在繼承稅中也應規定充分的免稅額[8]。
(四)為社會政策目的財產稅之租稅優惠,因與公共福祉相關,在規定了明確構成要件的前提下,是正當的[9]。
(五)如果繼承標的是企業,繼承稅的課征,不得損害企業的持續經營。因企業作為就業場所,負有增進公共福祉的義務[10]。
觀察德國法上的情形,我們可以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征收規范對征稅收具有“弱拘束力”。也就是說,在一般情形下,《德國基本法》中的征收規范并不當然拘束征稅,但如果課征過度,則違反財產權規范。此外,依財產的不同種類,對稅收的要求也略有差別。
二
《美國憲法》文本中的征收規范包含在《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之中。《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給予公平補償,私有財產不得為公用目的被征收。”《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將該規范適用于各州。這兩個修正案所涉及的對征收的限制能否適用于對征稅的限制呢?
一般認為,美國法對征稅權的唯一限制就是對政府權力的一般性限制。一項稅收制度如規定對白人和黑人,對女人和男人征收不同的稅,將被攻擊為違反平等條款。但如果征收同樣的稅,哪怕是很高的稅,就不易受到攻擊。針對報紙的特殊稅種將被攻擊為限制表達自由,而不是違反征收條款。一個稅率達100%的沒收性稅種可能被攻擊為恣意而無效,但攻擊是在實體性正當程序條款下進行的,與國家征收權(eminent domain)無關。“征稅權放在憲法的一個房間,而征收權在放在憲法的另一個房間。”“對一個權力的限制不適用于對另一個權力的限制。”[11]
之所以堅持征收規范不適用于征稅,是因為征收規范與補償伴隨,而不可能規定“當事人在納稅后必須得到利益補償……司法部門不可能堅持這樣的準則:每個納稅人都應該得到平等的利益,法官也不可能衡量納稅人的納稅數量和得到的利益數量之間的比例關系。”[12]但問題是:“征收和征稅是手的兩面,不是征稅和征收是否應該區分,而是如何區分。”[11]284自19世紀末期開始,直至1980年代,公眾以征收規范為依據,要求判決某類征稅違憲的訴求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聯邦最高法院時而謹慎地躑躅前行,時而有原則地后撤(注:篩選案例時,參考了Richard A. Epstein , Takings :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Power of Eminent Domain , Harvard Universitu Press ,1998.這些案例Epstein教授在該書中引用過,但沒有展開。案例的內容來自LEXIS數據庫。)。梳理這些判例,我們可以歸納出聯邦最高法院對該問題的基本態度。
(一)超過納稅人財產價值本身的專用稅是否構成征收:“諾伍德訴貝克案(Norwood v. Baker)”(注: 172 U.S. 269(1898)與該案類似的還有Martin v. District of Columbia,該案中,哥倫比亞特區向馬丁征收3倍于土地的專用稅,205 U.S. 135(1907).)
1898年,俄亥俄州漢密爾頓(Hamilton)縣諾伍德(Norwood)鎮為了延伸愛溫湖大街(Ivenhoe),征收了貝克的土地,并支付了2 000美元的補償。
當時的美國,有一種專用稅(assess)制度,即:公共不動產改造完成后,可能使毗連的財產升值,因此,毗連財產的所有人應該為此支付費用,即專用稅。最后測算出貝克應支付的2 218.58美元專用稅。
貝克認為,向其征收專用稅違反《第十四修正案》,構成沒有補償的征收。
經過一系列程序,該案最后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不否認專用稅的合法性:“沒有疑問,毗連財產的所有人應該繳納專用稅,以支付在其門前開放一條公路的費用——這種專用稅建立在已經確立的原則之上:從公共不動產提升中得到了特殊利益的人應該承受特殊負擔……立法部門可以創設一個新的稅收區域(taxing district),決定哪些地區屬于這一區域,哪些財產從計劃的公共不動產提升中獲得了利益。”[13]但立法部門在這類事務上的權力不是無限的。 “立法部門逾越了界限,在行使自己稅權時,與公民的財產權不一致。正如已經指出的,專用稅的基礎是:應納稅財產從不動產提升中獲取了特殊的利益,因此,財產所有人事實上不應支付超過其從不動產提升中所獲利益的任何東西。如果將它確立為一項憲法規則,立法部門將不動產改進的所有費用強加在某些私有財產之上,置所有人從該工程中獲得的特殊利益于不顧,還不允許他(指財產所有人——譯者注)在法院質問,公民私有財產的保障將受到嚴重侵蝕。立法部門規定毗連街道的財產從街道開放這一不動產改進工程中獲取了特殊利益,應該為此作出特殊的貢獻,并將它作為一個普遍的規則是一回事;而不問財產是否從街道開放中獲益,都需要按照其前座的寬度繳納固定的專用稅,以支付不動產改造的全部費用,這種稅確定或即將確定,且其總額超過納稅人從中獲得的利益時,不給當事人任何權利,完全是另一件不同的事情。”[13]279
具體到本案,“對私有財產所有人征稅以支付公共不動產改造的費用,數額實質性超過了納稅人從中獲得的特殊利益,超過得如此之多,是掩蓋在征稅權條款下的沒有補償的、對私有財產的公用征收。”[13]279聯邦最高法院之所以說“實質性超過”,是因為精確的等值稅收(指精確地判斷稅收和當事人從中獲得的利益)永遠做不到。
“因為超過,我們不能在征稅權和國家征收權之間做出區分。在征稅的場合,公民按照自己的比例承受公共負擔;當他的土地因公用目的而被征收,他的奉獻超過這一比例,這就是征稅權和國家征收權效力之間的差別。當超過公共不動產改造利益的費用強加在幾個土地所有人身上時,這些支付的稅收超過收益的公民,就被要求支付超過其公共費用份額的費用,這一強制性的行動不在征稅權的恰當范圍內。”[13]280
最后,法院認為:對貝克征收的專用稅實質性超出她獲取的特殊利益,構成對財產的征收,該征收為了公用目的,但沒有補償。所以是違憲的。
(二)遺產稅是否構成對公民財產的征收:“馬茍恩訴伊利諾斯信托儲蓄銀行(Magoun v.Illinois Trust and Savings Bank)”(注:170 U.S. 283(1898).這一時期,與本案類似的遺產稅案件還有Knowlton v. Moore,178 U.S. 41(1899);New York Trust Company ETAL., As Executors of Purdy, V. Eisner, 256 U.S. 345(1921)等。但這些案例與征收規范之間聯系的緊密度都不如本案。所以文章選擇本案展開。)
原告馬茍恩(Magoun)是紐約公民,且居住地在紐約。1898年,約瑟芬?托倫斯(Joseph T.Torrence)是伊利諾斯州人,有大批財產在伊利諾斯州。約瑟芬?托倫斯(Joseph T.Torrence)死后,委托伊利諾斯信托儲蓄銀行處理遺產,馬茍恩是繼承人。伊利諾斯州的庫克(Cook)縣征收5 000美元的遺產稅。該筆遺產總共價值600 000美元,庫克(Cook)縣要求信托公司直接從遺產中支付遺產稅。原告不同意,要求伊利諾斯信托儲蓄銀行不予支付。經過一系列程序,伊利諾斯信托儲蓄銀行要求聯邦最高法院審查遺產稅的合憲性。
伊利諾斯信托儲蓄銀行認為遺產稅法是違憲的。理由是:遺產稅針對遺產征收,是直接稅(注:在案件發生時,征收直接稅的是違憲的。依據是《美國憲法》第1條第9款第4自然段:“除依本憲法上文規定的人口普查或統計的比例,不得征收人頭稅和其它直接稅。”該款后被《第十六修正案修》正(1913年2月3日批準):“國會有權對任何來源的收入規定和征收直接稅,無須在各州按比例分配,也無須考慮任何人口普查或人口統計。”當今,學界對國會征收直接稅正當性仍有爭議。參見王曉剛,等.美國稅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146.),構成對公民財產的征收。
麥肯納(Mckenna)法官代表法院發表了判決意見。麥肯納(Mckenna)法官首先長篇敘述了遺贈和繼承稅的歷史,表明該稅不是新近出現的稅種。“遺贈和繼承稅并非新出現在我們的法律中。自出現在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以來,已逾60年,在其它州也一直執行。……這些稅種的合憲性一直被肯定……”[14]。談到這里,麥肯納(Mckenna)法官筆鋒一轉,“沒有必要評論這些案件,也沒有必要長篇大論支持這些判決的推理。它們建立在兩個原則之上:第一,繼承稅并不針對財產,而是針對財產的繼承;第二,通過接受遺贈或繼承獲得財產是法律的創造而不是自然權利(nature rights),是實證法上的權利(privilege),因此,授予這種權利的權力可以為該權利設置條件。從這些原則中可以推導出,州可以對這些權利征稅,在親屬之間作出區分,并在親屬和陌生人之間作出區分,規定不同的稅率,還可以允許一定的扣除;憲法中的有關征稅的統一性和平等性要求并不排除這種權力的行使。”[14]288
麥肯納(Mckenna)法官還引用了“布朗(Brown)”法官在美國訴珀金斯案(United States v. Perkins)中的判決 ,該案涉及到紐約州繼承法的合憲性,布朗(Brown)法官寫道:
“所有文明國家都承認,每個公民都享有對自己收入的絕對權利,他們可以享受自己的財產以及財產帶來的收益。在其一生中,除了這些,國家也可以要求其為公共負擔奉獻自己應該的那一份,通過立遺囑處分自己財產的權利歷來就被視為是法律的創造物,受到立法的規制。”[14]625
法院最后判決:遺產稅法是合憲的,不構成對公民財產的征收。
(三)為補貼農民向加工商征稅是否構成征收:“美國訴布特勒案(United States v. Butler Et Al., Receivers of Hoosac Mills Corp.)”[15]
1933年,美國卷入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農產品價格極度下滑,農產品庫存增加,農民的購買力下降。為此,美國國會于1933年5月通過了《農業調整法》。該法的內容之一是:與農場主簽定合同,控制主要農產品的播種面積,減少進入市場的農產品,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同時,對減少播種面積的農場主付以直接補貼。用于補貼的金錢來自對農產品加工商在購買原料時收取的“加工稅”(processing and floor-stock taxes)。加工稅率的高低以農產品市場價格和公平價格之間的差距來決定。主要農產品包括小麥、棉花、玉米、豬、大米、煙草、牛奶以及乳制品。該稅一直征收到農民的購買力恢復到1907年8月——1914年7月時的購買力為止。
1933年7月14日,農業部長在取得總統同意后,征收“棉花加工稅”,補貼給主動減產的棉農。布特勒是棉花加工商,認為該稅違憲。理由是:根據“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國會征稅只能用于“償付國債、提供合眾國共同防務和公共福利”,在本案中只能套用“提供公共福利”,按照一般的理解,是為了支持政府運作的征收:政府不能對一部分人征收金錢,卻花給另一部分人。如果對一部分人征收金錢,卻花給另一部分人,就構成沒有補償的征收,違反《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15]6。美國沒有從正面回應布特勒,而是認為,“稅進入國庫后可以用于任何用途,被告(指布特勒——譯者注)不再與之有利害關系。納稅人不能因自己認為花費不合法、降低了公共資金的使用效率,加重納稅人的負擔而追問國庫資金的用途。因為這種稅對具體納稅人的影響非常小,是否一定會加重納稅人負擔不可知。”[15]12
羅伯茨(Roberts)法官代表聯邦最高法院發表了判決意見。
本案的關鍵顯然是:加工稅的開征是否符合“提供公共福利”的要求,如果不符合,是否構成《第五修正案》中的征收。但羅伯次(Roberts)法官卻繞開這一棘手的問題,“法院不能也沒有必要確定公共福利的范圍,也無須確定為調整農業的征稅是否在公共福利范圍內”,而是從國會的權力討論開始。
國會有無權力將征收的款用于補貼減產的農民?這涉及到對《美國憲法》第1條第9款第7自然段的理解,國會“除根據法律規定的撥款外,不得從國庫提取款項……”。該條款是賦予國會的一項獨立權力,還是一項附屬性條款(即為保證國會行使其它權力的手段)呢?麥迪遜認為是行使其他權力的副產品,因為行使其它權力必須花錢;漢密爾頓認為是一項獨立的權力,只受到“提供公共福利”的限制;斯托雷法官(Story)在以往的判例中曾支持過漢密爾頓的觀點。要理解這一法條,還必須它和第一條第八款第一自然段聯系起來:國會有權征稅“以“償付國債、提供合眾國共同防務和公共福利”,“提供公共福利”是不是國會的權力?羅伯次(Roberts)法官談到:《憲法》第1條第8款規定國會有權“規定和征收稅……,用以償付國債、提供美國共同防務和公共福利”,其中,提供公共福利并不是一項單獨的條款,也不是一般性賦予議會提供公共福利的權力,而是用來定義和限制“規定和征收稅收”的權力[15]59。既然提供公共福利不是國會的一項權力,國會僅將征收加工稅作為調整農業的手段,調整農業是否在國會的權限范圍內呢?羅伯次(Roberts)法官談到:“我們的政府有雙重形態:在所有的州,都有兩個政府——州和美國;除了人民通過憲法授予美國的權力外,州有全部的政府權力,除非憲法否定或人民保留……如果我們承認公共福利條款支持稅收這一新穎的觀點,則那一條款不僅支持議會替代各州進行農業和其它工業的管制,還可將憲法中的其他條款作為手段,則勤勉設計出來的、為定義和限制合眾國權力、保留各州權力的機制將被破壞殆盡,各州的獨立性就此消滅,合眾國掠奪各州管理地方事務的權力,行使沒有限制的警察權,從而演變為全能政府。”[15]63此外,羅伯次(Roberts)法官還談到:農場主自愿減產并不能證明國會立法的合憲性,因為農民的自愿是在強制之下的“自愿”:不減產就得不到補貼[15]65。
歸納起來,法院判決要旨是:征稅是國會的權利,促進公共福利不是國會的權力。農產品的管制不是國會的權力,因為憲法沒有明確授予國會,應該屬于各州。不能通過征稅達到違憲的目的。國會沒有權力征稅以實現本屬于各州權限范圍內的事項。通過行使征稅權破壞分權原則,屬于權力的濫用。農民的自愿不是真實的,他們如果不遵守管制令,就得不到利益。
法院的判決到此,似乎可以收尾了,布特勒應該勝訴。但羅伯次(Roberts)法官忽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盡管如此,該法案并不影響布特勒的權利,因此,布特勒沒有訴訟資格。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邏輯再次上演了(注: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馬歇爾法官長篇大論地評價了賣迪遜行為的非法性,但最后卻認為:盡管馬伯里的權利受到侵害并應得到法律救濟,但是,聯邦最高法院對這一屬于政治性的問題沒有管轄權。因此判決馬伯里敗訴。Marbury v.Madison,5 U.S. 137 (1803))。
(四)開采稅的納稅人是否應該得到與納稅數額相應的服務:“卡蒙威爾斯?愛迪生公司訴蒙大拿州案(Commonwealth Edison Co. Et Al v. Montana Et Al.)”[16]
卡蒙威爾斯?愛迪生公司位于蒙大拿州,是一家一開采和出售煤炭為主業的公司。該公司開采的煤炭90%銷往其它州。
從1921年開始,蒙大拿州對該州境內開采的煤炭征收開采稅,根據煤炭價值、含熱量和開采方法,確定不同的稅率,最高可以按照合同售價的30%征收。1978年,卡蒙威爾斯?愛迪生公司和該公司的州外客戶認為該稅違憲,要求蒙大拿州返還他們已經繳納的開采稅540萬美元。1981年,該案最后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卡蒙威爾斯?愛迪生公司認為開采稅違憲的理由之一是(注: 文中的陳述只是卡蒙威爾斯?愛迪生公司等所持理由之一。認為開采稅違憲的其它理由是:第一,違反美國憲法中的商業條款:開采稅按照合同銷售價征收,蒙大拿州煤炭開采公司的銷售合同多是與其它州的用戶簽定的,所以,卡蒙威爾斯?愛迪生公司等認為,該稅構成對州際商業的管制。根據《美國憲法》第1條第8款,州際商業管制的權力屬于國會;第二,違反美國憲法中的“最高條款”,即《美國憲法》第6條第2自然段,美國憲法和聯邦法律是全國最高的法律,州憲法和法律不得與之抵觸。本案中,蒙大拿州開采稅的征收對象包括屬于聯邦,但位于該州范圍內的煤礦。蒙大拿州征收開采稅后,聯邦政府從中收取的使用金就會受到影響;第三,開采稅違反平等條款,構成對其它州用戶的歧視,因為開采稅最終的承擔者是州外的用戶;第四,開采稅違反美國的能源政策,當然最后一點不屬于違憲范疇。因本文的主題是討論征收規范的效力,所以不將上述4個理由展開。):開采稅的稅率太高,與蒙大拿州為煤炭開采業提供的服務不相稱。“州要為地方事務支出費用——修造學校、道路、維持警察和防火機構的運轉、維護公共健康、保護環境等諸如此類,折算出來,攤到煤炭行業的費用最多每噸2美分,而按照現行的稅率,相當于每噸煤炭支付了2美圓……從煤炭行業征收的開采稅中,50%存入信托基金,為后代人所享有,等于這50%用在了與煤炭行業完全無關的領域。”[16]621(注:將這筆錢存入信托基金的原因是:礦藏是當今美國人和美國人的后代共有的財產,現在對礦藏的開采剝奪了后代的財產權利,參見453 U.S. 621, (1981).)在這些推論的基礎上,卡蒙威爾斯?愛迪生公司認為開采稅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構成對財產的征收,所有人沒有得到補償。歸結起來,爭訴雙方爭議的焦點之一是:“征收不合理或者超出其份額的稅收”是否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
馬歇爾法官代表聯邦最高法院發表了判決意見。針對“征收不合理或者超出其份額的稅收”是否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這一問題,馬歇爾法官談到:
“正當程序條款并不要求從某一行業征收的稅款必須與政府對該行業提供的服務存在合理關聯。相反,一直以來的情形是:某些人或某些階層納稅,卻無法從稅金的花費中享受到直接利益,且他們無法得到救濟,這一點,我們再熟悉不過了。……稅不是專為利益服務的。正如我們曾經說過的,它是分派政府負擔的方法。納稅人從中得到的惟一利益是:在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中享受權利,這個有組織的社會之建立和保衛,都需要為了公共目的的納稅…… 憲法從未禁止蒙大拿州將開采稅的一定比例為后代人享有。”[16]623
聯邦最高法院最后判決:開采稅以及開采稅的稅率并不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不構成對財產的征收。
進入1980年代以來,美國國內稅改方案頻出。稅的正當性爭議多被稅的合理性爭議取代,辯論的舞臺也從法院移到了國會,針對的目標也從各州和各自治團體的稅種轉向聯邦稅種,征稅行為在何種情形下違反憲法文本中的征收規范,在法院的判例中逐漸淡隱。
綜觀上述判例,我們可以初步得出的結論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面對有關征稅案例時,并不絕對排斥征收條款的適用,征收條款對稅收具有“弱拘束力”。當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征收條款的適用是謹慎的: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選擇。第一個案例中,無法援引正當程序條款,也無法援引分權條款,征收條款的援引就成為的最后的殺手锏。而在第二個案例和第三個案例中,法院要么繞開征收問題,直接回到分權條款,要么將視線轉移:征稅的對象是財產的轉移而不是財產,從而回避征收條款的適用(注:該判決曾遭到愛潑斯坦教授的猛烈抨擊。愛潑斯坦教授認為:對繼承征稅和對財產征稅沒有本質的差別。因為本案中的繼承是根據遺囑繼承的,遺囑是所有人處分自己財產權的方式。愛潑斯坦教授進一步認為,繼承也應該視為自然權利,而不是法定權利。該權利的目的就是限制政府的征收權。當然,愛潑斯坦教授對美國稅制似乎存在強烈的“憤青”情節:他認為只有“平頭”(flat tax)才是正當的。參見Richard A. Epstein , Takings :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Power of Eminent Domain , Harvard Universitu Press ,1998, p.288.)。的確,法院要將征收條款適用于稅收,技術難度太大:法院不能代替國會認定稅收是否必須(比如是否為了提供公共福利),那會將法院置于政策判斷的汪洋中;盡管公民納稅之后也得到補償(購買公共產品,我們通常說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法院不可能判斷公民納稅數量和得到利益之間的比例關系。法院之所以在第一個案例中援引了征收條款,是因為專用稅的納稅人和受益人范圍都較為狹窄,納稅數量和得到利益之間的比例關系容易判斷(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的州法院將專用稅理解為土地征收,拒絕僵硬地劃分財產征收和收稅。People ex rel. Post v. Mayor of Brooklyn , 6 Bar. 209 , N.Y.Sup.Ct.(1849).)。這也從一個側面提醒我們:之所以在多數場合不將征收條款適用于征稅,不因為征收和征稅之間有本質上的差別,而是確定補償和征收之間關系在技術上有較大難度。
但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征收條款對征稅具有“弱拘束力”。在極端的情形中,“稅法可能被法院否決,如果它如此武斷,以至于人們被迫得出一個結論:那不是征稅權的行使,從實質和效果看,構成別的為憲法禁止的權力之直接行使,比如說,對財產的沒收。”[16]636聯邦最高法院一直在審理征稅是否違反征收規范的爭議時,這段話被反復援引。
三
德國憲法和美國憲法中的征收規范對征稅具有“弱拘束力”。也就是說,在極端情形下,稅法可能因違反憲法中的征收規范而無效,我們可以將其稱為對征稅權的實體控制。當然,對征稅的鉗制主要是通過程序控制來完成的:稅收法定主義對征稅具有“強拘束力”,即通過分權規范實現對征稅權的控制——代議士通過的法律是征稅的惟一規范依據。而《美國憲法》則主要通過“正當程序”規范來完成。實體控制和程序控制的結合,將征稅權限制在正當的軌道內。
這一制度框架是否適合于當下的中國語境?我們是否可能通過稅收法定主義和征收規范的立體框架完成對征稅的全面監控?我們無法逃避的追問是:在今天,中國的稅收法定主義尚未落到實處,討論適用我國憲法第13條來規范征稅,是否過于奢侈?此外,《憲法》第13條對稅收以外的征收控制尚且倍受爭議,討論該規范對征稅的控制,是否有些夸張?
也許,經典意義上的稅收法定主義在中國憲法文本中難覓蹤跡(注:我國《憲法》第56條規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該規范是否可以理解為稅收法定主義存在爭議。經典意義上的稅收法定主義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稅收法定主義中的“法”指代議機關通過的法律,沒有代議機關通過的法律不能征稅;征稅機關應按照代議機關制定的法律征稅。中國《憲法》第56條規定的法律是否單指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通過的法律不確定,從合憲性推定的角度出發,該規范所指的法律是廣義的,包括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因為我國存在大量的行政法規規定征稅問題;此外,該條規定了公民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沒有規定征稅機關按照法律征稅。參見覃有土,等:稅收法定主義[J].現代法學,2000,(3):44.),這正是我們從征收規范中挖掘對征稅權控制之意蘊的理由。而且,就全局而言,征稅對公民財產權的侵害遠大于其他征收:征收個別公民的財產只會對個別公民的財產導致個別損害,而征稅則針對不特定公民的總量財產。因此,如能從我國《憲法》第13條邏輯地解釋出對征稅權的合憲性控制意蘊,實在“功莫大焉”。
放眼《德國憲法》,我們能得到諸多啟示。第一,德國稅收的半數原則是從財產權的社會義務中推導而出,我國《憲法》第13條中的財產權條款有無該項意蘊?第二,《德國基本法》第14條推導出生存權的理念,因此,稅收不能有害于個人及家庭的生存,我國《憲法》第13條有無可能做這種推導?
《我國憲法》第13條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該規范用兩款的篇幅從正面肯定公民私有財產權,征收和征用僅僅是一種例外的情形,我們可以從中解釋出公民財產私有在邏輯上的優先性。我國《憲法》文本中盡管沒有規定生存權規范,但如果按照德國法的推演模式,我國《憲法》文本第13條對財產權的生存保障功能可以被演繹得更加充分。財產的功能大體上可分為兩個層面:營業和生存保障。我國《憲法》文本對財產權的營業功能是在第11條規定的,“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既然《憲法》第11條已經規定了財產權的營業功能,憲法第13條的重心就應是財產的生存權保障功能。如果將財產權對家庭的保障功能納入考察視野,我國《憲法》文本更不缺少規范資源——我國《憲法》第49條規定:“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于是,我們也可以邏輯地推演:關于構成“絞殺”效果的征稅違反我國《憲法》文本中的征收規范,對私有財產的征稅也應遵守“不超過半數”規則,對維持家庭或個人生存必須的財產征稅時,必須謹慎。
美國法上的情形對中國也有著不可忽略的意義。如果將納稅理解為購買公共產品的支出,在大多數情形中,購買的公共產品是否與公民的納稅額等價無法判斷。但如果出現在一個相對具體的語境中,公民納稅數量與得到的公共服務之間的比例關系容易判斷,如果征稅權的行使極其武斷,公民的納稅數量與得到的公共服務明顯不成比例,則征稅行為應被視為違反《憲法》文本中的征收規范(注:我們可以討論一個虛擬的案例。目前學界在討論將社會保險費改為社會保障稅,假設該制度已經實施。如果法律規定我們只有在80歲以后支取養老金。該法律就違反《憲法》文本中的征收規范:因為80歲以后可能領取的養老金數額極其有限,與公民繳納的社會保障稅數額明顯不成比例。將社會保險費改為社會保障稅的討論可參見林凱鴻.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費改稅芻論[D].中國優秀博碩士論文數據庫,http://dlib.cnki.net/kns50/detail.aspx?filename=2005075288.nh&dbname;=CMFD2005,2009年2月18日搜索。)。
參考文獻:
[1] 賀衛方.法邊馀墨[M].法律出版社,2003:9.
[2]葛克昌.所得稅與憲法[M].翰廬出版社,1999:30.
[3] BverfGE 4 , 7(17).
[4] BverfGE 30, 250(272); 38, 60(102); 63, 312(327); 67, 70(88); 70, 219.
[5] BverfGE 93, 149, 152 ff.
[6] BverfGE 93, 121.
[7] BverfGE 93, 121, Leitsatz 3.
[8] BverfGE 93, 165, 175.
[9] BverfGE 93, 121, 148.
[10] BverfGE 93, 165, 175.
[11] Richard A. Epstein , Takings :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Power of Eminent Domai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83
[12 Barron Dienes , Constitutional Law , West Publishing Co. 2005.P142
[13] 172 U.S. 278(1898)
[14] 163 U.S. 625, 627(1890).
[15] 297 U.S. 1(1936)
[16] 453 U.S. 609(1981).
Is Taxation Subject to the Takings Clause in the Constitution: A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LIU Lian-tai (Law School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taxation is not subject to the takings clause in the Constitution. Under German law and the American law, the Taking clause in the Constitution has merely “weak binding force” to taxation and only in extreme cases taxation may be held illegitimate because of violation of the takings clause. The binding force of the takings Clause to taxation in the German basic law mainly takes the form of “half principle,” while the takings clause in the US Constitution provides that “extremely arbitrary taxation amounts to takings without compensation.” The takings clauses in the German basic law and the US Constitution are of great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kings clause i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Key Words:takings; taxation; binding force
本文責任編輯:汪太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