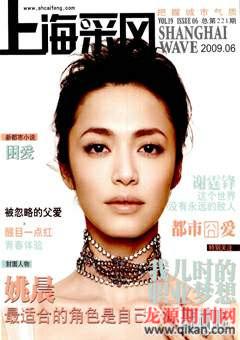南京南京,沉默離開
今何在
以前沒對《南京南京》抱很大期望,覺得這會是一個不會受太大關注的片子,默默上映,又默默離開,像很多國產電影一樣。覺得有必要去看一下是在看到了預告片花之后,發現它有國產電影中少有的真實感,以及像紀錄片一樣的質感,于是我理解了陸川想做的事。沒去細聽他的訪談,我想還是自己看見的會比聽他對媒體說出來的更真實。是否真實,是我評價這部電影的最重要標準,甚至是唯一標準。
看完電影,電影院的人都沉默著離開。沒有人議論情節,沒有人笑,有些人還一直坐在那。一部電影能在今天做到這樣已經很不容易。回到家中,去看網上關于這部電影的評論,卻看到了很多負面的評論,大多是從技術的角度出發,比如認為藝術性上不如《鬼子來了》,劇本不好;比如拿血腥和裸體當賣點,嚇到了小孩。這些評論之下,也往往都有憤怒的反擊。維護此片者卻沒有什么大道理或理論,只是覺得被震動了。就像我這樣。
這樣一部電影,應該算是歷史片;而歷史片最重要的東西,我想是真實。只要真實就好,其它的什么主題、技巧、劇情、表演……全都該讓觀眾忘記。雖然影片的真實感就是靠這些營造的,但如果觀眾看完后爭論的是這些,這部電影已經失敗了。“看清歷史”是許多主旋律影片中都會提的一句話,可真正做到的太少了。我記得小學或中學時學校組織去看了一部電影叫《屠城血證》,看完之后班上人人會喊的一句話不是“勿忘國恥”,而是“花姑娘的”。直到今天我回憶這部電影,其他鏡頭或情節都記不清了,倒是最先想起那個把女子衣服一扯到胸的鏡頭,而這樣的鏡頭出現了好幾次,我國的電影審查而不分級制度真是偉大,讓孩子們能看到許多外國孩子們看不到的東西,做為交換,他們也看不到一些外國孩子們能看到的東西。
我絕對有人性,也十分愛國,我有時候精英有時候憤青,大多時候我就是普通一個人,和廣大群眾好惡相同,但我就是沒法被《屠城血證》這樣的電影打動。我知道南京大屠殺,知道圓明園,知道甲午戰爭。我深以為恥,我曾不理解為什么成百上千人面對幾個日本兵卻不敢反抗,我也曾幻想過有朝一日占領東京揚眉吐氣。但多年后,我會想另外一些問題:假如當時自己是南京的平民,你會迎著刺刀沖上去嗎?或者也成為被驅趕的人群中的一個?假如我是一個沖進東京城的士兵,沒有了紀律,甚至下了屠殺的命令,我會去做那些日本兵所做過的一樣的事嗎?人性也許經不住拷問,這些已經完全超出了一部電影評論的范疇。但我看完《南京南京》后想的就是這些,至少這說明,它比《屠城血證》這樣的電影要成功得多。
大部分人看過這部電影后會沉默,沉默地離開。他們不會喊“中國不會亡”的口號,也不會笑著說這真是一部爛片啊,他們只是沉默。
現在的電影,能讓人沉默離開已經不容易。
但這不代表陸川或這部電影已經多偉大了。因為這種震撼更多是來自于歷史本身,誰能把這段歷史還原得更真實,誰就能震動人心,陸川只是最先想到這么做的人而已。他站在歷史的肩上,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大的貢獻。千萬別涂脂抹粉精心構思劇本研究人物。我寧愿陸川不是個拍電影的,寧愿這是部記錄片。看不見的攝像機帶著我們回到當年,去看城市的各個角落,各個瞬間的各張面孔。當時的人有多怯弱,就讓他們多怯弱,當時為了求生有多不惜一切,就讓他們多不惜一切。不要刻意營造勇敢和悲壯,也不要刻意嚎啕悲慘與血腥,任何人為的加工都是對歷史的扼殺。
陸川已經做得很努力,當然,這肯定離真實還很遠。
也許有些真實,是觀眾和導演都不愿去面對的。也許有些真實,早就隨死者永被遺忘。
遺忘是種好東西,雖然面對生死離別,雖然曾哀慟哭泣,但人總是要笑,總是寧愿把痛苦深藏心底,不愿一遍遍挖出來重新面對。現在拍南京的片子太多了,我不擔心人們忘記歷史,我倒擔心看了太多的苦難悲情,人會麻木。總有人會對著強奸場面想入非非,總有人會看到莫忘國恥時就選擇換臺,這就是人性,是普通人的人性。我們就這樣,我們不崇高,甚至不善良,神性和獸性就在一念之間,一個被屠殺者,換一個場景,給他一把槍,給他一次放縱欲望的機會,也許就會變成一個屠殺者。
《南京南京》的意義,就在它告訴了我們其實我們早就知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