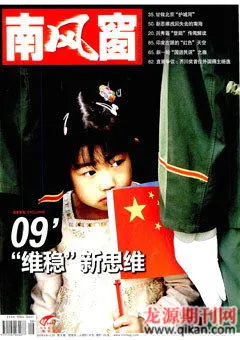國家決策的適度人數
賈西津
沒有一定人數不能體現民主性,但并非人數越多越民主,超過適宜規模反而會削弱代表團科學的民主決策性能,給有效決策增加困難。所以,各國中幾乎看不到一個成千上萬人的決策實體。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被視為中國特色民主的重要內容。《人民日報》理論版2月2日以專題總結道:“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最為重要的內容。”
中國的憲法中,人民代表大會可謂是人民的性命相托。它有權決定我們生存的規則,包括修改憲法自身;決定我們的政府、包括軍事的組成;決定政府怎么花錢,我們交多少稅,經濟和社會什么發展目標,怎么建制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特區,要不要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會的實際作用有待加強。兩個小時決定國家預算,代表在沒有看懂預算報本時就舉手表決的局面,也說明民主決策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一個決策科學問題。
正如社會學做問卷調查,什么調查規模,需要抽取多少樣本,有統計學規律。不合適的抽樣,任何調查結果都只是沒有意義的。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民主決策的方式,也有其決策科學的規則。代表產生的程序,代表大會的人數,是否符合民主決策的科學,是其決策代表性和有效性的前提。
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2987名,另外具有參政議政職能的全國政協委員還有2235名。以筆者看來,這樣的規模遠遠超出有效民主決策的范圍。如果全國人大代表人數減至目前的1/4以下,可能會有更好的效果。
有效民主決策需要適當的決策人數
縱觀不同民主制度下,民主決策機構中的人數有一定的共性規律。例如,在國家層次,實行總統制的美國參議院100人,眾議院435人,共535人;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上院)168人,國家杜馬(下院)450人,共618人;半總統制的法國參議院343人,國民議會577人,共920人;波蘭上院100人,下院460,共560人;實行議會制的印度上院250人,下院最多552人(目前545人),共不超過802人;加拿大參議院105人,眾議院308人,共413人;澳大利亞目前參議院76人,眾議院150人,共226人;德國聯邦議會612人;英國略有不同,平民院是人民的代表機構,有646人,具有榮譽性質的貴族院(上議院)定位于第二議院,作為平民院的補充和支持,包括終身貴族、法官、主教和92個選留世襲貴族在內的743人之多,超過了平民院。
在省和地方層次,加拿大各省和地區的議會人數從18人到125人;澳大利亞的省和地區議會人數在17人到93人;英國北愛爾蘭議會108人、蘇格蘭議會129人、威爾士議會60人;美國類似,州議會一般在幾十到上百,城市和地方議會很多不到10個人。歐盟議會作為國家間的民主代議機構,代表人數也并未因所代表人數之多而顯著增長,其議員共785人,其中名額最少的馬耳他只有5名,最多的德國有99名。大體看,具有一定人口規模的國家中人民代表的人數規律,在國家(乃至國家之上)層次以百計,州或省層次以十計,城市或鎮約在10人上下;國家立法機構的代表人數,在500人上下比較普通。
各國的人口數相差甚遠,國情千差萬別,民主模式也多種多樣,為什么民主代議機構中人民代表的數量卻大體相仿呢?這涉及決策科學和民主的技術問題。一方面,民主授權的事項越重要,越需要一定的代表人數,來保證決策的民主性,比如再小的國家,國家議會也不可能只有幾個人。丹麥人口543萬,是美國的1/60,印度的1/240,但其議會仍有179名代表。
另一方面,決策人數的增多無疑會給有效決策增加困難,所以幾乎不會看到一個成千上萬人的決策實體。美國從最初13個殖民地的代表到1929年眾議員增長到435名后,就決定不再隨人口增加擴大議員總數,其原因即發現規模再擴大將給有效決策帶來困境。因而,代表人數和民主決策具有重要相關,沒有一定人數不能體現民主性,但并非人數越多越民主,超過適宜規模的人數增加反而削弱代表團科學的民主決策性能。對于一個國家層次的人民代表群體,50人肯定比5人好,500人可能比50人好,但5000人肯定不如500人。
減少委托-代理偏差
目前,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模式是:在鄉、鎮、民族鄉,以及市轄區、不設區的市、縣、自治縣兩級政府層次,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設區的市、自治州,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同時,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作為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可以看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經過了三級或者四級選舉間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則經過了四級或者五級間接選舉。
經濟學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委托—代理”理論,揭示了作為管理者的代理人會偏離作為所有者的委托人之現象,經濟學家們發展大量模型試圖優化企業管理中的代理人機制。但無論怎樣優化,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差異永遠是存在的,它也是社會很多領域都能看到的現象。
現代議民主,選民與代表之間也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選民是國家權力的真正所有者,而事實上的管理權是由代表行使的,代表在多大程度上能“代理”權力所有者的意志呢?代議民主中的“委托-代理”關系一定不可避免,因此,對選民之選舉權的嚴格保障,對代表代理期間的公開機制、輿論機制、選民參與機制、倡導組織壓力機制、罷免機制,以及保留部分直接民主的機制等等,都是為了彌補代理人可能存在的問題。代議民主的一系列制度要求相當經濟學對企業管理人的優化機制,應不斷朝向減少委托—代理偏差的方向發展。
每一次選舉都意味著一次委托—代理關系的產生,可稱為“代表性折損”;二次的委托-代理就可能對所有者意志造成顯著偏離;而多次疊加的委托—代理關系,幾乎使最終代理人的行為與所有者意志之間失去關聯。可知多次間接選舉對民主的損傷是極大的。
1979年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設計了間接選舉的選舉模式,或許考慮到在地域廣大的中國直接選舉的技術性問題,當時對委托-代理問題的認識也沒有現在這樣清晰。
串聯選舉是當前的選舉模式,下一級選上一級,一級級選上去,是接力棒的模式,越向上的間接鏈條越長,代表性折損指數增長,人民授權的合法性越弱。而并聯選舉指將不同層級的代表名額均直接劃分到投票選區,各級代表獲得民主授權的合法性都直接來源于選民,只是不同層級代表的選民數比例不同而已。
從串聯選舉到并聯選舉,看似同樣產生一個人民代表大會,民主的效力卻會截然不同。串聯選舉的選民授權是間接的,每一環依賴下一環,代表性環環減損,合法性層層降低;并聯選舉則每一級獲得的選民授權都是直接的,某一方面的問題不至影響其他地方的“電壓”,授權有力,合法性強,有助于代表得到人民信任,民主對政權、穩定、秩序的好處才能體現出來。
具體說,目前最高直選層次在縣區(縣級市)級,2006年底中國全國行政區劃單位省級34個,地市級334個縣區(縣級市)級2860個,假如全國人大代表縮減到目前1/4,約750人,那么平均一個地市劃分為兩三個選區,或者三四個縣區劃為一個選區,就可以做到每個選區由選民直選一名全國人大代表。
此外,縮減人數規模也有利于代表專職化和工作方式的專業化,有利于探索更充分的選舉競爭機制。
停留在意識形態層次,爭論是要“西方式民主”還是要“中國式民主”,其實是一個假問題,比如美國就不是“多黨制”,英國就不是“三權分立”,每個國家的民主都是在自身國情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任何一種民主模式也不是一個動作可以完成,民主需要程序、科學、實踐。我們用口號對待民主,很簡單,但“民主”卻不會產生它應有的養分來反饋我們。所以,在爭論中國的民主還是西方的民主更具優越性之前,先讓我們認真對待自己的權力,把中國的民主做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