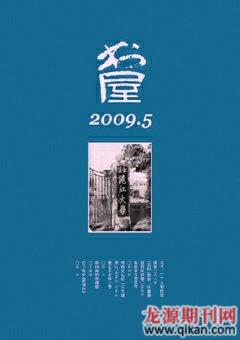文學(xué)是什么?
姜 弘
由謝韜先生題寫書名、裝幀精美的胡發(fā)云小說集《隱匿者》,到我手上已經(jīng)一個多月了,我還沒有讀,老伴張焱先讀了。她也是個老編輯,不搞理論,作品讀得比我還多,常常向我推薦好作品,介紹有關(guān)創(chuàng)作狀況。這次又是她說胡發(fā)云的作品是“另類”,許多年沒有讀到這樣的作品了:似曾相識又覺得新鮮,讓人動情更讓人思索,讀后心里不舒服卻還想再讀;會有人讀不懂或不喜歡這樣的作品。
于是,我放下正在寫的東西,先讀《隱匿者》。我的視力微弱,有幾篇是老伴讀給我聽的。讀著聽著,我就想到了這個似乎有點大而無當?shù)念}目。既然想到這里,就從這里說起罷。
一
讀小說,讀得我老淚橫流,久久不能釋懷,這確實是很久以來不曾有過的。正是從這里,讓我想到了“五四”和文學(xué)革命。文學(xué)革命發(fā)生在1918年,距今已過九十年。這中間,剛好三個三十年,分別以1918、1948、1978年開始,構(gòu)成了一個文學(xué)上的“否定之否定”三段式。第一個三十年,一般通稱“現(xiàn)代文學(xué)”,從一開始,先驅(qū)者們就不曾否定中國古代“言志”、“緣情”的美學(xué)主張,而是把它融入了從西方引進的新思潮之中,形成了具有主觀抒情性和理性批判精神相結(jié)合的新文學(xué)的啟蒙主義新傳統(tǒng)。我就是在這種文學(xué)居于主導(dǎo)地位時開始文學(xué)啟蒙的。巴金說過,他進行創(chuàng)作的時候,是和書中人物一同歌哭,一同歡笑,在內(nèi)心里重新經(jīng)歷那種生活的。我讀作品的時候,也同樣是和書中的人物一同歌哭,一同歡笑,受到感染而有所思有所悟的。所以,是否有情,能否從感情上打動我,在我的心靈深處產(chǎn)生震顫,是我衡量、評價文學(xué)作品的重要標準。后來,這種看法受到批判,在理論上受過教條主義的影響,但在閱讀欣賞習(xí)慣上,卻從未改變過這種以“情”為中心的價值取向。
第二個三十年即通常所說的“當代文學(xué)”階段,我之所以提前一年,從1948年算起,是因為那一年開始批判胡風的文藝理論和路翎的創(chuàng)作。胡風重視作家的主觀精神在創(chuàng)作中的作用,強調(diào)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感性活動”特征。路翎創(chuàng)作中那種主觀抒情色彩和理性批判精神,正是胡風理論和“五四”新文學(xué)啟蒙主義傳統(tǒng)最后的閃光。否定了這一切,就轉(zhuǎn)入了第二個三十年——教條主義理論橫行、公式化概念化作品泛濫的“當代文學(xué)”即“十七年”+“文革十年”階段。對于這一階段,后來陳荒煤曾有過沉痛的反思,說他們當年(指“十七年”)“做了一件極為愚蠢的事情,把人情、人性、人道主義、感情、靈魂、內(nèi)心世界等等,一律予以唾棄……到了十年浩劫時期,文藝終于成了無情的文藝,無情的文藝終于毀滅了文藝,這真是無情的噩夢!”不知道他意識到?jīng)]有,那種“無情的文藝”不僅毀滅了文藝,也造就了“無情的讀者”,使得整個社會的閱讀鑒賞能力普遍下降。不少人把薛寶釵視為擇妻的榜樣,而完全不理解林黛玉的精神氣質(zhì);說安娜是壞女人,說于連是深夜入室勾引少女的流氓等等。在那種“徹底唯物”的時代思潮的熏陶下,他們只知道“三大革命實踐”,而不知道人與人之間、人的內(nèi)心世界還有更復(fù)雜更美好的東西。在那種“無情”的文藝理論指導(dǎo)下,他們已經(jīng)習(xí)慣了那種“通過什么反映什么、說明什么問題”的閱讀習(xí)慣,人物、故事、主題、傾向都清清楚楚;敵與我,正面與反面、光明與黑暗、歌頌與暴露,全都一分為二,黑白分明,卻不知道什么是審美鑒賞。由此,我想起了波特萊爾的話:“假如藝術(shù)家使公眾愚蠢,公眾反過來也使他愚蠢。他們是兩個相關(guān)聯(lián)的項,彼此以同等的力量相互影響。”
事實不正是這樣么?積重難返,這種狀況至今也還沒有完全改變。
進入“新時期”即第三個三十年以后,文壇上新潮迭起,但總體藝術(shù)水平并不高,遠不能與第一個三十年相比。究其原因,主要是還沒有回歸到以“情”為中心的文學(xué)本土,還沒有擺脫以往那種文藝教條的束縛;我所說的是:取代了“五四”新文學(xué)啟蒙主義傳統(tǒng)、而在第二個三十年中居于主導(dǎo)地位的“反映生活”論。
到了世紀之交,文藝界真的進入了“世紀末”,急劇分化,各行其道:趨勢媚俗者回到了“幫忙”“幫閑”的老路,而且比先輩們走得更遠,更加肆無忌憚;真愛藝術(shù)而又憂深思遠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回歸到了啟蒙主義的正道。
是胡發(fā)云,讓我辨識出正在重新顯現(xiàn)的這條正道。從他的聲音語調(diào)里,開始有一種舊雨重逢之感。后來讀得多了,逐漸發(fā)現(xiàn),他的小說難以歸納主題,人物難分正反面,讀完全篇卻難以斷定是歌頌還是暴露。他那略嫌低沉、溫和而深情的語調(diào),久久回響在耳際、在心頭,讓我想起了魯迅、郁達夫、巴金、沈從文……
二
讀了《隱匿者》,我立刻想到了《如焉》,想到了兩年前的那些議論:稱贊者和批評者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品所涉及的一些歷史事件和相關(guān)思想,只有少數(shù)人注意到了它的文學(xué)要素——感情和語言。批評者認為這部小說在人物塑造和結(jié)構(gòu)布局上都不夠標準,雖有思想但缺乏文學(xué)性。如果用同一標準來衡量這本《隱匿者》,可能更不合規(guī)格:主題思想、人物形象、傾向性等等似乎都不夠鮮明突出。其實,陳荒煤所痛悔的那種“無情文藝”,倒大都符合這種“鮮明突出”的規(guī)格,這類作品堪稱“汗牛充棟”,可現(xiàn)在還有多少人還記得它們,再去讀它們呢?
相比之下,胡發(fā)云的作品確實屬于“另類”,是回歸“有情”之正道的真文學(xué)。從《老同學(xué)白漢生之死》和《駝子要當紅軍》這兩篇小說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特點。
這兩篇小說的情節(jié)和人物性格都比較復(fù)雜。白漢生原本是個老實平庸的人,初中同學(xué)聚會,竟然都忘記了班上還有過他這個人。是經(jīng)濟改革大潮改變了他的命運——被人利用又代人受過,頂罪入獄,后來又因此而受到照應(yīng),利用價格雙規(guī)制發(fā)了財,從此改變了他在眾人中的地位而受到注意和尊敬。為了回報這種尊敬,他盡其所能地滿足人們的需求,終因虧空破產(chǎn)而自殺;他寧肯以個人生命相抵,而不愿牽累別人。作者在以第一人稱并用同情和惋惜的口吻敘述這一切的同時,說到了前前后后人們對白漢生的贊揚和非議,像輕輕的嘆息,慨嘆人世的冷暖。
《駝子要當紅軍》的主人公趙耀的一生,卻是另一種景象,另一種調(diào)子。趙耀出生在邊遠的窮山村,早年喪父,孤兒寡母常常受到愚昧鄉(xiāng)民的欺凌。十四歲那年,他憤而放火燒了自己的家,投奔了紅軍。以后幾十年腥風血雨,九死一生;到老來功成名就,兒孫滿堂。在慶賀八十大壽的時候,他意識到自己以往引以為自豪的“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都已經(jīng)在兒孫們的戲謔中被“解構(gòu)”了;他心底留下的,是久遠的傷痛,一種深深的愧疚之情:深感對不起自己的母親、妻子和大女兒。當年放火造反時,不理解母親的苦況,也不顧及她的死活;結(jié)婚成家以后,他從沒有想到過妻子的獨立人格和事業(yè),后來更以專制的方式包辦了大女兒的婚姻,造成了她的不幸……
這兩個人物的命運際遇很有些相似之處:第一,他們的生命軌跡都呈馬鞍形或拋物線形、都是從卑微走向顯赫,最后歸于涅槃。第二,他們的發(fā)跡既有偶然性,更是歷史的必然:都是糊里糊涂地進入了歷史的大峽谷,一個是在經(jīng)濟大潮中發(fā)了財,變?yōu)楦缓溃灰粋€是穿過戰(zhàn)爭烽火幸存下來,成了英雄,而這又都是他們所始料未及的。第三,他們的過錯——白漢生的經(jīng)濟犯罪,趙耀的放火、吃人肉,都不能完全由他們個人負責,都有更復(fù)雜的歷史和文化的原因。最后,他們的結(jié)局,肉體的與精神上的涅槃,都讓人感到惋惜并產(chǎn)生同情。
也許,這正是促使作者寫這兩篇小說的內(nèi)在動因:他是在追憶往事,懷念故人,喟嘆人世冷暖,思索歷史真相,抒發(fā)他那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悲憫情懷。這中間,他好像特別看重這兩個人物身上保有的人性——誠實和善良。白漢生對待家人和同學(xué)的那種誠摯,對待自己歷史污點(有前科)的那種坦然,最后的以生命承擔一切,這都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同樣,老紅軍趙耀的精神上的變化,也很值得注意,依他那樣的經(jīng)歷和身份,能夠重新面對歷史,特別是能自責、有愧疚,最后沒有說要去“見馬克思”,要進高層革命公墓,而是準備魂歸故里,回到那個邊遠的窮山村,去尋找、去陪伴他那不知所終的不幸的寡母。不管他們的經(jīng)歷和身份多么不同,應(yīng)該承認,這兩個人物都是老實人、好人。是他們心里的那種真情、他們身上保有的那種人性中最可寶貴的品格——善良和誠實,打動了作者也打動了讀者。
三
我更欣賞也更看重的是《隱匿者》和《葛麻的1976—1978》,我覺得,這兩篇小說有些像“姊妹篇”,不僅所寫的題材都與“文革”有關(guān),它們總的意蘊都有明顯的啟蒙主義傾向。我讀《隱匿者》的時候,立刻想到了魯迅的《狂人日記》;讀《葛麻》的時候,也想到了《阿Q正傳》。
《狂人日記》本是一聲震撼人心的啟蒙吶喊,是清醒而沉痛的民族自省的獨白。那里面沒有“階級斗爭”,有的是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所謂“吃人”,指的是精神上的毒害,“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對國人的束縛和麻醉,致使“不把人當人”成了中國社會生活的常態(tài)。
《隱匿者》所寫的,就是一個當年的紅衛(wèi)兵對自己以往“不把人當人”的暴行的反思、自省,以及由此引起麻煩的故事。小說里的一個人物提到:“中國有句老話,叫‘知恥近乎勇,可惜我們社會中這樣的勇者越來越少了!”大概正是有鑒于此,胡發(fā)云才寫了這篇小說。能以這樣的勇者為對象寫出小說,勸誡人們知恥,已經(jīng)是難能可貴的了,更可貴的是,他揭示出了當年紅衛(wèi)兵暴虐行為的個人和社會的深層原因。
小說主人公當年是個十六歲的初三學(xué)生,他為什么要打他一向敬重的老校長呢?因為他前一天晚上突然得知,他的擔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父親被揪出來了,這就是說,他很可能就要從“紅五類”落入“黑五類”,成為“狗崽子”了。他恐懼而又憎恨,強作鎮(zhèn)定地參加了審問老校長的造反行動。他極力保持自己“紅五類”的威嚴,極力表現(xiàn)自己的“紅”與“忠”,表現(xiàn)出強烈的革命義憤,把因父親倒臺而從心底升起的憎恨轉(zhuǎn)移到眼前的斗爭對象身上,卻不料表現(xiàn)過分,失去控制,動手打了老校長,導(dǎo)致了后來的悲劇。這都是那個“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現(xiàn)”的陷阱,使得多少單純的青少年變成了“吃人”的暴徒!
胡發(fā)云的深刻之處在于,他揭示出當年的施暴者同時也是受害者,而這一切,全都基于那種野蠻的叢林法則——“你死我活”、“不斗行嗎?”如今,勇于自省者是要堅決告別那種“吃人”的歷史及其野蠻的意識形態(tài);拒絕自省的隱匿者阻撓別人自省,是唯恐失掉什么。對照一下《狂人日記》,當能悟出更多東西來。
現(xiàn)在再來看《葛麻的1976—1978》(以下簡稱《葛麻》),這是我和老伴都特別欣賞的很有些特別的作品。說它特別,首先在于行文的流暢自然:全文近四萬字,不分章節(jié)也沒有空行(這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從頭到尾一氣呵成;讀來如聽人敘舊,似無章法節(jié)奏卻娓娓動聽,引人入勝。他是用一種略帶調(diào)侃而一往情深的語調(diào)述說的。
這篇小說的第二個特別之處,是它的輕故事而重細節(jié)。看了葛麻對待女性和孩子的那些細節(jié)描寫,我想起了馬克思和胡適都說過的一種看法:從對待婦女和兒童的態(tài)度,可以判斷人的文明素質(zhì)如何。葛麻在女性面前的那種矜持、畏縮;他對孩子的那種無條件的愛,顯示出他的淳厚善良,讀時令人感動。這就是細節(jié)的力量。把小說、戲劇確定為“以寫人敘事為主”而忽略其“抒情”、“傳情”的本質(zhì)特征,從而重視編排情節(jié)、刻畫人物,卻忽視了細節(jié)和敘述語言——這是多年來的誤人謬見。從莎士比亞到托爾斯泰;從湯顯祖到曹雪芹,都不是這樣看、這樣做的。
第三個重要的特別之處,是他獨具慧眼,抓住了1976—1978這個歷史的空擋,而且看出并如實揭示了它的本質(zhì):這不是一般的孤立、停滯的時間段,而是如汽車行駛中的“空擋”——任由原來的慣性繼續(xù)滑行——那不就是“文革以后的文革”嗎?一點不錯,葛麻的造反和對葛麻的批斗、關(guān)押,都是“文革”中演練多年的鬧劇:上層的路線斗爭,中間的奪權(quán)斗爭,基層葛麻們爭取基本生存權(quán)的斗爭,同樣的旗幟口號,那內(nèi)容和指向卻大不相同,有著嚴重的誤解和錯位,各式各樣的陰差陽錯不一而足。可以說,這個“空檔”實際上是前面幾幕大戲的尾聲,濃縮了全劇的精華。
最后,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特別之處,那就是作品里貫穿著一種“文化流”——這名稱是我臨時杜撰的,指的是作品中人物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氣質(zhì)及其歷史文化淵源。小說里多次提到,葛麻們的日常生活用語中,有許多話都來自戲曲電影和樣板戲,“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xiàn)實”,可見他們的思想觀念與這種文化的關(guān)系之深。葛麻的一生,從棄兒、孤兒、流浪漢到進廠當工人,到“文革”中造反又被批斗,到二十年后那番驚人的議論,這中間確實貫穿著一條文化之線。這是以一種啟蒙的目光看出并描繪出的真實的歷史文化現(xiàn)象。葛麻很像阿Q,除了臉盤以外;他是比阿Q優(yōu)秀,但他的基本性格和命運遭遇,他的卑微、愚昧和不幸,特別是與這一切緊密相關(guān)的他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氣質(zhì),卻都是和阿Q一脈相承的。
四
從以上種種,似乎可以看出胡發(fā)云的創(chuàng)作的總的主旨——不就是魯迅所說的“人性的解放”,“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以及“創(chuàng)作總根于愛”嗎?可見,胡發(fā)云在向“五四”回歸。
以上文字被輸入電腦以后,我才注意到《隱匿者》前面的序言,讀了當然另有一些想法。不過,篇幅和時間都不允許我再啰嗦了,就摘引魯迅的話來做結(jié)尾,——我越來越感到魯迅離我們很近: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fā)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dǎo)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這是互為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于已經(jīng)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yīng)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yīng)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論睜了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