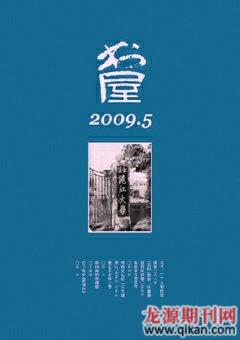從胡適、梁啟超的書目談起
巫少飛
單位給員工發了一本《學習筆記》,由我市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統一印發,大約是為了創建學習型機關而準備的。每次學習開會我都誠惶誠恐,不敢打開筆記本的原因是:《學習筆記》里面赫然印著胡適、梁啟超等人開列的書目。提到國學或漢學,我們幾位文友經常將陳寅恪、王國維、章太炎等列為一流高手。胡適因為參與事務繁多,連黃侃都笑他只留下半部《中國哲學史》;梁啟超好像知道自己早逝一樣,生前拼命著述,可是連他自己也說:“我梁某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陳寅恪)寥寥數百字有價值。”由此說明,胡適、梁啟超至少自己不敢稱國學大師,可即使這樣,胡適、梁啟超開出的書目仍讓我輩汗顏。許多書,我們不但沒仔細讀過,有的根本就沒聽說過。比如《佛遺教經》、《崔東壁遺書》等。讓我輩更抬不起頭的是:胡適、梁啟超開的書目定名為“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胡適對此還解釋:“我擬這個書目的時候,并不為國學有根底的人設想的……”筆者拿著胡適以為勉強可稱為“最低限度”的書目問身邊搞文化的朋友,大多數的人都表示沒讀過。
時下,歷史文化并沒多少人真正關心,我們打開電視機,見到的多是皇室名流、江山興亡、英雄美人、爭權奪利。“二十四史”的蕭條和歷史影劇的走俏形成相悖的走向。逛逛書店,一些書本正把秦檜稱“無間道”、把曾國藩稱“月光族”、把唐伯虎叫“房奴”……就這樣,歷史文化在電視、書市、講壇和市場的謀合下被弄得面目全非。在一個貌似歷史文化重新興盛的年代里,有一次,我讀到伍立楊的一篇短文,原文發在《文匯報》。伍立楊舉了這樣一例:一份中國臺灣省的中學國文試題,讓祖國內地一半以上的中文系博士做不來。
有一回,我市宣傳部的一位朋友問我:“現在可不可以稱‘文藝復興?”我正色告訴他“不能”,是因為李澤厚先生有一句話,“在我看來,如果‘五四那批人是‘啟蒙,那么一些人現在就是‘蒙啟。”是啊!“五四”那批文人不管是反對傳統、還是保守傳統,他們本身的學問都是深不可測。在西南聯大,最讓人看不起的沈從文,現在看來都高不可及。
行文至此,應該很清楚我想說的是:不是胡適、梁啟超開的書目太難,是我們眼下的社會銅臭太盛,文氣太薄,是我們整個國學的傳統斷檔了。需要反思的肯定還有很多,可是我們最需要反思的是:我們的讀者何以從欣賞漢文唐詩的高度墮落至欣賞電視小品、手機短信和后宮邀寵的洼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