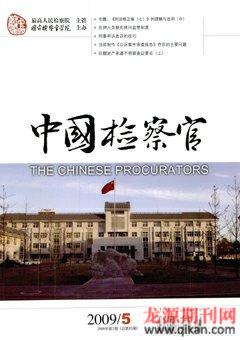《刑法修正案(七)》對懲治腐敗相關條文的完善
黃太云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中增加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并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進行了修改,對進一步完善刑法、懲治腐敗犯罪,必將起到重要作用。下文就《刑法修正案(七)》對上述兩個罪名的立法背景、條文修改完善的主要內容作簡要介紹。
一、增加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一)立法背景
為懲治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犯罪,在《刑法》第385條中規定了受賄罪,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利益的行為規定為犯罪。為懲治發生在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的斡旋受賄犯罪,《刑法》第388條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也規定為犯罪。關于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辦事,收受財物追究刑事責任的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1月13日發布的《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法〔2003〕167號)的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構成受賄罪共犯,取決于雙方有無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國家工作人員明知其近親屬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近親屬的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對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認定為受賄罪,其近親屬以受賄罪共犯論處。近親屬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構成受賄罪共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近年來,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中紀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一些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目前在處理涉及腐敗案件時遇到了一些新問題: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子女、親朋好友利用其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通過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辦事謀取不正當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事情敗露后,說財物是背著國家工作人員收的,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說根本不知道收受財物之事,使案件難以處理。此外,一些已經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雖然已不具備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但他們或者其近親屬及關系密切的人利用其在職時形成的影響力,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自己從中索取或者收受財物。這些行為嚴重玷污了國家公權利的廉潔性,敗壞了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應作為犯罪追究。另外,我國已批準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其中第18條對影響力交易犯罪也作了明確規定,要求各締約國將“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任何人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間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當好處,以作為該公職人員或者該其他人員濫用本人的實際影響力或者被認為具有的影響力,從締約國的行政部門或者公共機構獲得任何不正當好處的條件”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其中的“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任何人”就包括國家工作人員、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及其配偶、子女、親朋好友等非國家工作人員。一些部門提出,為適應反腐敗的需要,刑法的有關條文規定應當修改完善,與公約銜接,以有利于我國履行承擔的國際公約義務。
(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特征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有以下犯罪特征:
1.本罪的犯罪主體為特殊主體,即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以及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近親屬”主要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不正當利益”,是指根據法律、法規、規章或者政策規定不應得到的利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是指除近親屬之外的其他關系親近、可以間接或無形的方式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決定施加影響的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是指曾經是國家工作人員,但由于離休、退休、辭職、辭退等原因目前已離開了國家工作人員崗位的人。在草案審議修改的過程中,有的部門建議將條文中國家工作人員(以及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改為“特定關系人”。理由是,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聯合出臺的《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已經使用了“特定關系人”一詞,其中“特定關系人”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這個概念已被廣泛接受和使用;另外,條文規定的“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的概念過于寬泛,范圍也難以確定。法律委員會經研究認為:國家工作人員(以及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是與國家工作人員(以及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非國家工作人員,之所以將這兩種人利用影響力交易行為規定為犯罪,主要是考慮到他們與國家工作人員或有血緣、親屬關系,有的雖不存在親屬關系,但屬情夫、情婦,或者彼此是同學、戰友、部下、上級或者老朋友,交往甚密,有些關系甚至可密切到相互稱兄道弟的程度,這些人對國家工作人員(以及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自然也非同一般。實際中以此影響力由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辦事,自己收受財物的案件屢見不鮮。如果將影響力交易犯罪主體僅限于“特定關系人”的范圍,顯然窄了,不利于懲治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腐敗犯罪。因此,這個意見沒被采納。
有人擔心,《刑法修正案(七)》將國家工作人員(或者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關系密切的人”作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犯罪主體,是不是范圍太大?在實際執法中會否造成打擊面太大?這樣的擔心雖然可以理解,但擔心無太大必要。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18條中要求各締約國將“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任何人”規定為影響力交易犯罪的主體的要求相比,很顯然,我國規定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范圍還是相當小的。但即便如此,也并非只要滿足國家工作人員(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與其關系密切的人”的條件就構成犯罪,因為構成本罪除了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與其關系密切的人”以外,更為重要的是還必須有利用其影響力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利用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且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這里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構成本罪必須是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才構成犯罪;如果為請托人謀取的是正當利益,不構成犯罪。考慮到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犯罪主體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其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必須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才能實現,其社會危害性比國家工作人員直接利用職務進行的犯罪要小一些。因此,刑罰也比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要輕一些,最高十五年有期徒刑。
2.行為人在實施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時在具體行為上有所不同。“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是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而“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則是利用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1月13日發布的《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法〔2003〕167號)的規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是指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在職務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系,但是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如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等。
需要指出的是,《刑法修正案(七)》在新增的《刑法》第388條之一中,對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在不同量刑檔次和條件的規定方式上與現行刑法對受賄罪的規定方式有所不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雖然也屬受賄犯罪,但本條規定了“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等三個既考慮數額又考慮情節的量刑檔次,而對具體數額標準沒再做具體規定。這主要是考慮到受賄犯罪與貪污罪有所不同。貪污罪侵犯的是公共財產的所有權,貪污數額的大小,一般就可反映社會危害性大小;而受賄罪侵犯的則是國家公權力的廉潔性,受賄數額的多少并不一定能完全反映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有些受賄的數額不大,但給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的損失卻是巨大的。因此,對受賄罪的量刑,除了要考慮數額,還應當考慮其他情節。具體的數額和情節規定,要由司法機關根據實踐作出司法解釋。這樣一種規定方式,為今后完善刑法對賄賂等犯罪的量刑條件規定提供了經驗。
二、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修改
(一)立法背景
反腐敗需要預防和打擊并重,標本兼治。世界各國反腐敗經驗表明,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建立完善有效的對公職人員的監督制度,打造陽光下的政府,鏟除腐敗滋生、蔓延的溫床和環境,對于遏制腐敗犯罪的發生具有根本性作用。對公職人員的財產加強監督,是各國預防腐敗的普遍做法,《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也有明確規定。我國已經建立了黨政領導干部收入申報制度,這是建立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最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國家工作人員如實申報自己的財產,必要時對自己財產的來源作出合理說明,這是財產申報制度的基本要求。在現實生活中,有些國家工作人員聚斂大量財富,其擁有的財產遠遠高于其正常收入幾十倍、幾百倍,本人不能說明其財產的合法來源,司法機關也難以獲得其犯罪的證據,不能直接以相關犯罪認定。為了有效地同腐敗犯罪作斗爭,1997年《刑法》第395條第1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一些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在實際中查處的此類案件有的來源不明的財產數額多達上百萬、千萬、甚至幾千萬元,大多屬于利用職務和地位斂聚的非法所得或者其他非正當收入,數額特別巨大,只是其本人不能說明或者不愿說明來源,同時司法機關也無法查明,由于最高法定刑只有五年,有些案件來源不明的財產數額相差上千萬元,但刑罰只相差一年,明顯與這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不相適應,也與貪污、賄賂犯罪刑罰不平衡,從而使這些貪官逃避了法律應有的制裁。鑒于這類犯罪社會影響惡劣,建議提高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刑罰。另外,有的部門提出,本條“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規定,是指財產和支出兩項總和明顯超過合法收入還是指其中一項明顯超過合法收入不清楚,建議從文字上明確。
(二)修正情況
《刑法修正案(七)》規定,將《刑法》第395條第1款修改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該國家工作人員說明來源,不能說明其來源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額特別巨大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
修正案對原條文主要做了以下修改:
1.將法定最高刑從五年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在草案向全國征求意見和常委會審議過程中,有些意見主張將本罪的最高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死刑。基于以下考慮,常委會沒有采納這種意見:首先,本罪是在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其財產的差額部分是通過任何其他違法犯罪行為取得的情況下,將這部分財產推定為采用非法手段獲得而設立的一個罪名,從證據角度講,這樣給人定罪只能是特例;其次,我國財產申報制度尚未真正建立;此外,從實際辦案情況看,犯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人,幾乎都還涉及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其他犯罪,可以數罪并罰判處刑罰,并不會影響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貪官的打擊力度。如果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法定刑規定過重,不利于司法機關盡力深挖腐敗犯罪。
2.將“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修改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使財產、支出無論其中一項達到,還是二者相加達到差額巨大的數額標準,都可以追究刑事責任的涵義更加明確,更有利于打擊這類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