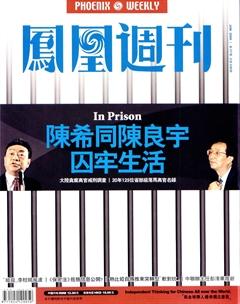病毒全球化與公眾知情權
張曉波
2008年年底,出于對“一戰史”的興趣,偶然翻閱到美國學者巴里所著《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一書。當時未曾留意書中所寫的“西班牙Lady”(西班牙大流感)的起源,居然是今天引起全球恐慌的“甲型H1N1流感”。之后,又閱讀了勞里·加勒特獲普利策獎的《逼近的瘟疫》一書,同樣是講全球化時代的瘟疫,同樣是面對無法解決的問題。兩本書同時提出了一個問題,疫情信息為何必須公開?
戰爭是瘟疫天然的盟友。1918年的春天,一戰正酣由于馬克沁機槍的發明,迫使歐洲數百萬軍隊在泥濘的戰壕中對峙,后方數以千萬的后勤人員忙碌于支援戰爭。戰爭物資,人員的高速流轉也加速了“甲型HIN1流感”的傳播。病毒首先由駐扎在美國東部的軍隊帶到歐陸的軍隊當中,再通過戰爭與運輸機器僅僅5個月之內,就傳播到全球。據最保守的估計,1918年大流感至少造成全球2000萬人死亡,僅西班牙一地,就死亡800萬人,國王阿方索三世也未能幸免。1918年大流感不同以往,青壯年成為受流感攻擊的主要人群,交戰國為了不讓敵國獲知軍隊戰斗力,都紛紛隱瞞病情,而中立國西班牙首先公布疫情,故此流感得名為“西班牙Lady”。
對于1918年大流感的恐怖無須過多渲染,在《逼近的瘟疫》一書中,作者提供了這樣一組直觀的信息:“在1918年9月1日到11月1日之間,加納的每20個公民中,就有一人死亡。西薩摩亞的民眾被病毒驚呆了,1918年11月和12月間,西薩摩亞的3.8萬居民幾乎全部感染流感,其中7500人死亡,約占人口的20%。”
持續一年的“西班牙Lady”可預知的結果是使交戰雙方作戰人員大量減員,也使一戰提前結束。此次流感,更能引人深思的是病毒傳播的全球化與速度。在此之前,全球所有的瘟疫,基本上是區域性、流動性相對較低的。“西班牙Lady”之后,疫情的全球化成為了最致命的問題,國家與國家之間隔離并不能有效防止流感的傳播,任何一次流感病毒的發作,都很快走上全球傳播路線。最近一次,與我們最密切相關的瘟疫經歷是2003年的SARS。
西班牙大流感的另一個挑戰是公眾知情權,政府當局必須開放公眾對于疫情的知情權,才可能使公眾對于瘟疫有正確的心態。西班牙大流感期間,正是因為各國對于疫情信息的不透露,導致醫院、戰地臨時病房、公共區域成為瘟疫傳播最有效的場所。公眾對于知情權的強調,同樣也是勞里·加勒特《逼近的瘟疫》一書的重點。
勞里·加勒特認為,20世紀下半葉的冷戰意識形態事實上將對瘟疫的治療也當成了意識形態。盡管前蘇聯一再宣傳,“我們已經消滅了某某傳染病”,但病毒似乎并不庇佑意識形態,無論是共產主義世界還是資本主義,在傳染病面前仍然顯得脆弱不堪,尤其是1981年發現艾滋病之后,據目前已知的統計數據,這種新型的病毒,已經使得全球2000多萬人喪生。勞里·加勒特指出,盡管大家都知道艾滋病的恐怖不下于1918年全球大流感,但卻為很多政府官僚所諱言,疾病往往與“不潔的性關系、國家意識形態乃至于政府形象”聯系在一起,最終的結果是諱疾忌醫,不到萬不得已,絕不向公眾告知真實情況。
在加勒特看來,官僚對于疫情的掩蓋,乃是有意無意地成了病毒事實上的幫兇,這一批評不僅對1918年大流感的全球傳播有效,對于發生在2003年的SARS同樣有效。加勒特也提到了中國政府某些官員在SARS初期的錯誤做法,同樣,她也肯定了中國政府在2006年之后全面公開疫情使全社會獲知這一做法。
勞里·加勒特是一位帶有悲觀主義氣質的學者和醫學工作者,她對于不斷變化感染方式的病毒,顯然認為“我們在打一場無法打贏的戰爭”。對于病毒的治理,她的基本看法是,讓公眾知情,讓公眾參與治理。經歷了2003年的SARS,我們也更明白知情權的難能可貴。
編輯 曉波 美編 黃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