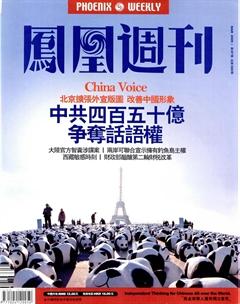臺(tái)灣“叛逃者”的大陸人生
王騫
1949年國民黨退守臺(tái)灣后,兩岸不斷相互策反,以優(yōu)渥待遇吸引對方陣營人士投奔,韋大衛(wèi)、朱京蓉、王錫爵,這些彼岸的“叛逃者”至此岸即成“起義者”。半個(gè)世紀(jì)后的今天,兩岸政治氛圍日漸和緩,但這些投奔事件的主角們,仍未得到對岸最后的“寬恕”,面對故土家園,止于隔海相望,歷史的一頁遲遲未能翻過。
平淡的當(dāng)下
聊了一下午舊事,總是笑瞇瞇的朱京蓉起身打開燈。陳設(shè)簡單的客廳里只有幾個(gè)燈泡還能亮,趴著烏龜?shù)聂~缸成了最明亮的物件,泛著幽幽的綠。這套空軍分給他的住房,位于北京的北四環(huán)外,他和妻子,兩個(gè)兒子住了十幾年,現(xiàn)在房子舊了,一個(gè)兒子剛搬出去。
到今年5月,朱京蓉來大陸整40年了。1969年5月26日,他的教官國民黨空軍上尉黃天明開著T-33A型噴氣教練機(jī)到達(dá)廣州,坐在教練機(jī)后側(cè)艙位的他,就這樣被動(dòng)投誠了共產(chǎn)黨。那年6月的《人民日報(bào)》上,報(bào)道了他們“駕機(jī)起義回歸大陸”的消息;20多歲的他們手持《毛主席語錄》,還高喊著剛學(xué)會(huì)的“毛主席萬歲”。
因長年在大陸軍隊(duì)系統(tǒng)工作,到大陸后他從未接受過媒體采訪。三年前從空軍指揮學(xué)院科研部副部長任上退休后,這個(gè)規(guī)定才算失效。如今朱京蓉每周有六天去一家臺(tái)灣人的飯店當(dāng)顧問。
“累,今年不想干了。”這樣的話從他嘴里說出來,更像謙虛而不是抱怨。唯一的休息日,他留著或陪夫人逛街,或接待來自臺(tái)灣的朋友,偶爾,也去東邊會(huì)會(huì)住在望京的韋大衛(wèi),喝杯酒。
韋大衛(wèi)比他早來大陸13年,開到大陸來的還是蔣緯國的專機(jī)“塞斯納”。已經(jīng)81歲的他,看上去比年輕時(shí)瘦小了一圈,手腳略有不便,上下樓梯要扶一把。新買的房子里平日就他和夫人住著,兒子常來探望。天氣一冷,他甚少出門,太陽好時(shí),老夫婦就帶著收養(yǎng)的流浪狗在小區(qū)里散步。
朱京蓉在北京每年能見幾次的,還有王錫爵。1986年開著華航貨機(jī)飛來大陸的王錫爵,只比韋大衛(wèi)小一年,自中國民航總局華北分局副局長任上退休后,如今住在國務(wù)院機(jī)關(guān)管理局分配的公寓中。喜歡游山玩水的他,前幾年還常陪住在臺(tái)北的夫人赴各地觀光,近年游興大減,只是每周在跑步機(jī)上練練腿腳。
對這些年歲漸長的“叛逃者”們來說,那些驚心動(dòng)魄的逃亡生涯,已經(jīng)離開當(dāng)下愈來愈遙遠(yuǎn)。朱京蓉用“平淡”兩個(gè)字形容現(xiàn)在的生活,對他們而言,這份平淡亦是幸福。
無奈的“叛逃”
從1940年后期到1970年后期,每一個(gè)來自國民黨陣營的逃亡者,都曾讓那個(gè)時(shí)代的大陸民眾倍加確信,盤踞在小島上的“蔣介石賣國集團(tuán)”,是多么黑暗可怕。大陸改革開放后,這樣的逃亡者,又成為“臺(tái)灣人民響應(yīng)祖國和平統(tǒng)一號(hào)召”的鐵證。
相同的政治話劇在臺(tái)灣也不時(shí)上演,唯一的差異在于,大陸叛逃者大多成為“向往自由的反共義士”。為鼓勵(lì)更多的人起事,1958年,臺(tái)灣頒布《共軍官員起義歸來優(yōu)待規(guī)定》,按照起義者開來的飛機(jī)機(jī)型,獎(jiǎng)勵(lì)黃金,據(jù)說最高給過7000兩黃金。1960年代的大陸也出臺(tái)過類似政策。
但具體到每個(gè)“叛逃者”的身上,真實(shí)的逃亡原因卻未必和政治黃金有多少關(guān)系。
帶著朱京蓉一起回大陸的黃天明,從未公開透露過他回大陸的真實(shí)原因。據(jù)朱京蓉了解,黃天明曾是臺(tái)灣雷虎隊(duì)中能參與九架飛機(jī)飛行表演的資深飛行員,某次代人受過后,他被貶到空軍學(xué)校當(dāng)老師,始終心氣難平。
1956年逃來大陸的韋大衛(wèi),原是廣西人,1948年報(bào)考國民黨的海軍軍官學(xué)校,結(jié)果被軍艦拉到臺(tái)灣直接當(dāng)兵。雖然國民黨不斷宣傳“一年準(zhǔn)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以穩(wěn)定軍心,韋大衛(wèi)還是打定主意要逃回去。廣西的家里,有他的父母、大哥和兩個(gè)妹妹。離鄉(xiāng)7年后,韋大衛(wèi)才找到機(jī)會(huì)飛回大陸,那架“塞斯納”上,還藏著他的兩個(gè)朋友,這兩人后來一個(gè)安家南寧,一個(gè)落戶成都,他們回來的理由僅是“想家”。
王錫爵自稱逃離臺(tái)灣原因有三:想家、認(rèn)同兩岸統(tǒng)一,還有早先他在華航當(dāng)機(jī)長時(shí)發(fā)生的一次飛行事故。當(dāng)時(shí)他開著一架波音707從關(guān)島飛往夏威夷,快到終點(diǎn)時(shí)發(fā)現(xiàn)迷了路,差點(diǎn)讓上百名乘客迫降海面。最后雖憑他個(gè)人經(jīng)驗(yàn)安全到達(dá)目的地,事故主因是美國的航空公司提供給華航的電腦計(jì)劃有誤,美方在王錫爵落地后還打來電話致歉,但華航不敢追究美方責(zé)任,仍將王錫爵從正駕駛降職為副駕駛半年。耿耿于懷的王錫爵和在臺(tái)北的夫人都沒通個(gè)氣,就回了大陸。
從近年兩岸媒體的報(bào)道可見,“叛逃者”的動(dòng)機(jī)除了政治傾向等因素外,多半也包含個(gè)人的難言之隱。1981年開著美制F-5F戰(zhàn)斗機(jī)在福州降落的黃植誠,因非空軍官校畢業(yè),在軍中前途受打壓;1989年在廣東上空棄機(jī)跳傘的林賢順,無法忍受妻子引發(fā)的流言,來大陸后還要求與妻子離婚。
據(jù)大陸軍中人士介紹,從1946年到1989年間國民黨空軍有102人投奔大陸而解放軍里至少有15名軍官逃往臺(tái)灣,究其原因也基本不離個(gè)人家庭問題,或在軍中遭遇的種種難言之隱。
“文革”際遇
朱京蓉的被迫叛逃,使他成為這群“叛逃者”里最為特殊的人物:
1969年6月2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huì)堂接見了黃天明和朱京蓉。會(huì)上,周恩來宣布“朱京蓉協(xié)助教官駕機(jī)起義也立了功”。一直擔(dān)心自己下場如何的朱京蓉松了口氣。會(huì)后,中共安排他們前往大陸各地游覽半年,上海的紡織廠、造船廠、東北的鋼鐵廠,地下660米的煤礦,讓朱京蓉對大陸的生產(chǎn)力印象頗佳。
其時(shí)大陸正經(jīng)歷“文革”,他們參觀的工廠是否在正常運(yùn)作很難判斷,朱京蓉也沒有機(jī)會(huì)了解真正的大陸社會(huì)正經(jīng)歷怎樣的起伏,但當(dāng)時(shí)臺(tái)灣尚處于經(jīng)濟(jì)起飛前夜,那些工廠礦區(qū)本身的龐大已讓他們開了眼界。
一次偶發(fā)事件,曾讓他懼怕留在大陸。當(dāng)時(shí)他和同行軍官閑聊,3歲跟著父母到臺(tái)灣的朱京蓉,說自己從小就想當(dāng)飛行員,那名軍官聞之色變,說自己從小就立志為人民服務(wù),兩人爭執(zhí)了幾句,對方要批斗朱京蓉、朱京蓉哭了三天,提出去香港定居。“去了香港,臺(tái)灣也會(huì)派人暗殺你。”一句話,把他嚇了回來。
1969年11月,空軍司令吳法憲宣布兩人加入解放軍,朱京蓉被任命為空軍第九航空學(xué)校第二訓(xùn)練團(tuán)參謀,原是國民黨上尉的黃天明,被任命為第三訓(xùn)練團(tuán)副團(tuán)長,兩人均比在臺(tái)灣的軍職高出一級(jí)。
因不準(zhǔn)部隊(duì)參與“文革”,朱京蓉平穩(wěn)過了許多年。但進(jìn)入民航工作的韋大衛(wèi),在“文革”中歷經(jīng)折磨。
韋大衛(wèi)回大陸時(shí),正遇上政府搞公私合營。一位北京的私營業(yè)主告訴他,如果拒絕公私合營,政府不但要你養(yǎng)著工人,還不給你批生產(chǎn)原料。“政府也有它的一套。”韋大衛(wèi)的清醒讓他既不喜歡這些,也難討人喜歡。
“文革”開始后,他拒絕周恩來的保護(hù),和民航批斗他的人互貼大字報(bào)。1968年,民航專案組以“駕機(jī)叛國投敵陰謀”首犯的名義,將他送進(jìn)沈陽皇姑區(qū)監(jiān)獄。5年間,每隔一天他就得挨專案組的審訊人員一頓打,被逼承認(rèn)罪名。
1974年10月,已被轉(zhuǎn)移到北京繼續(xù)關(guān)押的他,乘看守疏忽,從瞭望臺(tái)上跳出高墻,溜進(jìn)城找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wù)院聯(lián)合接待室。接待人員將他的情況上報(bào)葉劍英,他才得以安然度過“文革”。那時(shí)他已被打斷過兩根肋骨,妻子也被專案組逼迫跟他離了婚。
比韋大衛(wèi)晚20年來大陸的王錫爵,有幸未遇此種波折。1987年,臺(tái)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夫人與他在北京重逢。
禁地
在部隊(duì)工作的近40年,朱京蓉從來不談臺(tái)灣,早年是他沒人可談,后來是怕惹麻煩主動(dòng)不談。
1970年的春節(jié)前,他剛到部隊(duì)時(shí),雖然是周恩來宣布過的立功者,卻沒人敢靠近和他說話。他被單獨(dú)安排在一個(gè)辦公室,到晚上辦公室又成了臥室。這年11月,他和同事介紹的工廠女工結(jié)了婚,他說從此下了班,至少有個(gè)能說話的人。
大陸開放后,經(jīng)濟(jì)日益代替政治成為大陸人的生活重心,部隊(duì)里的年輕人對臺(tái)灣也充滿了好奇,知道他經(jīng)歷的飛行員,有時(shí)跑來問問他臺(tái)灣什么樣,他總是笑笑,避而不答。這習(xí)慣還救過他一次。1976年他在青島療養(yǎng),排隊(duì)時(shí)遇見范園焱,兩人沒說話,第二年范園焱開著米格戰(zhàn)斗機(jī)逃到了臺(tái)南。“如果那次說了話,我就死定了。”朱京蓉說。
不能言說的臺(tái)灣,對朱京蓉而言更是不可歸去的臺(tái)灣。近十幾年,兩岸關(guān)系時(shí)好時(shí)壞,但即使關(guān)系最融洽時(shí),經(jīng)濟(jì)方面儼然一體的兩岸,對這些“叛逃者”們來說依然是一片禁地。
1992年從美國回大陸探親的李顯斌,1965年駕轟炸機(jī)逃往臺(tái)灣,一回大陸,即被青島市中級(jí)人民法院以投敵叛變罪處15年徒刑,2002年因病在大陸去世。而1975年逃至大陸的吳渺火,1998年返臺(tái)探親后,被判處4年徒刑。
前幾年,母親去世時(shí),朱京蓉曾向臺(tái)灣提出返鄉(xiāng)奔喪。畢竟臺(tái)灣從未宣布他屬于“叛逃”,黃天明和他在飛行訓(xùn)練時(shí)“失蹤殉職”才是臺(tái)灣當(dāng)年的官方口徑,即便他被宣布為叛逃罪,此時(shí)也已超過臺(tái)灣刑法中20年的追訴期。臺(tái)灣方面在商討許久后,答復(fù)他只能從機(jī)場直接到殯儀館參加葬禮,葬禮完畢后立刻返回機(jī)場。當(dāng)時(shí)軍職在身的他,看到條件如此苛刻就未能成行。
和朱京蓉一樣,王錫爵也是有家難回,至今他的夫人仍在臺(tái)北定居,他說:“兩岸不統(tǒng)一絕不回臺(tái)灣。”
舊事難忘
2009年春節(jié)后的一個(gè)下午,朱京蓉和記者講起幼年居住的眷村、愛唱川劇的母親,還有那個(gè)被父母留在四川江安老家,恨了他們一輩子的二哥。
每隔一會(huì)兒,他都會(huì)跑進(jìn)屋子里,拿出幾張照片,讓圖像幫助記者更好地理解那些過往。他的記憶充滿了細(xì)節(jié),就連當(dāng)年剛跨出飛機(jī)時(shí),拿著槍包圍上來的民兵留著什么樣的發(fā)型,都能描述得清清楚楚。
對于那些已經(jīng)模糊的記憶,朱京蓉還能夢到。比如1948年被母親抱著走上國民黨空軍運(yùn)輸機(jī)的場景已經(jīng)模糊,但在他的夢里,一次次出現(xiàn)的、長長的用鋼板搭建的野戰(zhàn)跑道卻永遠(yuǎn)都能保持明晰。
王錫爵也是如此。《鳳凰周刊》在一年多前曾刊登過臺(tái)灣作者郭冠英采訪王錫爵后,寫的一篇回憶他和張立義往事的文章。文中提到張立義駕機(jī)在包頭上空出事那天,本該輪到王錫爵開這架飛機(jī)。“郭冠英寫錯(cuò)了,那天就該是張立義。”王錫爵說。為了糾正這個(gè)細(xì)節(jié),他多次給《鳳凰周刊》發(fā)送傳真,直到雜志答應(yīng)刊登一個(gè)特別的聲明。
接受采訪時(shí),他給記者播放了一張光碟,那是朋友在他飛離臺(tái)灣后,錄入的港臺(tái)地區(qū)各家媒體對他的電視報(bào)道。面對電視里他在人民大會(huì)堂接受中外記者采訪時(shí)的畫面,他對本刊記者說:“我這輩子高調(diào)做事,低調(diào)做人。”
較之這兩人的念舊,韋大衛(wèi)甚至連年輕時(shí)的惡習(xí)都固執(zhí)地保留著,每頓飯都得就著三兩二鍋頭才吃得下,談起話來煙不離手。當(dāng)年就是靠著這兩樣,讓看守飛機(jī)的警衛(wèi)和他成了哥們,使得他有機(jī)會(huì)偷到“塞斯納”。
“今年,我很想回去看看”,朱京蓉說,他打算重提申請,嘗試突破禁忌。半年前,兩岸已經(jīng)實(shí)現(xiàn)“三通”,從北京直飛臺(tái)北僅需3小時(shí)。只是3小時(shí)的空間距離,不知他們還需花多久才能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