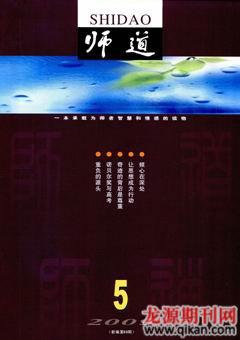奇跡的背后是尊重
胡元華
青年教師最苦惱的就是借班上課。這時,決定著課堂成敗關鍵的學情變得陌生了,原先依賴的教學習慣談不上了,師生之間的默契不存在了,善于發言的孩子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唱獨角戲,更擔心點到一顆“啞炮”,呼而不應或答非所問。可似乎苦什么就來什么,各種賽課、展示課又大多需要借班,所以,這種普遍的苦惱慢慢上升為恐懼。
有趣的是,大師們在異地展示時總是借班上課,他們不但不怕,甚至連提前進班和找原任教師了解情況都省了。我有幸和于永正、支玉恒、王松舟、孫雙金等大師共同參加過一些教學研討活動。作為晚輩,得見前輩大師的機會不多,所以格外珍惜,全程陪同,虛心討教,寸步不離。我驚奇地發現,課前他們無一不輕松自如,談笑風生,有決勝于千里的氣度;課堂上更是如魚得水,左右逢源,能收獲預期的精彩紛呈。一些原任教師聽課后更是連聲稱奇,說特別佩服的是那些原本不起眼或是崇尚沉默是金的孩子,在大師的課堂上竟然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語出驚人,表現突出。
關于此,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未得到答案前姑且稱為“大師效應”吧。和我有同感的朋友很多,許多同仁撰文稱這種現象為“奇跡”或“神話”。直到省電教館的小陳送來一些現場攝制的光碟后,我才從中找到了奇跡背后的答案。小陳指著于永正先生寫板書的一個鏡頭說:你看,于老師多么注重細節,他把身子蹲得很低,把頭偏向一邊,這樣就不會遮擋住任何一個孩子的視線了,所有人都能看到板書。從攝像的角度來看,這個鏡頭畫面完整,過程清晰,動感十足。小陳又播放了王松舟先生提問的片段,并介紹道:你看王老師提問時,從不說“你說”,而是說“你請”,同時主動遞上麥克風。一個字、一個動作,就足以讓孩子有受尊重的感覺,不努力發言都難。再看支玉恒、孫雙金老師和孩子對話的畫面,多么和諧、溫馨。這些畫面都有一個共同點:教師和孩子的距離很近,師生雙方的目光有交流,如友人見面敘舊。而且伴隨著交談,老師常有撫摸、搭肩、握手等肢體語言。我恍然大悟:原來大師和孩子不僅僅在對話,還通過眼神、動作等渠道傳遞著一種信息——孩子,我尊重你。而對比再看一些青年教師的實錄就很明顯了,課堂上教師關注的是自己的環節推進、引導言語,心中的答案早已界定,提問也好,互動也罷,只不過是流程而已,目標明確,急于求成。這樣的課,難怪給人以生硬的感受。至此,答案已經明確——奇跡的背后就是尊重。
再一琢磨,該給“大師效應”正名了。其實,它就是一種教育中的“霍桑效應”。霍桑一詞源于美國西部電氣公司的一間工廠。研究者最初進行實驗,目的在于研究工作條件與生產效率之間的關系,后來得出心理學上著名的“霍桑效應”,進而延伸到社會、人文、教育等領域。教育領域內的“霍桑效應”,指的是由于受到額外的關注而引起績效上升。不可否認,在許多原任執教者的潛意識中,孩子們已經被劃分為不同的類群:活潑的、善思的、沉默的,林林總總。而常態教學中,那些善于思考、喜好發言的孩子自然受到更多關注,享盡“馬太效應”帶來的福音;而沉默寡言的孩子則受“馬太效應”影響,越發不被關注,最后干脆心靈游離,在課堂上作一具“行尸”。而大師們沒有先入為主的偏見,隨機點請孩子,掏真心、露真意,用真情去和孩子交流,給與孩子最大的尊重。孩子受到這般“額外的關注”,自然激發出隱藏于心的潛能,努力回應做答,出現“績效上升”的現象。其實,孩子的突出表現反過來也使大師們的課堂教學藝術展示得淋漓盡致,更有看頭。
作為后生,我時常想起于永正先生,他年近古稀但卻童顏不老。他常說:微笑就是我的名片。你別以為微笑人人都會,先生這張名片的正反兩面,都用心地寫滿了一個詞——尊重。
(作者單位:福州教育學院一附小)
責任編輯鄒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