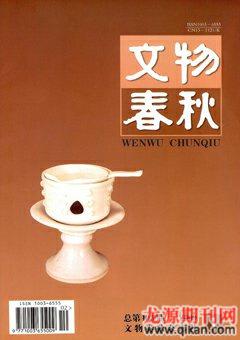偃師商城一期一段的相對年代疑議
尚友萍
【關鍵詞】偃師商城一期一段;鄭州商城第一期;外圍軍事據點;亳王;先商文化;早商文化
【摘要】湯放桀而復薄(亳),在三千諸侯大會上即天子位,此亳是鄭州商城。它標志著商王朝建立,早商文化開始。為鞏固新生政權并開疆拓土,商湯向商王朝外圍派出軍事力量,設立軍事據點,此即一系列圍繞鄭州和偃師的早商文化遺存。同時開始修筑偃師商城。偃師商城屬于早商文化,而鄭州之地則存在從先商至早商的連續文化——鄭州二里岡的文化遺存。結合外圍軍事據點的時間上限,可得出這樣的結論:以鄭州二里岡H9為代表的商文化遺存的早段是先商文化,其偏晚階段是早商文化的開始階段。偃師商城一期一段與商王朝外圍軍事據點的時間上限基本同時,相當于鄭州商城第一期偏晚階段。說偃師商城一期一段早于以鄭州二里岡H9為代表的商文化遺存,是沒有事實依據的。
偃師商城三期七段的分期框架是杜金鵬先生提出來的,關于其中一期一段的相對年代,杜先生說:“根據充分而可靠的地層依據,我們把偃師商城的商文化遺存分為三期,共七個發展階段。其中第一段文化遺存比以往人們所知道的以鄭州二里岡H9為代表的商文化遺存要稍早,而與二里頭文化的第四期偏晚階段大體同時,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商文化遺存。”[1]本文并不是對偃師商城三期七段的分期框架有疑問,而只對其中一期一段相對年代的判斷有疑義。
從理論上講,最早的商文化發生在偃師地區,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晚夏都城在偃師二里頭,商湯只有攻克夏都并打敗夏桀之后,才是夏朝滅亡以及商朝開始的標志。在此之前,商湯在鄭州地區無論是征伐韋、顧、昆吾,還是筑了一座名亳的商城,都是先商時期發生的事。這也是不會產生異議的事。
一、從已知最早的商文化看商湯滅夏的時間
因為本文的目的是要檢驗偃師商城一期一段的年代,所以這里所說的“已知最早的商文化”不包括偃師商城一期一段。至于鄭州地區的早商文化,因其與先商文化混在一起,故留待后文討論。
最早的商文化的材料來源主要有兩項,一是《中國考古學·夏商卷》[2],二是王立新先生的《早商文化研究》[3]。
目前已知最早的商文化遺址,有山西省垣曲縣的垣曲商城[4],山西夏縣的東下馮商
城[5],河南焦作市西南郊的府城商城[6]。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將垣曲商城的二里岡文化劃分為四期,對應原報告垣曲商城所劃分的兩期四段,其結論是:“各期的器物特征分別與鄭州商城第一期偏晚階段、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偏早階段的同類器相近,年代亦相當。”
《夏縣東下馮》一書將該遺址的夏商文化劃分為六期,并指出后兩期為商文化,相當于二里岡下層和上層。王立新先生將其各一分為二,分別推定為早商文化的一至四段。《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在此基礎上稍加調整,分為前后相繼的四期:“東下馮商文化一至四期的器物特征分別與鄭州商城的第一期偏晚、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的同類器一致,其年代亦相當。”
關于府城商城,《中國考古學·夏商卷》認為:“就目前發掘資料分析,發掘者認為,府城城址至遲修建于‘二里岡下層時期,廢棄于白家莊期晚段。”
前兩個遺址早商文化的上限年代完全一致,其所謂“鄭州商城第一期”,指的是以鄭州二里岡H9為代表的商文化,也就是過去常說的二里岡下層早段;其“偏晚階段”,指的是二里岡下層早段的偏晚階段。府城商城的年代也應與其相當。
除此之外,還有兩處早商文化遺存與以上遺址在時間上一致。其一是湖北省的盤龍城遺址[7]。盤龍城遺址的早商文化相當于鄭州商城文化的第二、三期,其第一期遺存是《中國考古學·夏商卷》的著者從發掘者認為的二里頭遺存中辨認出的:“我們注意到:在王家嘴下層等被發掘者認為相當二里頭時期的遺存中,卷沿、垂腹、分襠甚高的薄胎鬲等一些器物可上溯至早商文化的第一期。至于當地是否存在完整的相當早商一期的典型單位,很值得研究。”
另一處是陜西省關中地區的老牛坡遺址[8]。老牛坡遺址是一處以晚商遺存為主的大型遺址,其早商遺存屬于北村類型。有專家將該遺存統一劃分為兩大期(早商、晚商)六小期,其中第一、二小期為早商文化,年代分別估定為二里岡下層和上層時期。王立新通過器物分析,認為“老牛坡一期的年代應大致相當于二里岡遺址的第1、2組”,也就是二里岡下層的早段和晚段。
以上這些古遺存有兩大特點引人注目:一是時間上限基本相同,都發生在二里岡下層早段偏晚或相當時期;二是分布于以鄭州和偃師為中心的外圍(北、西北、西和南面)。這一現象是耐人尋味的——它使我們聯想到這與商湯打敗夏桀后的軍事行動有關,換句話說,這是商湯打敗夏桀后有計劃地在外圍設立的軍事據點。被派出的這些軍事力量既有鞏固新生政權的職責,同時也肩負著開疆拓土的任務。鄭州的東面出現商軍事力量的空白,更加證實了這一推測的可靠性。商夷結成聯盟打敗夏桀已是不爭的事實。豫東長垣縣宜丘遺址先商文化遺存[9],杞縣鹿臺崗先商文化遺址[10],說明豫東是商部族的勢力范圍。豫東的東面是岳石文化分布范圍,亦即東夷人的勢力范圍。商夷聯盟的存在是商湯在開國之初沒有向豫東方向部署軍事力量的原因。
商湯向外圍派出軍事力量,設立軍事據點,應該是在打敗夏桀之后。商湯滅夏桀后是先在外圍設軍事據點,還是先建偃師商城(假設如西亳論者所主張的,其性質為都城)呢?筆者認為應是前者。當然,向外圍派出軍事力量、設立軍事據點的同時,并不影響偃師商城的開工。也就是說,二者發生的時間可以同時,但如果非要在二者之間區別早晚,肯定是設軍事據點在前而建偃師商城在后。由此看來,這些外圍軍事據點的時間上限可能比建造偃師商城距商湯打敗夏桀的時間更近。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外圍軍事據點的時間上限就是距離商湯打敗夏桀最近的時間。
二、由春秋時關中的商族后裔看商湯滅夏的時間
老牛坡遺址在晚商時期的關中地區是商文化地方類型的代表,稱老牛坡類型。老牛坡的文化遺存在晚商時最為豐富,下限已延續至西周初年。讓我們感到欣喜的是,古文獻中記載了活動在關中地區的這支商族人在春秋時的蹤跡。《史記·秦本紀》載:“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集解》引徐廣曰:“蕩音湯。社,一作‘杜。”《索隱》云:“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史學界“湯居亳”之“杜亳”說即源于此。
活動在陜西關中地區的這支商族人不稱商王而稱亳王,是有講究的。商王是中央政權的稱號;亳是商族人對居住地的稱呼,其源出于商族祖先發祥之地——河北保定的古博水,稱亳王說明他們出身于正統的商貴族。其邑曰湯社,明含尊湯之意,說明他們以湯為始祖。《索隱》稱其為“成湯之胤”是完全正確的。
這樣一個結論說明什么問題呢?大家知道,夏商周時期的社會結構,是以血緣親屬關系結構起來的社會共同體,或者說,是按家天下的原則結構起來的社會共同體,這支以湯為始祖的商族后裔毫無疑問是商湯的宗族近支。山西垣曲商城、東下馮商城、府城商城以及湖北盤龍城早商遺存的主人,同關中這支商族人一樣,都應該是接受商湯的派遣,而且其第一代應該是湯的子侄輩。
這一結論進一步證實了前面的結論:這些外圍軍事據點的時間上限,就是距離商湯打敗夏桀最近的時間。
如果允許在時間的計算上有一點點誤差,那么,上面這個結論還有另外一種表達方式:早于這些外圍軍事據點的早商文化是不存在的;當然也可以這樣說,早于這些外圍軍事據點的商文化是先商文化。
三、由古文獻看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早晚
商湯即天子位的地點不在偃師,而在鄭州。《逸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于天子之座右。湯退, 再拜,從諸侯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后湯即天子之位。”[11]湯“復薄”之薄(亳),自然是鄭州之亳——因為偃師商城此時還沒有動工修建。就這樣,鄭州之亳在一夜之間由先商都城躍升為早商都城,商王朝的歷史由此掀開了新的一頁,早商文化的歷史也由此開始計算,只可惜《逸周書》沒有記下湯即天子位的具體時間。
從揮師南下到西進消滅夏桀,中間這段時間商湯是在鄭州度過的。他在鄭州地區做了兩件大事:第一,征伐韋、顧、昆吾。《詩·長發》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目前學界對韋、顧、昆吾的地望雖然還有分歧,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都承認這三地位于今鄭州地區。第二,筑城。從古文獻中看到,商湯在鄭州地區確鑿無疑地建造了一座名亳的商城。《尚書·商書序》:“伊尹去夏適亳,既丑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這里的“北門”,當然是指北城門,即亳城的北門。《呂氏春秋·慎大覽》:“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從伊尹離開亳城到返回亳城,長達三年,可見商湯在這里生活的時間不短。《慎大覽》又云:“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偃師二里頭為晚夏都城已是學界共識,既然商湯的軍隊由東而西進攻夏桀,自然證明商湯的軍隊是從偃師東方的鄭州地區出發的。《后漢書·逸民傳·野王二老傳》:“昔湯即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就是說,商湯消滅夏桀之后,又為鄭州之地的亳城修筑了外郭城。凡此種種,都說明鄭州之地有一座帶外郭城的商城,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商湯即天子位就發生在這里。應該承認,古文獻所記載的地點在鄭州,時間在先商,名亳,且在早商時又筑了外郭城的商城,就是我們現在已知的鄭州商城。
以上這些古文獻所提到的歷史事實,均發生在由先商向早商過渡的時期。由此我們看到,鄭州地區的商文化由先商進入早商是連續發生的,中間并不存在缺環。在鄭州地區具備這樣條件的商文化遺存非二里岡文化莫屬,這就是說,鄭州地區的先商文化就存在于二里岡的文化遺跡中,具體地說,存在于二里岡文化的最下層。顯而易見的是,偃師商城屬于早商文化,在那里不存在先商文化。如果說商湯即天子位時還沒有動工建造的偃師商城早于鄭州地區的商文化,那是無論如何也講不通的。
可是,為什么那么多人都眾口一詞地說偃師商城早于鄭州地區的商文化呢?持這種意見的論者應該想一想該怎樣越過古文獻這條鴻溝。換句話說,既然歷史文獻已經證明商湯伐夏必須先到鄭州之地而后到偃師,那么,為什么偃師商城的年代反倒早于鄭州地區的商文化呢?對此,趙芝荃先生寫了一系列討論文章,并于2003年著文對自己的研究作總結說:“這些研究曾論及商湯伐夏必須事先到達鄭州之地,然后才能西進滅夏,建立偃師商城,宣告夏亡商興,占領中原,統一天下。關于商湯開國之事應與鄭州之地毫無關系。”[12]這種解釋過于牽強。夏亡商興固然以位于偃師的二里頭夏都被攻占為標志,但商湯進軍偃師是由鄭州之地出發的;顯而易見,二里頭夏都被攻占時,偃師商城還沒有建立,商湯是回到鄭州的亳城即天子位的,怎么能說“關于商湯開國之事應與鄭州之地毫無關系”?再說,商湯“宣告夏亡商興”,也不必像趙先生所說的那樣一定要等到“建立偃師商城”之后。問題的關鍵是:趙先生既然承認商湯伐夏必須事先到達鄭州之地,那就必須承認在鄭州之地的商文化中,必定有一部分(其中的先商文化部分)早于偃師商城的商文化。可結果呢,趙先生比杜金鵬先生走得更遠——在杜先生偃師商城三期七段的分期框架中,一期一段文化遺存比鄭州二里岡下層一期早一個文化段;趙先生則為偃師商城的商文化劃分了六段,這個分期方案比鄭州之地的商文化整整早了兩個文化段[13]。按測年專家仇士華先生所說,“據考古學上的分析,一般文化分期之間的間隔約在50年左右”[14],那么兩個文化段就是100年。趙先生一方面承認“商湯伐夏必須事先到達鄭州之地”,同時又不承認鄭州之地有早于偃師商城的先商文化,這不是自相矛盾了嗎?
四、問題癥結試析
杜先生說,偃師商城一期一段文化遺存早到與二里頭文化的第四期偏晚階段大體同時。這個結論是怎樣得出來的呢?答:是與二里頭遺址的同類器物做類型學分析后得出的。杜先生針對偃師商城說:“1996~1997年對宮城北部灰溝的發掘,在灰溝的底部發現了目前所知偃師商城最早的商文化遺存(偃師商城第一期一段)。”接著將其與二里頭遺址的文化遺存進行比較,并得出結論說:“其陶器形制,與二里頭遺址的二里頭文化第四期偏晚階段的典型單位(如83YLⅢH23等)中所出的陶器基本相同。這類文化遺存的發現,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把商文化推定至二里頭文化的第四期階段。”[15]請注意,杜先生將參照物與被參照物比較后得出的結論是:二者的“陶器形制”“基本相同”。既然如此,按照類型學分析,二者不但年代相同,而且在文化類型上也應該是相同的。換句話說,二者不應該分屬兩個文化類別。
讓我們回到杜先生拿來做參照物的二里頭遺址Ⅲ區“四期偏晚”的典型器物上來。二里頭遺址Ⅲ區的發掘者將H1、H3、H5、H8、H10、H23等單位,列為二里頭文化的四期偏晚階段,并由此引出了一個在考古研究中產生極大影響的著名結論:“四期偏晚的這批陶器更加深了我們在二號宮殿遺址發掘時所證實的認識:二里頭四期是與二里岡期下層同時的,并直接發展為二里頭V期(二里岡期上層)。”[16]這個判斷問題很多,但最根本的問題表現為發掘者對“四期偏晚的這批陶器”的文化性質判斷有誤。到目前為止,學界已很少有人再認可那個與二里岡期上層同時的二里頭五期,而是把二里頭五期劃歸二里岡期商文化(下層、上層),并列于二里頭文化四期之后。比如,《中國考古學·夏商卷》明確表示,所謂二里頭五期“事實上已超出二里頭文化范疇”,并指出:“最近出版的《偃師二里頭》第一階段發掘報告,就把二里頭文化四期之后的商文化遺存,分別概括為‘二里岡下層和‘二里岡上層商文化的兩期。”[17]這就是說,《偃師二里頭》第一階段發掘報告已經放棄了“二里頭五期”的提法。王立新先生早就對“四期偏晚”尤其對杜先生強調的H23所出陶器進行了類型學分析,認為“有部分單位從組合上已不宜歸入二里頭四期,從性質上也不能歸入二里頭文化了”,結論是“暫將ⅢH23為
代表的遺存稱為二里頭早商期遺存的第1組”[18]。
依據這樣的結論,被杜先生拿來作參照物的二里頭遺址Ⅲ區“四期偏晚”的典型器物,本不屬于二里頭文化類型,而屬于早商文化,其年代與鄭州二里岡以H9為代表的商文化遺存是同時的。參照物的文化性質與年代如此,被參照物的文化性質與年代當然也應如此。這就是說,偃師商城三期七段分期框架中的一期一段,既不早于二里岡期下層,更不與二里頭四期同時。杜先生之所以將偃師商城一期一段年代推定至二里頭文化的第四期,問題出在對參照物的年代及文化性質的不同認識上。
杜金鵬先生認為偃師商城一期一段文化遺存,比以往人們所知道的以鄭州二里岡H9為代表的商文化遺存早了一個文化段,即早了50年。對此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偃師商城一期一段這50年,在整個商文化體系中處在怎樣一個位置呢?因為杜先生主張“偃師商城為夏商界標說”[19],所以,偃師商城一期一段在杜先生的商文化分期體系中當然是最早的商文化,或者說它是早商文化的排頭兵,在它之前是先商文化,在它之后,目前所知最早的商文化,就是被杜先生拿來與之做比較的以鄭州二里岡H9為代表的商文化遺存(鄭州商城第一期、二里岡下層早段、早商文化第一期、二里岡文化第一組、早商期遺存第1組)。到目前為止,在整個商文化分布范圍內,還沒有發現早于以鄭州二里岡H9為代表的任何一處早商文化遺存——現在沒有發現,我相信以后也不會發現,這是一段真正的商文化空白期。大家知道,偃師商城一期一段的劃分,主要依據的是“大灰溝”9層、10層的文化遺存。“大灰溝”現已證實為祭祀遺跡——這就是說,它是商朝王室貴族留下的文化遺存。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這個被杜先生稱為“目前所知最早的商文化遺存”,只孤零零地存在于偃師商城之內,而在偃師商城以外沒有發現一處呢?這種“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現象,該作何解釋?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商民族除了王室貴族等領導層外,還有更廣大的族人。為什么只有王室貴族留下了文化遺存,而廣大的族人卻沒有留下絲毫的蹤跡呢?難道在這50年當中,他們從人間蒸發了嗎?問題的答案只有一個:比鄭州二里岡以H9為代表的商文化還要早的早商文化遺存,根本是不存在的。
找出商湯在鄭州時期的先商文化,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早年鄒衡先生將鄭州地區以H9為代表的二里岡下層早段和南關外期商文化,指認為早商之前的先商文化[20]。李伯謙先生同意以H9為代表的二里岡下層早段為先商文化,而否認南關外期為商文化[21]。張立東先生“認為以鄭州C1H9為代表的二里岡文化第一組、下七垣文化(僅指漳河型)前三段和后岡二期文化較晚階段,應該是先商文化自后而前的三個階段”[22]。這就是說,二里岡文化第一組為先商文化的最后階段,被這些先生們共同認可。這些意見值得重視。鄒衡先生所說的鄭州地區以H9為代表的二里岡下層早段,張立東先生所說的以鄭州H9為代表的二里岡文化第一組,以及《中國考古學·夏商卷》所說的鄭州商城第一期,所指內容完全相同。聯系前面提到的商朝開國之初外圍軍事據點的時間上限——鄭州商城第一期偏晚階段,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鄭州商城第一期早段是先商文化的最后階段,而鄭州商城第一期偏晚階段則是早商文化的開始階段。
這樣一個結論決定了偃師商城的時間上限,不能早于鄭州商城第一期偏晚階段。也就是說,偃師商城的時間上限只能與商朝開國之初外圍軍事據點的時間上限——鄭州商城第一期偏晚階段——相當或略晚。這就是本文的結論。
————————
[1]杜金鵬:《偃師商城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52頁。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3]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4]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縣博物館:《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報告》,科學出版社,1996年。
[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縣東下馮》,文物出版社,1988年。
[6]袁廣闊、秦小麗:《河南焦作府城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0年4期。
[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年~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8]劉士莪:《老牛坡》,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9]鄭州大學歷史與考古系等:《河南長垣宜丘遺址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5年2期。
[10]同[2],第156頁。
[11]引文據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釋》,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79頁。
[12][13]趙芝荃:《評述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幾個有爭議的問題》,《考古》2003年9期。
[14]張雪蓮、仇士華:《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應用的系列樣品方法測年及相關問題》,《考古》2006年2期。按此文公布的數據,鄭州商城的年代為公元前1500年,偃師商城不足公元前1600年,后者比前者早了近百年,與趙芝荃先生的結論相近。測年數據是測年專家利用高科技手段得出的結論,自然應該認同。但疑問還是有的,比如鄭州商城年代的得出,所測對象有一件是間接材料——屬于二里岡上層一期偏早的井圈木,所得到最外輪的年代為公元前1400±8年,然后加兩個文化段(至二里岡下層二期偏早、再至二里岡下層一期偏早)計100年,得出“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測年結果與之相合”的結論。可是,如果按照杜金鵬先生發掘偃師商城得出的三期七段的分期方案,在二里岡上層一期至二里岡下層一期之間,存在四個文化段(加新增的第三段為五段),計200年,這樣算下來,對于二里岡下層一期,應該說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測年結果與之相合。
[15]同[1],第126~127頁。
[16]鄭光、張國柱:《偃師二里頭遺址1980~1981年Ⅲ區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7期。
[17]同[2],第70頁。
[18]同[3],第52~53頁。
[19]同[1],第169~195頁。
[20]鄒衡:《試論夏文化》,載《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1]李伯謙:《先商文化探索》,載《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22]同[2],第144頁。
〔責任編輯: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