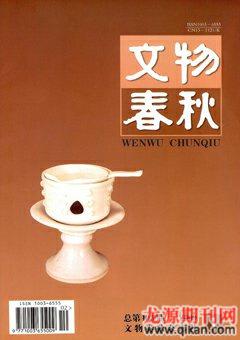關于冀北山戎的幾個問題
張立柱
【關鍵詞】冀北地區;夏商周時期;山戎;戎族;四壩文化
【摘要】本文以史籍記載結合考古資料,力圖梳理出商周時期活動于我國北方的山戎民族的一些軌跡,認為山戎人不是土著民族,而是夏商時期活動于西北地區的游牧民族西戎的支屬,商晚周初逐漸東遷進入冀北地區,是在冀北發展起來的戎族。
1998年我在承德參加會議時得知:山戎系春秋時期的部族名,活動區域包括今河北灤平和豐寧一帶,盛產戎菽、冬蔥。由此對山戎產生了興趣,總想搞清它的幾個問題。循著山戎的線索翻閱相關資料,發現山戎人與秋千有關系。史載:秋千本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者。后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繩懸木立架,……名曰秋千。山戎人還是最早發明并使用火鍋的,北京延慶龍慶峽山戎墓葬曾出土了青銅火鍋,底部有火燒的痕跡。其火鍋又分兩種類型:一是鍋灶聯體,下部點燃木柴,上部是銅鍋;二是單體火鍋,架于柴草之上將水煮沸。最近,我陸續查閱了相關的考古發掘報告及一些文物資料,慢慢梳理出山戎的一點梗概:一個消失了2000多年的古老民族,一個充滿神秘色彩又活潑生動的民族文化,經過文物工作者幾十年的艱苦努力,經過山戎尋覓者不懈的探索、分辨、比對,正在逐步揭開神秘的面紗。
山戎,華夏中國少數民族的一支,有過強盛,有過衰落,黃金時代在西周末到春秋時期,戰國中后期被秦和齊打散。在河北北部的燕山、軍都山一帶及潮河、灤河流域,有許多山戎人的墓葬和聚居地遺址,有他們的征戰場和祭祀地。山戎人有比較發達的畜牧業和種植業,手工業工具和產品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河北、北京、天津同屬于一個文化區,自西向東在赤城、宣化、懷安、延慶、豐寧、灤平、隆化、興隆、寬城、遷西、遷安、昌黎、撫寧等縣市,均有山戎遺跡的發現。
一、戎族——氏族社會時期的游牧民族
在新石器時代中葉,我國北方和西北高原與丘陵地帶是一片尚未開墾或尚未完全開發的地區。這里有草地、森林,野生動植物資源豐富,這片土地上的絕大多數民族仍然處于氏族部落狀態,被稱作西戎的氏族部落便是其中之一。
夏因禹建朝夏地、稱夏伯而有國。《尚書》注說:“冕服彩章曰華,大國曰夏。”夏是中原之國,對居于其東、西、南、北的不同氏族以衣著、居地或其它特點稱謂之,如、皮膚鳥夷、畎夷等。《尚書·禹貢》中有“夷”、“戎”、“蠻”的記述。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述了堯舜之時“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的傳說,還提到了“蠻夷率服”,“望夷猾夏”,“西戎、析支、義渠”等。可以這樣設想,既然堯舜時已有了戎的族稱,那么夏時存在是必然的。再者,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夷、狄、戎、蠻等字,而實際存在的族稱應早于文字的出現,所以戎族在夏時就已存在應為不爭的事實。
夏代的社會發展情況特別是少數民族的社會發展情況缺乏文字記載,這些年的考古成果尚不能夠把夏代的歷史全部連貫起來,所以文獻中零散的記述以及對考古資料的辨認研究都是值得關注的。《禹貢》中“黑水西河惟雍州”,是說它的地理位置和重要作用。古代九州之一的雍州位于黃河中游以西至甘肅張掖的廣大地區,其東部是夏族的主要分布區,而眾多的少數民族則居于雍州西部,這里就包括屬于西戎氏族集團的一些部族。戰國時魏國的史書《竹書紀年》提到夏代的畎夷:“帝葵即位,畎夷入于岐以叛。元年,踵戎來朝。” 宋代人著的《路史》說:“葵不務德,……于是犬戎侵岐居之。”后者說的犬戎就是畎夷。夏代后期他們入居于陜西岐山一帶,而岐山以北是他們的主要游牧區。《史記·匈奴列傳》還記有:“桀崩,其子淳維妻其眾妾,遁于北野,隨畜轉徙,號葷育,逮周日盛,曰獫狁。”葷育即熏育,殷時稱鬼方,西周稱嚴允,即犬戎。夏時期,我國北方和西北已經居住著稱為“熏育”、“畎夷”的戎族。
西戎是繼新石器時代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之后的四壩文化的主人,也是近4000年前的河西先民。西戎人距夏人的主要生活區不遠,容易借鑒夏人的先進生產技術,學習夏人的先進文化,在戎族中改革最早,先一步踏入了青銅時代。
四壩文化是由著名的考古學家安志敏先生命名的。1976年以后在甘肅永昌以西的河西走廊一帶發現黑、紅彩夾砂彩陶和直刃彎背青銅刀,錐、斧、鐮、矛、鏃等工具和兵器,還有鏡、鐲、臂釧、指環、耳環等裝飾用品。安先生發現這些陶器、銅器的工藝及紋飾既不同于馬家窯文化,也不同于齊家文化的特征,命名為四壩文化。經碳14測定,其存在年代相當于夏代中期。
商代稱諸侯國為“方”或“邦”,有關文獻上有“萬方百姓”、“萬邦為慶”,都是眾多的意思。居于商都北方和西北的有薰育、獫狁、犬戎、畎夷,甲骨文記有土方、鬼方、狄,從當時的社會發展進程看,這些都是部落群名稱。他們已經從夏時的零散部落組成了某種人群的共同體,仍然過著游牧生活,但是有不同的政治中心。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史稿》里說:“土方是住在今山西、陜西北部直到內蒙古河套以北的游牧民族。”鬼方“游動在今陜北、內蒙古及其以北的遼闊地區,是強大的游牧部落。”與土方、鬼方同時活動在商代中心區域西部、西北部的余無戎、燕京戎、奚落鬼戎、驪山戎、犬戎以及羌方、熏育、北羌等,較之夏時的軍事實力有所增強,散落的力量結成部落聯盟,為尋求新的牧場和狩獵場經常游動,與商朝屬地不斷發生沖突。商王武丁之前,這類記載較少,從武丁開始文獻資料多起來,僅殷墟甲骨卜辭就有數10條。
在這些記載中,多次提到羌,有羌方、北羌、河曲羌、西羌。《后漢書·西羌傳》說西羌源于三苗,本姜姓之戎的別種,被舜逐至三危,即河關之西南羌地。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析支、義渠、渠搜、昆侖都是羌人部落,又同為西戎集團成員。武丁伐羌,最多時用兵達13000多人,遠遠超過征土方時的5000人。羌人曾占領過商屬的大片土地和草場,武丁也曾俘獲大批羌人,還俘虜過羌人的部落首領。只要成為俘虜就變為被強制生產的奴隸,還可能被作為祭祀品或隨葬者。武丁及其后的征戰反映出羌人力量強大對商造成的威脅,說明爭奪的殘酷。郭沫若先生據甲骨文的記載得出結論:“殷人之敵在西北,東南無勁敵。”殷商時的“四夷”概念,在夏的基礎上又有發展,古籍中不僅較多地出現夷、狄、蠻、戎的記載,而且甲骨文中也把這些族稱固定下來。基于征戰的印記,象形文字的戎是一件兵器,用戎來稱謂西方的主要民族,西戎的概念逐漸形成。
周武王滅商,追謚封王上至古公為止。這個古公父在商武丁元年被“賜以岐邑”,成為諸侯,經多年苦心經營,為周人發展奠定了基礎。《尚書·武公》說:“至于太王,肇基王跡。”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竹書紀年》記載公季時期與西戎進行過多次戰爭:“三十五年,周王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徙之戎,捷其三大夫。”這些記載清楚表明,公季時期與西戎的戰爭頻繁而且十分激烈。
公季死后西伯侯繼位,是為周文王,他也多次興兵伐戎狄。《史記·周本紀》記文王受命,“明年,伐犬戎”。《竹書紀年》記有:“三十四年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尚書》疏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這個時期,周室伐西戎之力度也是相當大的。
周武王繼位后大行分封,特別將功臣、近臣封在與西戎、北狄打交道的重地。封首要功臣姜尚為齊王,召公長子為燕王,鎮守北方要地,將晉王封予成王弟叔虞,守衛山西曲沃到太原一線。《春秋左傳正義》稱姬發提醒他們注意“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即注意應因戎人的風土習俗。這時期的西戎因連年征戰,兵力受損,加之武王初立,軍師強勁,所以戰事相對平靜。
到周穆王時,仍對犬戎、西戎用兵不斷,加劇了民族矛盾。穆王孫周懿王在位時,“王室遂衰”,西戎和北狄同時伐周,迫使懿王遷都。《竹書紀年》記載:“懿王七年,西戎侵鎬。十三年翟入侵岐。十五年,自鎬徙都犬丘。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山戎,敗逋。”周宣王時接續出兵“西伐西戎”,及至周幽王時,“四夷入侵,中國皆叛”,褒姒亂政,國人悉怒,申侯與繒、犬戎攻幽王,殺于驪山下。幾代周王征伐西戎,最后還是申侯聯手戎人將周幽王推翻,也算歷史為戎人討回了一點公道。
周平王東遷,離開自武王至幽王經營了300年的鎬而遷都洛陽,主要原因是戎狄的軍事攻擊。《史記·秦本紀》記載:“周避犬戎亂,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奉詔伐戎,得勝,于是“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秦以岐為基地,逐漸發展成為春秋時代的西部強國。公元前623年,即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與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西戎民族集團自夏代開始活躍于西部和西北部地區,生息發展了1500年,其主力族群最終被秦國擊散。
二、山戎——商晚周初遷徙到冀北的戎族一脈
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列傳》中寫道:“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熏育,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這里說的“北蠻”應該是籠統方位,即北和西北;其中的山戎還不是春秋時的山戎,應當是后來被稱作北狄的游牧民族部落群;獫狁、熏育則是居于西部和西北,后來被稱作西戎的游牧民族部落。司馬遷生動地記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習性,我們從有關史料對西戎和北狄的描述中也讀到了相似情景。司馬遷接著記述了西戎的部分部落從古雍州以西到岐山以北,再到山西北部、內蒙古北部。《竹書紀年》則記載商與西戎、周與西戎連連征戰的歷程。這一方面說明義渠、析支、西羌、犬戎等西戎部落一直繁衍生息在西部、西北部,為生存發展不斷與商、周發生爭奪地盤的事,有時爭奪還十分激烈;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據此推斷:西戎民族集團中的部分部落面對殘酷的現實,面對被毀壞的家園,是不是已經開始遷徙轉移,尋找新的生存空間?東南是強大的華夏,往北走是荒漠一片,向東去才是最佳選擇,那里有自己的兄弟族群,彼此相距并不太遙遠,從而這些先民成為北戎、后稱山戎居地的最早踏足者和創業者。
《史記·匈奴列傳》寫道:“夏道衰,……其后三百有余歲,戎狄攻大王父,父亡走岐山,而豳人悉從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后,荒服不至。……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卻。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公與戰于齊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這段記載記述了公元前777年,申侯聯手犬戎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秦襄公救周王始秦發跡史,其后110年,齊桓公應燕國請求救燕伐山戎,這是公元前664年的事。從這個時間往前推,公元前13~11世紀是商武丁、帝辛時期,也是周人初起,商周與西戎連年征戰的時期。根據相關史料的追索,這個時期很可能就是西戎集團的某些部落嘗試東移的階段,其中有的到達陜北、晉北,也有的南進到華夏腹地又被迫轉移。《匈奴列傳》將西戎、畎夷、犬戎、戎夷、戎狄等作為一個民族集團來看待,字里行間流露出的西戎與北狄的關系是時而各自為戰,時而聯合抗敵。
犬戎引人注目。史載犬戎居地在今山西北部和內蒙古北部,周朝中期已經比較強大。犬戎所處介于北戎和西戎之間,應該與雙方都有聯系。也有文獻認為犬戎屬北狄民族集團,有一定的道理。山戎或北戎春秋時屬北狄,他們和犬戎本來就是相通的民族群落。
《匈奴列傳》接“周襄王遣使告急于晉”記述:“當是之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狄,居于河西、洛之間,號曰赤狄、白狄。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諸、緄戎、狄、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這里記述者仍將戎、狄合稱。隴西八戎含河西走廊中西部的戎、陜西北部的戎、晉北之戎和燕北之戎,他們分散居住,各有各的部族首領,有聯系而不相屬,百有余戎沒有統一的領導,也泛指西戎和山戎,并非專指山戎。
這樣的散落狀況,西戎人大約持續了600余年,而北戎歷200余年發展成軍事聯盟性質的族群,即將單個部落的“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組合為整個部落聯盟的軍事行動。春秋早期,北戎、山戎人開始強大起來,有些華夏之國也開始與戎人結盟,借用戎人的力量。有關史籍載:
公元前721年春正月,魯會戎于潛(今山東濟寧);秋八月,魯公與戎盟于唐(今山東金鄉);
公元前716年冬,周大夫凡伯聘于魯,戎伐凡伯于楚丘(今河南濮陽以北);
公元前714年冬,北戎伐鄭;
公元前706年夏,北戎越燕伐齊;
公元前677年夏,魯公追戎于濟西;
公元前674年冬,齊人伐戎;
公元前670年冬,戎伐曹;
公元前668年,魯公伐戎;
公元前650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史記·匈奴列傳》載:“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狄,戎狄朝晉。后百有余年,……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后義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于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時,……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
戎人強大之后伐魯、伐鄭、伐齊、伐曹,魏國、趙國與北戎、西戎邊界相接。這時候的西戎義渠部落被秦擊潰。公元前7至6世紀,中原國家兵器先進,齊國和趙國重兵征討,使山戎軍事聯盟的力量遭受重大挫折,有的部落融于趙、燕、齊、秦,有的投入東胡、匈奴。盡管零星山戎部族在冀北地區還存在,但作為一個統一的族稱,山戎在公元前5世紀中葉消失了。太史公在《匈奴列傳》終了發出感嘆:“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圣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戎族之中,包括西戎各部落、北戎和山戎部族,不是沒有出眾的組織與軍事人物,他們能在局部或一時的戰爭中取勝,但不能積累發展成戰略和全局的勝利,實在是因為缺乏指揮、運籌、才能、品德杰出的領袖人物!
三、戎人西來的判斷因由
山戎人不是土著民族,也不是春秋時期才來到冀北的,他們是西戎的支屬,準確地說是在冀北發展起來的戎族。他們在西周后期、春秋時期被稱為北戎,大概有西戎的因素吧。判斷戎人西來,大體有如下考慮:
其一,史籍對西戎的記載早于山戎,且有考古資料可予以佐證。甘肅省自1976年相繼出土了一批屬四壩文化范疇的文物,其所有人當歸西戎。《史記》中“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是指公劉世代為官掌管農業生產,夏朝中落失去官位,率其族人遷至戎地,改革西戎的風俗習慣,恢復農業種植,使那里的游牧民族改變為畜牧加農耕的生產方式,并建起了都邑。《鹽鐵論·和親篇》評價說:“故公劉處西戎,戎狄化之。”其時間是在夏代中葉,而史籍具體記載北戎的歷史事件則始于公元前8世紀。
其二,冀州開發遲于雍州,戎人東遷在情理之中。《尚書·禹貢》記載,夏禹將華夏分為九州,后依各州田畝等次順序排列是:雍、徐、青、豫、冀、兗、梁、荊、揚。田畝等次體現了各州開發先后的農業生產水平差異,顯然古雍州的發展水平在古冀州之前。游牧民族向尚未完全開發的地方轉移,合情合理。
其三,西戎和北戎的生活習性相近,葬俗相似,當屬同宗戎族。有關史料記錄了戎族的生活習性,從“兒”到“少長”到“士”,從“寬”時到“急”時,描寫得形象逼真。“利則進,不利則退”,這對于戎人不是難為情的事,這種天性決定了與之相關聯的習俗和習慣。葬俗是民族文化的展示形式之一。西周至春秋時期,隴西四戎與岐梁四戎合稱西戎八國,而晉北戎、燕北戎雖“自有君長”,但對歸去者的葬俗一直傳承,無大差別。四壩文化的墓葬形制多是長方形豎穴,以仰身直肢單體葬為主;燕北灤平、豐寧的山戎墓葬形制亦多為長方形豎穴,仰身直肢單體葬式。出土遺物同為夾砂紅陶器和動物紋飾青銅器。燕北山戎的家畜有馬、牛、羊、狗,沒有豬,隴西四壩文化域內也多是如此。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定,東移支屬仍保留著初始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征。
其四,相近的崇拜物,是同族的文化體現。西戎崇水怕水,因為有水才有草,而水大又會淹沒家園。山戎崇龍崇蛙,因為龍能生雨,有蛙就有水,灤平出土的蛙面石人屬半人半神的圖騰。西戎、山戎都崇犬,有的部落將族名與犬聯在一起,如畎夷、畎戎、犬戎。他們崇犬、愛犬,以犬為貴,北戎犬與玉、馬并稱三寶。因為狗是人類的朋友,更是游牧民族射獵或放牧逐狼豺的協助者。山戎墓多有狗殉葬,腿骨在下,頭骨在上,祈愿在另一個世界繼續為伴。
其五,商末周初的連年征戰是戎人東走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商周奴隸主需要更多奴隸充當會說話的勞動工具,另一方面,通過擴地占有戎人的資源,伐戎使之臣服,從而增強實力,霸有天下。從商武丁開始,經周公季歷、周文王、周武王,華夏王朝連續討伐西戎,雖然各有勝負,但戎人遭受了重大打擊,傷亡慘重,其生存環境和生產條件遭到了極大破壞。為了圖存尋找能夠生活的環境,為了免于被奴役、被殉葬,一些人、一些部落逃離祖居地走上遷徙之路。當然,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也造成逃離,部落內部矛盾引發的殘殺或仇恨使得一些人出走同樣可能。西戎民族集團的部分部落由西或西北往東遷移的時間,應該不晚于公元前12~10世紀,即商武丁中后期到周文、武、成、康前后。他們逐漸到達冀北山區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11世紀左右。勿庸置疑,相對集中的遷徙之外,還會有零星的遷徙者。其路線大致是:隴西→陜北→晉北蒙北→冀北,先在今赤城、延慶、豐寧、灤平一帶的燕山、軍都山、潮河、灤河流域扎根,然后擴展至今天津北及唐山、秦皇島北部一線。初稱北戎,后叫山戎。
其六,山戎不具有土著民族的特征。一個地方的土著民族,相關史籍特別是區域志書或多或少的會有些歷史記載,而冀北相關市縣的志書均沒有春秋之前關于山戎的史料,也沒有夏商周之際關于山戎的故事或傳說線索。就地理和生存、發展條件看,這里應是黃土民族,以農耕、畜牧相結合,而不是單一游牧民族。遠古時代及夏商周時期這里是尚未完全開發的“荒蠻之地”,初始民族難于以落后的生產方式有所作為。北戎、山戎的活動,應當是遷徙民族沿習已有的生產方式,然后逐漸發展壯大起來。
————————
主要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
2、范曄《后漢書》。
3、戰國·魏《竹書紀年》。
4、宋《路史》。
5、《尚書·禹貢》。
6、郭沫若:《中國史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
7、田繼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8、段連勤:《北狄族與中山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
9、甘肅省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載《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10、甘肅省文物局:《甘肅文物菁華》,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吉金鑄國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銅器精粹》,文物出版社,2002年。
〔責任編輯:許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