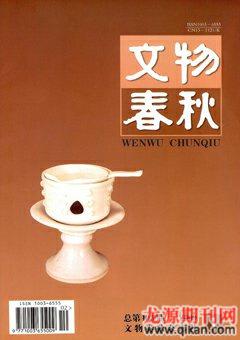簡論燕下都瓦當承載的文化信息
吳磬軍
【關鍵詞】燕下都;半瓦當;紋飾;燕國;都城營建
【摘要】燕下都瓦當承載著許多歷史、文化和社會影響等方面的信息,其紋飾和形制反映了燕國都城建設的發達和文化的繁榮,其最具代表性的饕餮紋飾可從先商及商代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文化背景和燕商關系等方面找到歷史淵源,對燕下都瓦當的分期研究可作為探討燕下都都城營建年代的重要依據。
燕下都瓦當自上世紀初出土以來,歷經百余年時間,以其豐富的紋飾種類、深厚的文化內涵、精美的制作工藝以及特有的半圓規制,引起了史學界、文博界和收藏界極大的關注。一些學者從其紋飾種類、內容題材、藝術特征以及地域特色等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就其承載的歷史淵源、文化背景、思想內涵和社會影響等方面的信息卻發掘得不夠深入。這里就這幾方面試作一些探討,不妥之處,還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一、瓦當的使用與經濟文化的繁榮
考古資料表明,目前發現的燕下都瓦當,按當面紋飾可劃分為10余個類別60余個品種,主要有饕餮紋、人面紋、窗欞紋、樹木卷云紋、幾何凸線紋、菱形紋、龍紋、鳥紋、獸紋、雙龍雙螭紋、山云紋、山形紋、卷云草葉紋等十幾大類。其中,在饕餮紋中又可分為雙龍饕餮紋、卷云饕餮紋、三角雙螭饕餮紋、雙狼饕餮紋、四狼饕餮紋、獨獸卷云饕餮紋、山形饕餮紋、山形花卉饕餮紋、山珠花卉饕餮紋等小類,而雙龍饕餮紋還可分為雙龍背項饕餮紋、雙龍背項抵角饕餮紋、雙龍背身俯首饕餮紋和雙龍團身仰首饕餮紋,卷云饕餮紋按細部紋飾特征也可分為若干小類;龍紋中又有獨龍紋和雙龍紋,鳥紋中有雙鳥紋和雙鳳紋,獸紋中又可分為獨獸紋、雙獸紋、雙鹿紋、四獸紋和怪獸紋等;山云紋按細部紋飾特征也可分為若干小類。
在形制上,燕下都瓦當碩大、厚重,一般常見瓦當的底徑在15~25厘米之間,壁厚1厘米以上;脊瓦和檐前筒瓦當面底徑一般在26厘米以上,壁厚在1.5厘米以上,瓦身長在75厘米以上;最大的垂脊筒瓦當面底徑達38厘米,壁厚近3厘米,瓦身長達1米以上。這些脊瓦和檐前筒瓦瓦身背表都飾有三段貼壓模制紋飾,為山形幾何紋和團龍紋相間構圖,脊瓦頂背部位又多飾以裝飾物及瓦釘,其尺寸之大,花紋之復雜,制作之精巧,都超過了在趙國故都、齊國故都和魯國故都等地發現的與其同時期的建筑材料。由此推想,承載這些大瓦的構架該是多么高大,它所依附的建筑物又應是多么宏偉!
燕下都故城遺址在今河北省易縣縣城東南2.5公里處,坐落在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間,整個城址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約8公里,南北寬約4公里,是戰國時期各國都城中面積最大的一座。從殘存的建筑夯土臺基看,城內武陽臺東西約140米,南北約110米,高約11米;望景臺東西約40米,南北約26米,高約3米;北垣外的老姆臺南北約110米,東西約90米,高約12米。也是戰國時期諸侯國都城中最為壯觀的[1]。
都城是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而宮殿建筑可以說是代表統治階級最高權力的象征。但時至今日,建筑物蕩然無存,建筑夯土基址和敗落的城墻殘垣也隨著歲月的流逝日漸縮小乃至消失,而附著在宮殿建筑物上的瓦當則在沉埋地下2000多年后不斷出土。我們可以通過這些瓦當去考證它所依附的建筑物的一些信息。
燕下都瓦當變化多端的紋樣,集中反映了燕下都宮殿、作坊以及居住建筑裝飾的藝術成就,瓦當紋飾所蘊藉的文化內涵和藝術魅力,使象征王權的宮殿和反映國家實力的都城建筑之宏偉氣勢又添華美和壯麗。燕下都瓦當與其他建筑材料和構件一樣,不但反映了燕國當時的工程技術成就、工藝水平、藝術風格和審美情趣,而且還反映出燕國都城建設的發達和文化的繁榮,折射出燕國的社會意識和民族崇尚[2]。
以上表明,作為戰國七雄的燕國,既能保持當地的優秀文化傳統,又在社會生產和軍事等某些方面具有高出其他諸侯國的水平,并且實際上具備了統一北方甚至稱霸中原的實力。方圓15公里的燕下都的規模和規格,就表現出燕國的這種雄才大略[3]。
二、瓦當半圓規制與姬燕政權的穩固
燕下都瓦當,從其產生、使用到戰國末期被秦統一,皆為半圓形規制,從未見過整圓形的,故學者、專家多稱其為“燕下都半瓦當”。它既不像趙、韓、楚等國的瓦當僅見圓形,也不像齊、秦、中山等國的瓦當既有半圓形又有整圓形。就是這樣一個看似平常的特征,卻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學術課題,承載著重要的政治、文化信息。
中國古代的房屋建筑由“茅茨”發展到瓦屋是在西周早期。當時瓦的基本形制有兩種,即筒瓦和板瓦,二者俯仰扣合以覆蓋屋頂及檐前部位。檐前部分的筒瓦常向外探出,以蔽護枋木和墻壁。西周中晚期,這部分筒瓦開始在底部施以半圓形當,即瓦當,起初的當面是素面,后來才設計紋飾圖案以裝飾美化[4]。生產力水平和建筑結構設計決定了瓦當的形制,隨后才是在半圓的空間內設計紋樣,而這些紋樣的構成則是由社會崇尚來決定的。到了戰國時期,一些諸侯國如秦、齊、趙、中山等有了圓形瓦當。瓦當變為圓形,更利于束水吐溜。而到了漢代,瓦當基本上均為圓形的了。我們從建筑學角度考察,當板瓦的弧度幾近消失,支撐板瓦的椽頭部位直露于外,這就需要比半圓再大一些的面積來遮護它,因此更為實用的圓形瓦當便應運而生。在圓形瓦當上設計紋樣,自然要比半圓形的余地大得多了。
如果我們對瓦當由半圓形向整圓形過渡、變化的分析是順理成章的話,那么探討的焦點就出現了。前邊提到,戰國時期燕下都都城的規模、規格都大于或高于其他諸侯國,其宮殿建筑也應更加宏大壯觀,其建筑技術和能力也不會低于其他各國,但是在燕下都宮殿建筑上乃至整個都城的作坊、居住建筑上,卻始終未出現圓形瓦當。難道說燕國的工匠就不知道圓形在遮護椽頭、紋樣設計和裝飾建筑等方面優越于半圓形嗎?關鍵在于,半圓瓦當一經產生,在其當面上設計紋樣時起,燕先民就賦予了它某些特定的意識。或者說,這半圓形的空間已經不是一種單純的幾何圖形了,它的確在象征著什么。
燕國從初封到滅亡,周姬政治一直延續到底而未發生改變,其政治改革較為薄弱。從召公瓿醴獾窖嗤蹕踩十三年滅于秦,其在位的40余位國君大多表現平平,如燕昭王之雄才大略者甚少,故不能使國家長盛不衰;而昏庸喪國如燕王噲者也甚少,才沒有使燕國滅亡或異姓當權。燕國的人民不愿意亡國,其他諸侯國的合縱、利用也沒能使其亡國。另外,也一直沒有形成像田氏代齊和韓、魏、趙三家分晉那樣的政治局面。從而使燕國的政權始終保持在姬姓君主手中,而未在政治變革上出現更加劇烈的動蕩[5]。
燕國北面為尚未開化的蠻貉,雖然隨時受到其威脅、侵擾,但直到為秦所滅,卻未先亡于北蠻,也可見燕國在“尊王攘夷”方面的貢獻。在燕國國君心目中,他們“于姬姓而獨后亡”,始終是正統的周的嫡系,他們從周那里繼承、延續下來的半圓規制與保持商周青銅器饕餮紋遺風一樣牢固。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燕先民以這半圓規制象征天地,姬燕政權則和這天地一樣長久、穩固、莊嚴,而又不容傾斜和倒置。不論是對內的“諸侯爭霸”,還是對外的“尊王攘夷”,它都是周的化身。
三、饕餮紋的歷史淵源和文化背景
我們通過對燕下都瓦當的分期研究發現,從春秋中期到戰國末年,饕餮紋貫穿了燕下都瓦當使用的全過程,其瓦當紋飾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饕餮紋以及由其演變而成的紋飾,或是含有饕餮紋遺意的紋飾,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這種從商周青銅器上直接承襲下來的標準的饕餮面像,在燕下都乃至整個燕國的瓦當上沿用了400多年的時間。“作為戰國時代標志性的瓦當面裝飾在各國都有新題材出現,唯燕國仍保持了以標準的饕餮面像為基本題材,不僅在燕下都而且在燕山以北遼西地區戰國遺址也普遍發現有饕餮紋瓦當。這種商周青銅器上的主體花紋從西周中期以后,在中原地區的青銅容器上逐步消失,而在戰國時期燕國仍流行。這說明,作為三代傳統的文化因素,原在燕山南北地區有著濃厚的歷史淵源。”[6]的確,同是春秋戰國時期,秦、齊、魯、趙、楚以及中山等國的瓦當上很少有饕餮紋的使用,而整個燕國瓦當卻一直把饕餮作為主體紋飾使用,而且出現最早,消失最晚,保持得十分牢固、凸顯和久遠。這一現象有著怎樣的歷史淵源和文化背景,又產生著怎樣的作用?這里,我們從商周青銅器的發展和燕山南北地域文化特征的角度作一考察。
關于商周青銅器的饕餮紋飾,自北宋《宣和博古圖》沿襲《呂氏春秋》中“周鼎著饕餮”之說,稱之為“饕餮紋”后,一直沿用至今。關于饕餮這一概念,古代文獻如《左傳·文公十八年》、《呂氏春秋·恃君覽》、《神異經·西南荒經》、《淮南子·兵略篇》等都有記載。所謂饕餮一詞,包括兩個方面,一為族群貪得無厭者,一為周鼎所見的一種藝術獸面紋飾。有學者稱,古代中國(華夏)人以饕餮稱異族或為異族之動物祖先,后來戰勝異族并圖于器物以表勝利[7]。這樣便把族群和圖像二者聯系成為一體。
據史載,夏商周三代有象征國家政權傳國之寶的九鼎。 “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在九鼎上鑄“百物”之像有著享神避邪的宗教力量,但就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夏鼎象物的圖像無從可見,夏代的陶器、玉器上也未曾見到“百物之備”的紋飾。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嵌綠松石獸面銅牌飾,確有一種簡意的獸之正面頭像的意味。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出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陶罐,器身上以紅、白色繪出饕餮紋,與以后商周青銅器上的饕餮紋圖案有著某種關系。
殷商時代的青銅器出土數量之大、品種之多、分布地域之廣、冶鑄技術之高、制作工藝之精前所未有,但凡禮器、兵器、食器、樂器等,幾乎無不鑄有繁縟的紋飾。 這一時期的饕餮紋以器物“棱鼻”為中心,兩個側面的獸形對接,構成一個尖角翻卷、雙目圓瞪、齜牙咧嘴的正面猙獰形象,成為當時流行的一種主體紋飾。 這種圖案化的形象就是宋儒依據《呂氏春秋·先識覽》所說的饕餮,它是兇狠貪婪的象征,也是權力和力量的標志。
周人淡化神權,確立了以“敬天”、“明德”為基本內容的政治教化思想,以宗法為根本的國家政治制度,以禮樂為核心的社會規范等,形成了一套相當完備的國家運行機制。“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一種不同于殷商神秘主義的新文化逐漸產生并發展成熟。在青銅禮器及藝術風格上的繼承雖然看似一種簡單拿來和照搬,但對饕餮紋賦予了一種嶄新的意義——戒貪,使原本就有的祈福避邪的獰厲美又添上了一種“廉明”的德行色彩。這便有了《呂氏春秋》“周鼎著饕餮,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的說法。西周所封的燕國原本就是商的屬地,這種殷商青銅器饕餮紋的延續也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大致了解了青銅器饕餮紋飾的歷史淵源和沿革變化。可以這樣認為,到了周代,饕餮紋已經成為集震懾、凝聚、恤惜、戒貪、廉明于一身的祈福避邪的美好載體,以莊嚴獰厲、尊貴華美的象征繼續在青銅器以及其他類別的重要器物上流行使用。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當這種貞祥的紋樣在其他諸侯國的使用已日趨淡化并在青銅禮器上逐漸消失時,為什么在燕國卻堂而皇之地轉移到了象征王權的宮殿瓦當上,而在其他諸侯國的瓦當上卻毫無痕跡呢?這里,我們試從先商及商代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文化背景、燕商關系和西周以降燕文化的發展影響這三方面尋找原因。
其一,考古資料表明,在商代青銅器上大量使用饕餮紋之前的先商時代,分布于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彩繪陶器上,就出現了以饕餮紋為代表的各種類似商代青銅器的花紋,它們從單元母題、基本組合到在器物上的布局,三方面都與商代青銅紋飾有相對應之處。由于紅山文化已經出現了被認為與饕餮紋起源有關的獸面紋飾,彩繪陶器在遼西出現較早,其上設計的饕餮紋可能是商文化饕餮紋的前身[8]。夏家店下層文化由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發展演變而來,與商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商晚期,即夏家店下層文化后期,在京津地區,兩種文化已經與先燕文化交融在一起了。當夏家店下層文化進入華北平原北部以后,就逐步地融匯于先進的燕文化之中了[9]。如果說夏家店彩繪陶器的紋飾圖案與商周青銅器上的紋飾風格存在著多層次的祖源關系的話,燕下都乃至整個燕國瓦當上饕餮紋飾的歷史淵源和文化根基也正是在這里。
其二,通過考古資料還可以看出,商人在燕山南北地區勢力很大,影響很深,當地的傳統文化與商文化有著很深的關系。北京琉璃河和遼西出土的商周時期燕國青銅器銘文都有當地殷遺服事于燕侯的記錄,包括商鉅族侯在內。周王封權勢持重的召公曖諮啵就表明了周王朝對北方的重視。據研究,商文化的起源與燕山南北地區有關。除上述談到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陶器組合上的饕餮紋與殷商銅器上的饕餮紋特征相一致外,還有與商王族關系密切的殷墟中的貴族人骨具有北亞、東亞蒙古人種相混合的特征等,都證明了這一點。在河北北部保定地區的易水流域,有早在商先公王亥、王恒時期就與商人發生過聯系的有易氏,后被商先公上甲微所征服。而在與北京接壤的河北淶水,清末曾出土了北伯、北子銅器,說明這里可能是卜辭所記“北方”部族所在地,這也說明了商人和商文化在這一地區的勢力和影響。
曹定云先生《商族淵源考》說:“燕山是燕人之山,燕人乃玄鳥氏族之先民也,燕山為商族的發祥地。商族根于太熳宀柯洌商文化源于紅山文化。”[10]另據文獻關于“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和“燕亳”的記載,燕、商可能是同祖。在燕下都的布局上,都遵循以東北為尊的規律,公墓設在城內宮殿區附近。從商以后戰國時期的燕國繼續強烈地表現出來的這一特征看,燕、商很可能共祖。
燕山南麓是紅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及其后續文化的分布區,而紅山文化和夏家店文化也都有一個由北向南移動的趨勢。這是燕國形成和發展自身文化的先決條件,也是燕國立國的基礎,所以自周初封燕一直到秦統一,燕國都城都建在燕山南麓。據此分析,在燕下都和燕國各地戰國城址普遍使用饕餮紋瓦當,應該是當地從紅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層文化發達的獸面紋延續下來的傳統。
其三,周初封燕之后的燕文化,既不是周文化的簡單傳播,也不是商文化的直接嬗遞,而是當時社會統治集團在兼并過程中,尊重當地燕族文化并相互交融,從而產生的一種新的文化——姬燕文化。姬燕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和關中周文化的聯系逐漸減弱,而和太行山東麓在商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的西周文化關系密切。新近在河北易縣七里莊遺址的考古發掘說明:“土著燕國文化發展到西周初年,與周武王分封形成的燕國文化相互糾纏、碰撞、融合,逐步形成一種新的燕國文化。”[11]亦即我們前面所說的“姬燕文化”。在以后整個周朝時期延綿不斷的發展中,這種新的燕國文化便成了以后燕文化的源頭。七里莊遺址距燕下都故城遺址不足5公里,呈西北—東南方向,由此可見,燕下都的修建有其特殊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燕國自西周初年封國后,以燕山南麓為基礎,其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連同它的文化,逐步向東北地區擴展。河北北部—北京地區—東北大部不僅是燕國控制和開拓的領域,而且是燕文化的大背景。
蘇秉琦先生曾說:“認識到了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中心的我國北方地區,在我國古代文明締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我們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一連串問題,似乎都集中地反映在這里。”[12]紅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無論是在有關我國文明社會的到來,還是在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都起著“脊梁”的作用。在整個燕國疆域內,中原農業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相互交錯、碰撞、融匯,燕文化則在這種背景中不斷發展變化。故此,在燕下都和整個燕國疆域內的瓦當主體紋飾饕餮紋,以及由其演變而成的其他紋飾,既有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根基,又有對商代青銅文化的直接承襲,還有對北方草原文化吸收而表現出的新面目。
四、瓦當分期、影響與燕下都的地位
公元前11世紀中葉,武王滅商建立周王朝,并實施了利用諸侯國拱衛王室的分封制。召公曄芊夂螅仍留在鎬京輔政,以其元子就國,在姬燕和商郾的奴隸主聯合的基礎上建立了燕國政權,以商郾的國都為都,其故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區的琉璃河董家林一帶。當時,今河北中部及遼寧西部地區分布著燕亳、薊、孤竹、肅慎等商朝的屬國,這些屬國在武王滅商中的政治態度各不相同,使得這一地區的政治、軍事力量錯綜復雜,其地理位置也因與周王室所封的齊、魯、衛、晉等國在軍事上遙相呼應、互為犄角之勢而顯得特殊和重要。西周初年,周王朝兩次東征,為燕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較長時期的穩定環境,燕國憑借著周王朝的軍事威勢統治著這一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