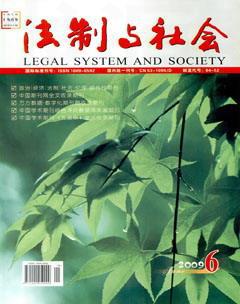比較法方法之辨析
劉芝秀
摘要比較法研究中,根據研究目的裁減研究對象的現象很突出,不利于深入了解比較對象。比較法中的功能比較和文化比較兩種基本方法都有其弱點:功能比較易于流入形式化,文化比較則容易陷入對象的迷陣中。本文指出必須取長補短,采取一種“整體觀下的目的性”,統率功能比較和文化比較,以一種有選擇、有重點同時又兼顧大局的態度進行比較法研究。
關鍵詞比較法方法功能比較文化比較目的性
中圖分類號:D9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6-001-02
與人文科學或者社會科學中的比較研究不同,比較法研究是“一項規范性和政策導向的事業”,①不可避免地采納一種工具理性的態度,如同德國一代法學巨匠耶林(RudolfvonJhering)在其巨著《羅馬法精神》(GeistdesromischenRechts)中所言:“外國法制之繼受與國家無關,僅是合乎目的性及需要之問題而已。如果自家所有的,同屬完善或更佳,自然不必遠求。惟若有人以奎寧皮藥草非長于自己庭院而拒絕使用,則愚蠢至極。”②——可以說,一種合乎目的性的“拿來主義”研究方法已經成長為比較法學研究的主流。
然而,比較法學因此陷入困境:一方面,目的是比較法學中不可或缺的指導,如果沒有目的性的指導,如何知道比較什么?為什么而比較?但是,另一方面,過強的目的預設又損害研究的真實性,因為其一,目的性容易將研究對象削足適履;其二,過于堅持目的很容易忽略研究對象的細微精奧。本文認為這種困境正是比較法方法中主客體二元緊張的難題,即比較法研究者主體的主觀目的性與研究對象客體的客觀實在性之間存在對立和緊張。本文將粗略思考這樣一種解困之道:在一種整體觀下的目的性的指導下,結合文化比較與功能比較兩種方法,緩解主客體二元的緊張。
比較法方法可以大致分為兩類:文化比較和功能比較。這兩方法各有其優長和缺陷,在具體研究中應當得到小心對待。
文化人類學者對比較法學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對法律的比較研究路徑]還能變成,從稍具實踐的角度看,一種在某一更集中的問題上(比如規范之根據與事實之說明間的關系,或者規范之說明與事實之根據間的關系)完成這種闡釋學的大努力(grandjete)。”③
對于強調文化是一種“意義之網”的人類學家而言,比較研究所關心的意義,是通過把行動置于更大的“分類甄別意指系統”中進行的觀察,在這種觀察中,不是削足適履地“解釋”研究對象,而是“理解”其自身所處環境的意義。
這里以哈佛大學安守廉教授的一項研究為例說明文化比較的意義。安守廉教授指出,長久以來,學者們都錯誤地將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中的一些禁止盜印官方文書、盜印他人典籍的法令當成現代知識產權的萌芽。事實上,如果充分考慮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可以發現,上述所有的禁止法令只是為了一個目的,即維護皇權的至高無上而實施的,雖然現實中也起到保護作者的版權、創作等等作用,但是制度設計絕對沒有在這方面的初衷;而且,同樣只要充分考慮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會發現古代文人對知識的繼受,重視的是薪火相傳的傳統和過去(past)的圣賢之言,絲毫沒有標榜自我創新的意思,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保護作者的知識創新似乎是沒有必要的。因此,所謂“現代知識產權在古代中國的萌芽”這個命題沒有太大的學術意義④。安守廉教授的這項研究給我們展現了一個文化研究的極佳實例,即將視野放進研究對象所處的歷史文化大背景中,充分理解其自身的邏輯,絕不能削足適履地“剪裁”對象,更不能為了現實的目的任意給研究對象附加一些“意義”。
不過,必須注意,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應用于規模小、同質性高、共識未遭破壞的村落共同體與應用于幅員廣闊、變動頻仍、難于形成共識的社會,其效果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即使在村落共同體中,人們的認識也可能千差萬別,比如,對“革命黨”的認識,阿Q與“假洋鬼子”不一樣,和吳媽也不會一樣。所以,堅持文化人類學的比較方法,很有可能只滿足于給讀者展現一幅生動復雜的生活活劇,不能夠給出一個相對明晰的指導路徑,當為了“學習和借鑒”而進行比較法研究時,文化比較所從事的工作只是第一步而已,更艱巨、更有實用價值的分析工作還遠遠沒有展開。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帕森斯創造了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方法用以分析社會,提出適應環境、實現目的、達到綜合、維持結構四個基本功能要件(AGIL)的系統分析框架⑤。利用由此發展起來的方法,通過功能性的比較,分析中介、媒體的作用,尋找功能替代項,似乎可以超越無法作結論的價值評判,同時能夠給工作的改善提供指導。在中國學者中,季衛東教授對功能主義方法有著深刻的體會,我們可以通過他的研究簡約觀察功能主義方法的優長和局限。法律試行的作法一向被認為是我國法制建設中的一種獨特作法。由于改革開放、建設市場經濟的舉措是史無前例的,一切改革都處在摸索過程中,為市場建設提供制度根基的法制建設也不得不在摸索中前進,于是立法上有“成熟一部,制定一部”的指導思想,現實中有法律試行、暫行規定等等措施。這種與“法治系統工程”相悖的作法,引起許多爭論,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現實的作法,應該得到重視,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機會主義的作法,會損害法治的權威。季衛東超出這些有關“法治價值”、“權威”的爭執,應用功能主義的方法,比較中國立法中法律試行與美國試驗主義法學的異同,從現實的作法中提煉出中國法律體系的反思性因素,尤其是從功能的角度看待試行機制對構建法治秩序可能具有的優勢和可能產生的危害,強調法律試行中的試錯機制、民主參與機制等,最后主張在程序理性的框架之內整合法律試行的反思因素,將恣意轉化為自由選擇⑥。應用功能主義理論分析現實,他的研究顯得相當細致,深入了對象的機體之內,而且有導向、有批判,并不以“存在即合理”為原則。
當然,功能比較也不是萬全之策。功能主義將整個社會視為一個體系來看,然后通過將這個社會化解成部分對整體、整體對目標的功能作用,力圖確定一套函數或指標以比較各個不同的社會,這種方法有極大的局限性。功能主義社會理論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幾乎是美國惟一的一門社會理論,指導著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其最大的弱點就在于,這套理論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形態當作了可以普適化的真理,所確定的社會功能分項幾乎都著眼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當前的情況,忽視了多樣性發展的可能。同時,功能主義進路傾向于靜態地描繪社會,將其用于指導第三世界的法制現代化改革時,無法反映出這些國家在外國資本和本國政治、軍事力量等多種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運行的復雜動態⑦。
比較法研究必須綜合文化比較(側重于理解客觀對象)和功能比較(側重于調試主觀目的)兩種方法。
比較的方法無論是歷史的比較,或是橫向的比較⑧,都存在一個如何安排主客體關系的問題:要么主體支配客體,使得對客體的研究合乎自己的需要(用比較法哲學家格雷·多西的術語講,這是一種“認知控制”的比較方法),要么聽任客體支配主體,使得客體神圣化,成為反過來宰制主體的支配性話語。在這種艱難的比較中,既不能過于突現目的的作用,又不能將目的完全拋棄。有限制地使用目的,或許不失為一種良策。問題是用什么來限制目的?我們發現,文化比較方法的難點在于,文化研究首先要求深入研究對象的內部,然而進入內部之后卻發現,該對象各部分對整體的認知存在千差萬別的差異,從而造成“不識廬山真面目”的尷尬局面;功能比較的難點在于,無法保證參照物的整體性,要么流于泛泛的橫向比較,要么將參照物化整為零,喪失整體性。這二者的缺陷正好都與一種整體性的概念有關,可以將之與目的導向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有限制的目的論:“整體觀下的目的性”(holismofpurpose)。
在主觀者目的和研究對象的實踐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距離,這種距離影響了比較法方法的應用,法國社會學家路易·迪蒙對此指出:在我們的社會與被觀察的社會都可能有A和B兩種因素,但是,在一個社會里是A從屬于B,在另一個社會里則是B從屬于A,于是進行簡單地對應比較就會不妥,必須將之與各自的等級系列整體相聯系,并且保持事實與價值的整體聯系性,才能做出有益的比較⑨。這就是一種“整體性”的比較思路,即將主體的目的和研究對象分別放在各自的等級序列里,不是將個別元素挑出來作比較,而是用整體與整體進行比較,目的在其中是作為切入口,也是作為重點指引。按照這樣的比較思路,比較法的任何課題都是文化價值、歷史傳統、現狀認識、未來預想的綜合比較。同時,由于有目的的存在,這類比較又不會落入空泛,而是圍繞著中心進行的思維發散式的比較。就目的觀念在整體環境中的地位而言,社會哲學家溫奇更明確地指出:“觀念和處境之間的關系是內在的關系。觀念是通過它在體系中扮演的角色來獲得意義的。”⑩依此說法,目的觀念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一種積極的姿態參與整體環境的塑造,在指導認識整體的同時也接受整體的修正。可以說,整體性的目的觀打破了主客體二元對立的思維范式,將一切有形的、無形的、文字的、行動的、思想的元素都納入比較之列。
就此而言,首先,整體觀下的目的性是為了突出重點,可以突出研究對象的某個方面,將其定為重點,從而防止文化研究在深入對象內部之后迷失在對象中的無所適從。
其次,整體觀下的目的性是開放的、流動的,可以加強研究者的自主性,能保證有相當針對性地切入研究對象的內部,同時又通過整體性敦促主體對目的進行自我反思,不斷地調試目的的指向,從而防止功能比較在將參照物化整為零之后形成不了系統的看法。
再次,文化比較因為在對象的意義系統中作業,反過來可以修正目的性裁減對象的弊端;功能比較因為分拆整體成為部分,又以功能性將部分與整體緊密聯系,反過來可以避免目的性忽略對象細節的不足,然后將這兩種方法得來的結果,重新放在整體性的關照下檢查,從而得出比較全面、踏實的研究結論。
最后,在整體觀下的目的性的領導之下,我們看到文化比較的意義甄別系統和功能比較的功能要件構成了一個統一體,即將研究對象的內部認知、共識、結構、功能統合在研究者的主觀需要下,形成了一個兼具動態變化和靜態功能的綜合體,為法律制度的比較和學習借鑒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