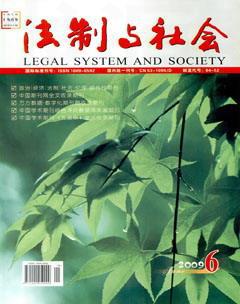論國(guó)際刑事法院管轄權(quán)補(bǔ)充性原則與非締約國(guó)主權(quán)的沖突
于 鵬
摘要2002年7月1日,人類歷史上第一個(gè)常設(shè)國(guó)際刑事司法機(jī)構(gòu)——國(guó)際刑事法院在海牙成立。但是成立后的國(guó)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quán)與非締約國(guó)主權(quán)問題一直是國(guó)際社會(huì)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國(guó)際刑事法院羅馬規(guī)約》中有關(guān)管轄權(quán)的規(guī)定與傳統(tǒng)的國(guó)家主權(quán)原則存在矛盾:主要體現(xiàn)為在檢察官啟動(dòng)調(diào)查程序階段產(chǎn)生的沖突。在本文中將會(huì)針對(duì)這些問題提出解決措施。
關(guān)鍵詞國(guó)際刑事法院補(bǔ)充性原則非締約國(guó)主權(quán)
中圖分類號(hào):D926.2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009-0592(2009)06-149-02
一、國(guó)際刑事法院管轄權(quán)補(bǔ)充性原則及其提出
國(guó)際刑事法院(ICC)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gè)常設(shè)國(guó)際刑事司法機(jī)構(gòu),于2002年7月1日在荷蘭海牙正式成立。該法院以《國(guó)際刑事法院羅馬規(guī)約》(以下簡(jiǎn)稱“規(guī)約”)為其設(shè)立依據(jù),目的在于有效打擊那些國(guó)際社會(huì)所關(guān)注的最嚴(yán)重的犯罪,從而使這些罪犯不再逍遙法外。①截止到目前為止②,批準(zhǔn)規(guī)約的締約國(guó)總數(shù)已達(dá)105個(gè)。但是,ICC的管轄權(quán)與國(guó)家司法管轄權(quán)之間的關(guān)系一直倍受世界各國(guó)的質(zhì)疑與關(guān)注。
在規(guī)約的制定和投票過程中,我國(guó)代表團(tuán)認(rèn)為ICC的管轄權(quán)近乎確立了普遍管轄權(quán),這將有損于第三國(guó)的國(guó)內(nèi)司法主權(quán),影響第三國(guó)的國(guó)內(nèi)司法程序;實(shí)際上授權(quán)ICC判定任何國(guó)家(包括非締約國(guó))行為的權(quán)利,這將使ICC成為凌駕于國(guó)家之上的超國(guó)家的司法機(jī)構(gòu)。③
針對(duì)各國(guó)的提案與建議,ICC的締造者們?cè)谝?guī)約中制定了補(bǔ)充性原則,即將ICC司法管轄權(quán)作為在特定情形下對(duì)國(guó)家司法管轄權(quán)的補(bǔ)充,而非絕對(duì)可以完全替代后者,避免其成為超越國(guó)家主權(quán)之上的國(guó)際司法特權(quán)。這說明,ICC管轄權(quán)應(yīng)當(dāng)尊重國(guó)家主權(quán)、維護(hù)國(guó)家司法主權(quán)。其中,規(guī)約對(duì)案件可受理性的規(guī)定是這一原則在司法實(shí)踐中的最直接體現(xiàn),可謂“ICC運(yùn)作的基石”④。
二、補(bǔ)充性原則與非締約國(guó)司法主權(quán)的沖突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4條明確規(guī)定:“條約非經(jīng)第三國(guó)同意,不為該國(guó)創(chuàng)設(shè)義務(wù)或權(quán)利。”第35條進(jìn)一步規(guī)定:“如條約當(dāng)事國(guó)有意以條約之一項(xiàng)規(guī)定作為確立一項(xiàng)義務(wù)之方法,且該項(xiàng)義務(wù)經(jīng)第三國(guó)以書面明示接受,則該第三國(guó)即因此項(xiàng)規(guī)定而負(fù)有義務(wù)。”因此,國(guó)際條約的效力應(yīng)當(dāng)僅限于締約國(guó),而不得任意擴(kuò)張至非締約國(guó)。ICC的補(bǔ)充性原則雖然避免了和非締約國(guó)司法主權(quán)相沖突的大多數(shù)情形,但是并沒有完全排除這種可能。
根據(jù)規(guī)約第13條的規(guī)定,ICC檢察官啟動(dòng)調(diào)查程序的情況有三種:締約國(guó)提交情勢(shì)、聯(lián)合國(guó)安理會(huì)提交情勢(shì)和檢察官自行啟動(dòng)調(diào)查程序。這三種啟動(dòng)調(diào)查程序的方式都會(huì)引起ICC和非締約國(guó)司法主權(quán)的沖突。具體論述如下:
(一)締約國(guó)提交情勢(shì)產(chǎn)生沖突
根據(jù)規(guī)約第12條的規(guī)定,只要犯罪人國(guó)籍國(guó)或犯罪地國(guó)中有一國(guó)接受了ICC的管轄,則ICC就對(duì)案件享有管轄權(quán)。這樣的規(guī)定勢(shì)必會(huì)造成這樣一種情況,即:甲國(guó)公民或國(guó)家公務(wù)人員在乙國(guó)犯罪,乙國(guó)作為犯罪地發(fā)生國(guó)接受了ICC的管轄,而作為犯罪人國(guó)籍國(guó)的甲國(guó)則沒有接受ICC的管轄。根據(jù)規(guī)約,只要乙國(guó)向ICC提交了情勢(shì),那么ICC對(duì)該案件就享有了當(dāng)然的管轄權(quán)。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甲國(guó)不接受甚至抵觸ICC的管轄權(quán),ICC仍然可以對(duì)案件進(jìn)行管轄。也就是說,任何具有司法管轄權(quán)的非締約國(guó)都不能夠以不接受ICC的管轄為理由而免除ICC對(duì)其正常司法程序的干擾和影響。
在本例中,ICC管轄權(quán)的產(chǎn)生來自于乙國(guó)這一締約國(guó)的情勢(shì)提交,在締約國(guó)依法定程序提交情勢(shì)讓渡其國(guó)內(nèi)管轄權(quán)之后,ICC作為締約國(guó)國(guó)內(nèi)管轄權(quán)的補(bǔ)充則可以行使當(dāng)然的管轄。但是,在本例中ICC要實(shí)現(xiàn)其管轄權(quán)就必須要給甲國(guó)這一非締約國(guó)施加一定的義務(wù)——將本國(guó)國(guó)民交由ICC管轄——而甲國(guó)的管轄權(quán)就因?yàn)镮CC的這種補(bǔ)充性管轄權(quán)而喪失。也就是說,ICC的補(bǔ)充性原則在無形中給非締約國(guó)施加了當(dāng)然的義務(wù),在不經(jīng)國(guó)家同意的情況下對(duì)非締約國(guó)的義務(wù)做出了規(guī)定,損害了非締約國(guó)的國(guó)家司法主權(quán),違犯了《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相關(guān)規(guī)定⑤。
(二)檢察官自行啟動(dòng)調(diào)查程序產(chǎn)生沖突
根據(jù)規(guī)約第15條的規(guī)定,檢察官可以自行根據(jù)有關(guān)ICC管轄權(quán)范圍內(nèi)的犯罪的資料開始調(diào)查。而檢察官啟動(dòng)調(diào)查的階段有二:情勢(shì)的調(diào)查階段和案件的調(diào)查階段⑥。在情勢(shì)調(diào)查階段,檢察官可以跟據(jù)自己掌握的信息進(jìn)行調(diào)查,而不必考慮案件的犯罪地國(guó)和犯罪人國(guó)籍國(guó)是否接受ICC的管轄。這也就是說,“檢察官可以對(duì)非締約國(guó)領(lǐng)域內(nèi)實(shí)施的或非締約國(guó)國(guó)民實(shí)施的犯罪進(jìn)行調(diào)查和起訴,而且ICC可以對(duì)這類案件行使管轄權(quán)。”⑦在案件調(diào)查階段,檢察官的調(diào)查雖然要經(jīng)過預(yù)審分庭的同意與制約,但是“實(shí)踐中也不能否認(rèn)預(yù)審分庭的決定有時(shí)會(huì)受到檢察官意志的影響,而認(rèn)可檢察官的請(qǐng)求。”⑧所以,ICC這種強(qiáng)化檢察官功能的規(guī)定實(shí)際上又造成了ICC與非締約國(guó)司法主權(quán)的沖突。
(三)聯(lián)合國(guó)提交情勢(shì)產(chǎn)生沖突
聯(lián)合國(guó)提交情勢(shì)的依據(jù)是《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第7章,通過對(duì)聯(lián)合國(guó)所有會(huì)員國(guó)(包括非締約國(guó))產(chǎn)生國(guó)際法意義上的拘束力,(下轉(zhuǎn)第156頁)(上接第149頁)來推定只要聯(lián)合國(guó)安理會(huì)提交了情勢(shì)則表示同意接受ICC的管轄權(quán),這恰恰造成了ICC與非締約國(guó)的司法主權(quán)沖突。
2005年3月31日安理會(huì)通過1593(2005)號(hào)決議,決定把2002年7月1日以來蘇丹達(dá)爾富爾局勢(shì)問題提交ICC檢察官。雖然蘇丹政府于2000年9月8日簽署了規(guī)約,但是至今未批準(zhǔn),也沒有自愿接受法院對(duì)有關(guān)犯罪行使管轄權(quán)。在安理會(huì)提交之后,蘇丹政府一直強(qiáng)烈反對(duì),并以非締約國(guó)為由對(duì)聯(lián)合國(guó)安理會(huì)的決議采取拒絕的態(tài)度,拒絕接受ICC的管轄權(quán)。這從實(shí)證的角度證實(shí)了ICC與非締約國(guó)司法主權(quán)沖突的存在。
三、ICC補(bǔ)充性原則與非締約國(guó)司法主權(quán)沖突的解決
針對(duì)上文中提到的幾點(diǎn)沖突,我將提出以下幾點(diǎn)解決建議:
第一,規(guī)約第12條的規(guī)定應(yīng)該加以補(bǔ)充,即:在犯罪的發(fā)生地國(guó)或犯罪人國(guó)籍國(guó)一方接受ICC的管轄后,如果另一方不是規(guī)約的締約國(guó),那么ICC應(yīng)該和另一方進(jìn)行協(xié)商。協(xié)商結(jié)果無非有二:
1.另一方愿意接受ICC的管轄,那么將由ICC進(jìn)行管轄。
2.另一方不愿意接受ICC的管轄,那么應(yīng)該先由該國(guó)進(jìn)行管轄。在此種情況下,如果該國(guó)對(duì)該案件進(jìn)行了合理的管轄,則ICC對(duì)該案件不再管轄;如果該國(guó)的管轄出現(xiàn)了第17條規(guī)定的相關(guān)情況,則根據(jù)補(bǔ)充性原則由ICC繼續(xù)進(jìn)行管轄。在此種情況下,非締約國(guó)已經(jīng)對(duì)本案實(shí)施了管轄權(quán),ICC的管轄已經(jīng)不會(huì)再干擾和影響非締約國(guó)的正常司法程序,也就不再存在ICC管轄權(quán)與非締約國(guó)司法主權(quán)的沖突問題了。
第二,規(guī)約第13條對(duì)檢察官的權(quán)力進(jìn)行適當(dāng)?shù)南拗?既要限制檢察官過于強(qiáng)大的權(quán)力,又不要減損檢察官應(yīng)有的獨(dú)立性,能夠有效履行追訴規(guī)約第5條所規(guī)定的國(guó)際犯罪的神圣職責(zé)。這可以通過以下三個(gè)方面的補(bǔ)充規(guī)定來實(shí)現(xiàn):
1.限制檢察官情勢(shì)調(diào)查的范圍,在啟動(dòng)情勢(shì)調(diào)查時(shí)就要限制在有管轄權(quán)的范圍內(nèi)。并且應(yīng)該考慮到案件可受理的相關(guān)情況,即將案件調(diào)查階段的要求提前到情勢(shì)調(diào)查階段。
2.限制檢察官就某一案件向預(yù)審分庭重復(fù)提出請(qǐng)求的次數(shù),并且要限制兩次請(qǐng)求提出之間的時(shí)間間隔。這樣就可以避免預(yù)審分庭因?yàn)闄z察官的堅(jiān)持而受到影響。
3.安理會(huì)提交案件的時(shí)候預(yù)審分庭要考慮案件的實(shí)際情況,對(duì)有爭(zhēng)議的案件由檢察官進(jìn)行補(bǔ)充調(diào)查,如果存在規(guī)約17條規(guī)定的情況則由ICC進(jìn)行管轄。否則就由有管轄權(quán)的國(guó)家進(jìn)行管轄。
四、結(jié)語
相信修正后的補(bǔ)充性原則將在實(shí)現(xiàn)國(guó)際正義、維護(hù)法律公正、保障人權(quán)等方面起到更加強(qiáng)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