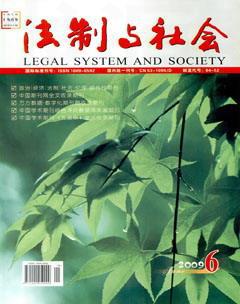論應急狀態下期待可能性理論及其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
王媛媛 蹇林君 張邦鋪
摘要本文擬從期待可能性理論的概念出發,對期待可能性引入的必要性加以分析,最后對期待可能性理論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提出了相關建議。
關鍵詞期待可能性地震司法濫用
中圖分類號:D920.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6-0171-01
一、期待可能性理論的概念
行為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無可奈何被迫實施了違法行為,其刑事責任如何,這就是期待可能性問題。法律只能要求人們做其有可能去做的事,不能強迫他人做其不可能做的事。對于行為人的行為,若要確認其確實有罪,必須根據其行為當時的具體情況,能夠期待其實施適法行為而不為犯罪行為。如果根據其行為當時的具體情況,能夠期待行為人為適法行為,則為有期待可能性;反之,則為無期待可能性。無期待可能性成為阻卻責任的重要事由。即行為人在不得己、在無法選擇的情況下的違反刑法的行為,為無期待可能性,不能評價為犯罪。
二、期待可能性引入的必要性分析
5·12汶川特大地震,形成了特殊的社會環境,也出現了特殊的犯罪行為,如妨害公務行為、災民的盜竊行為等,也就是我們平常說的“情有可原”,這些涉震刑事案件完全可以用期待可能性理論詮釋,對案件作出恰當的處理,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期待可能性的引入可以解決社會危害性所引發的諸多矛盾。在司法實踐中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行為人的行為雖然具有客觀的社會危害性,但是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確實不合理,而要減輕或者免除其刑事責任又沒有合理依據,而且還可能違背罪刑法定原則。這些現象使我國刑法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顯得缺乏應有的靈活性。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危害性理論是造成該現象的主要根源,因此社會危害性理論受到越來越多的批判。社會危害性作為衡量刑事責任的標準具有不確定性、模糊性、潛在的超法規性以及欠可操作性等弊端。期待可能性的引入為免除或減輕行為人實施某行為,就應當免除或減輕刑事責任提供了合理的依據。因為如果確實不能期待行為人為適法行為,就應當免除或減輕責任,這與刑罰謙抑性是一致的。
三、期待可能性理論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
期待可能性的標準問題,即有無期待可能性,以什么為標準去進行判斷。如果標準不明,在實際應用中就會造成混亂,破壞法的統一性和嚴肅性。筆者認為期待可能性的有無及大小的判斷標準問題應采用“行為人標準說”。因為期待可能性理論的設立就是為實現具體情況下的實質正義和個別正義,而且個人責任是責任主義的基本要求,法律只能對行為人的個人行為及其所體現的人格態度予以非難和譴責。所以期待可能性判斷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是行為人自身的狀況和行為時的具體情況,站在行為人的立場上,設身處地地考慮其作出意志選擇的可能性,脫離具體的行為人狀況和具體的行為環境,就不可能實現期待可能性所追求的個別正義。
從輕處理應急狀態下(如:地震中)的特殊刑事案期待可能性應當放在責任論中,在考察行為人是否具有責任能力、違法性意識之后,再考察行為人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如果行為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則可能免除行為人的責任,也可能減輕行為人的責任。由于個人責任是現代刑法的基本原則,因而判斷期待可能性的有無、程度的標準,只能求之于行為人,即在判斷行為人行為時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時,應以行為人本人的能力為標準,在具體的情況下,能夠決定期待其他適法行為是否可能,根據行為人本人的能力,能夠期待其為適法行為的,則具有期待可能性,否則則無期待可能性,應當免除或者減輕責任。同時,應允許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適用超法規的期待可能性阻卻或減輕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并應持慎重態度。
地震中特殊刑事案犯罪主體的主觀意圖與普通刑案有區別。期待可能性理論對于刑事司法的指導意義集中體現于挖掘行為主體在特殊情況下實施犯罪的主觀意圖,以此明確在地震特殊時期,一些犯罪主體的特殊心態。如災民因生活所迫所實施的盜竊,有別于出于奢侈享受實施犯罪的群體。災區發生的特殊盜竊案,應當屬于生活沒有依托的表現形式之一。地震中特殊刑事案有強人所難之處。期待可能性理論的核心在于刑法不強人所難,故判斷生活無著者從事適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強度不能脫離本人的精神狀態與經濟狀況,并應當通過其行為對象的被害情況進行側面校驗。如盜竊案為了生活所需盜竊電視,當然電視也有別于生活必須品,有一定的期待可能性;妨害公務案件,當事人回家看望親友,救助親友是人之常情,他選擇違反交通管制是他的唯一選擇,具有較強的期待可能性。特殊時期的特殊刑事案只能作從輕判斷。期待可能性缺失的認定,應從嚴把握,必須注意各種利益的平衡以及利益重要性的比較。
如何避免司法濫用的缺陷?無期待可能性作為超法規責任阻卻事由并且采用行為人標準,無可避免會引起人們關于是否會造成司法濫用的擔心。從維護法律的安定性的角度來看,對其適用要進行嚴格的限制,因此筆者認為法律有必要明確期待可能性的適用原則和程序以避免司法濫用。可以將期待可能性的適用限制在少數的非常規、應急狀態的情況,比如地震中。有關期待可能性適用的程序性的規定,如在審判階段不應由法官依職權提出,期待可能性有無及大小應由辯護方作為辯護理由提出,再由法官依據行為人狀況與行為時具體情況作出裁判,如果辯護方并沒有將期待不可能性作為阻卻責任的辯護理由,法官在裁判中也不應當認為行為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程度低而免除或減輕行為人的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