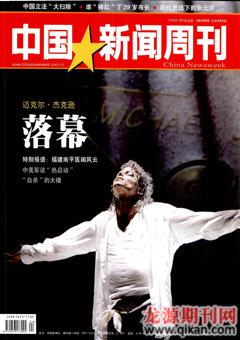難以統一的真善美
邵 建
一個人很難選擇了陽光,卻不要隨之而來的陰影。選擇本身難以完美,正如同任何一種社會亦都難以完美。不完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善于圖畫烏托邦式的完美,我們居然還相信
倫理批評是文學批評多元形態中的一種,這種批評看似美善同體,其實是以善代美,即善的就是美的。作品在它眼里只是一個倫理對象而非審美對象,盡管它號稱文學批評,但卻沒什么文學可言。因而在課堂上,我對這種批評持批評態度。
問題并不到此,它還可以延伸。延伸固然一時溢出了教材,但在我看來也是一種教學必要。接下來的時間,我從倫理批評的美善同體,延伸到我們常說的真善美合一。我以前的一位同事,聲稱他一輩子的目標就是追求真善美,而我們的教育歷來也是如此教育學生。我并非反對真善美,但,我以為,當我們把它捆綁起來作為一種價值追求時,至少也應當知道它們之間的更復雜的情況。我的意思是,真善美的統一,如果有,或許也只能屬于小概率,更多的情況倒是它們之間的不融洽。比如魯迅。他和他的學生許廣平長期同居,如果他們彼此有感情,那是真的,也是美的。但,它對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來說,善嗎。或者,魯迅一輩子和朱安生活在一起,如同胡適和江冬秀一樣,這當然是善的,但,轉從兩性的情感角度看,它美嗎。類似的例子當然還有,何況中國古人早就說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西諺中亦有真理乃丑陋之類的表述,這些都顯示了真善美難以統一。
從現象層面消解真善美的統一不難,但還需要觀念層面上的支撐。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919年在慕尼黑大學作過兩次講演“學術與政治”。在第一次講演中,韋伯涉及的一個問題是“價值多元”。價值多元如果用韋伯的一個比喻來表述,就是“諸神沖突”。在古希臘神話中,奧林匹斯山是眾神居住之地,可是眾神之間,并非和諧,而是沖突不斷。這正象喻著人類生活中的許多觀念——比如真善美——并非像太陽光譜一般有序排列,而是不僅存在著內在的緊張,同時表現為外在的抵觸。我知道,這樣的聲音對學生來說不免陌生,非但如此,聽慣了真善美統一的聲音,再聽韋伯,甚至感到刺耳(此正所謂“信言不美”)。但,為什么不讓學生聽到不同的聲音呢。只聽一種聲音是灌輸,聽到不同的聲音才是教育。
這是我當時為學生抄錄的韋伯的一節文字:“一事物雖然不美,但卻可以是神圣的,還不僅如此,而且神圣就神圣在不美上??一事物雖然不善,但可以是美的,還不僅如此,而且美就美在不善上??一事物雖然不美、不神圣、不善,卻可以是真的,還不僅僅如此,真就真在不美、不神圣、不善上。”馬克斯?韋伯關于“學術與政治”的講演,國內先后出過三種譯本,我都有。我比對過這三種譯本,僅就本節文字而言,旅居德國的王蓉芬女士的翻譯最合我意,而且極有語勢,同時它又直接譯自韋伯的德文,所以我抄的是它。
韋伯的語境是談論價值多元,在觀念的層面上,長期以來,我們更熟悉的不是多元而是一元。真善美的統一就是一種一元化的表述。其實我們可以仔細想想,這三個對象如何“統”又“一”于誰。就像倫理批評的美善同體,最終是以善蔽美;真善美的統一,無論“一”于誰,幾乎無不是對其他二元的遮蔽。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多元的。多元在于,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是相互沖突的,由此導致的各種觀念和價值也是相互沖突的,這應該是我們人類生活注定了的處境。在這一處境中,即使何為真何為善何為美,也未必能尋得一個固定的統一意見,又遑論真善美的統一。
祛魅了的真善美,就不是三位一體的真善美;而是真是真、善是善、美是美。但,人類的天性中有一種把所有的美好都統一起來的愿望,這個愿望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對象間的內在沖突。這一點,東西方幾乎相同。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撩撥了無數人為之喋血。可是,自由與平等,訴求方向不同,無法兼容。只要兌現個人自由,伴隨的結果就無以平等。在一味的平等面前,自由也只好傷身打折。《中庸》聲稱:“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其實,萬物是否相害,只要看看大自然中的生物鏈就行了。道,固可以并行,如儒家有為,道家無為;但,欲其不悖,戛戛乎其難哉。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的世界。多元意味著沖突,也意味著選擇;而且,選擇就是代價。一個人很難選擇了陽光,卻不要隨之而來的陰影。選擇本身難以完美,正如同任何一種社會亦都難以完美。不完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善于圖畫烏托邦式的完美,我們居然還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