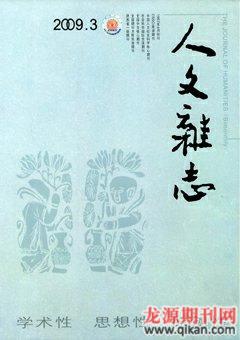梵語味論詩學和西方詩學比較
尹錫南
內容提要 婆羅多、新護、波伽等人的梵語詩學味論與西方詩學相關理論,存在很多可以比較探索的地方,如情由論和艾略特的“客觀對應物”、味論普遍化與康德的非功利論、新護的潛印象原理與榮格的原型理論、波伽的艷情味和弗洛伊德的原欲說,等等。這說明,在中西詩學比較之外,引入梵語詩學與西方詩學比較研究的新維度,將會使中國比較詩學研究的內容更加豐富。
關鍵詞 梵語詩學 西方詩學 比較詩學 味論
〔中圖分類號〕I0-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09)03-0142-05おお
梵語詩學雖然重視語言修辭,但它對世界詩學最大的貢獻卻是極具印度特色的味論。中國古代文論中也存在詩味論,但和具有明顯形式分析特色的印度味論相比,其重意境淡寫實的中國特色更加突出。雖然西方詩學沒有可以與梵語詩學味論完全對等的理論話語體系,但華茲華斯、蘇珊?朗格、T.S.艾略特、榮格、弗洛伊德等人的某些理論主張和味論極具跨越時空的比較價值。本文便對味論詩學和西方詩學相關理論進行一些簡略的比較,以探求東西方詩學心靈的共同點和歧異處。
1、情味、情由與情感、客觀對應物
味論詩學是一種注重情味表達的詩學。有的譯者將味即rasa譯為表示情感的英文詞sentiment。在西方詩學史上,重視情感表達的詩學家大有人在。這就使梵語詩學味論和西方詩學擁有更多的可比性。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它也是情感的創造物。婆羅多在《舞論》中說:“這里,有人問:何以有情?是否感染人者為情?回答是:使人感受到具有語言、形體和真情的藝術作品的意義,這些是情。情是原因和手段,與‘促成、‘熏染、‘造成同義。”①
歡增和新護、宇主等人都接受了婆羅多的味論。新護在《舞論注》中說道:“無論如何,味就是情,一種以品嘗為特征的、完全擺脫障礙的感知對象。”②梵語詩學家對情味的探索為東西方詩學情感論的比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重視詩歌或文學中的情感表達歷來是印度與西方詩學家共同的話題。郎加納斯認為,詩人的思想往往通過直接表達情感的詞語來傳達,而這種情感保證詩的崇高性。如果不傳遞真實情感,詩會顯得浮華可笑。崇高情感的出現是把凡俗的詞語變成金子般的精神的神秘要素。古典文論家對于情感的高度重視對后世詩學家影響甚巨。西方古典詩學重視情感表達的傳統到了浪漫主義詩人那里,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身為浪漫主義詩人的華茲華斯強調詩歌中情感成分的重要,他的話已經成為西方詩學強調情感的經典句子:“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 本文為200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印度文論史”(項目編號08BWW016)和第44批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
①② 黃寶生:《梵語詩學論著匯編》(上冊),昆侖出版社,2008年1月,第52、486頁。
⑤拉曼?塞爾登編:《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劉象愚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73、314頁。)其實,華茲華斯對詩歌情感的強調早在九世紀推崇味論的韻論者歡增那里就有了先聲。歡增認為:“在浩瀚無際的詩歌領域,詩人是唯一的創造主。世界依照他的心愿運轉。如果詩人充滿艷情,這個世界就變得有味。如果詩人缺乏激情,這個世界也就乏味。”黃寶生:《印度古典詩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23頁。)這說明藝術是一種蘊涵情感的精神活動。它的創作欣賞都與情味有關。梵語詩學家的這一論調不僅和華茲華斯的情感說相似,還與劉勰所言“繁采寡情,味之必厭”極為相近。這體現了東西方詩學心靈的契合。
卡西爾和蘇珊?朗格等現代西方批評家公開承認從梵語詩學中獲得了靈感。這些西方詩學家與梵語詩學思想親近,使他們的詩學主張打上了東方烙印。蘇珊?朗格高度贊揚印度對于世界的貢獻:“雖然某些印度評論家貶低甚至反對戲劇藝術而喜愛戲劇中所包含的文學成分,但是,他們對戲劇情感的各個方面的理解,卻遠遠超過其西方的同行。”(注: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劉大基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374頁。)印度味論關于戲劇情感的論述,對于朗格的文藝美學觀的形成起著一種催化的作用。作為朗格美學觀基礎的東西是情感。例如,朗格強調道:“所謂藝術品,說到底也就是情感的表現。”(注:蘇珊?朗格:《藝術問題》,滕守堯譯,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142頁。)朗格對情感問題的關注使她和婆羅多、新護等人有了更好的對話平臺,這將在她的情感符號論中得到更完美的體現和揭示。
T.S.艾略特深受印度文化影響,他的詩歌作品如《荒原》和《四個四重奏》就帶有濃厚的印度宗教文化痕跡。艾略特的詩學話語“客觀對應物”和“非個性化”理論似乎也有隱秘的梵語詩學味論因素。這里先看他的“客觀對應物”理論。艾略特認為:“以藝術的形式表現情感的惟一方法就是尋找一個‘客觀對應物;換言之,一套客體,一種情形,一系列事件都可以作為那種特殊情感的表現方式;這樣,當提供了必須終結于感官體驗的外在事實時,就立即激發了情感。”⑤“客觀對應物”和味論中的核心話語“情由”(vibhāva)所包蘊的思想原理存在驚人的一致之處。婆羅多說過:“何以為情由?回答是:情由的意思是認知。情由、原因、緣由和理由也是同義詞。語言、形體和真情表演依靠它而展現,因此,它是情由。”⑦
黃寶生:《梵語詩學論著匯編》(上冊),昆侖出版社,2008年1月,第52、460頁。)具體地說,所謂“情由”是指戲劇中的有關場景和人物。勝財在《十色》中解釋道:“情由是通過對它的認知而孕育情。它分成所緣情由和引發情由兩類。”⑦所緣情由(ālambana)是基本情由,指劇中人物,引發情由(uddipana)是輔助情由,指劇中的時空背景。兩相對照,艾略特推崇的“表現情感的惟一方法”即“客觀對應物”和婆羅多的“情由”并無二致。在艾略特那里,激發情感的“客觀對應物”是“一套客體,一種情形,一系列事件”;在婆羅多和勝財這里,情由是指展現真情、表達情味的場景人物。“情由導致味的產生的觀點值得與艾略特提出的‘客觀關聯物的觀點進行比較。”K. Krishnamoorthy,Indian Literary Theories: A Reappraisal. Delhi:Meharchand Lachhmandas,1985, p.25)因此,說艾略特的“客觀對應物”就是現代西方版的“情由”也未嘗不可。
通過對東西方情味(情感)論的比較觀察,不難發現,梵語詩學和西方詩學都關注文學感情表達。相形之下,西方的情感論越到后來,其宗教色彩越來越淡薄,而味論到了那耶迦和新護時代則進入神秘宗教階段,拋棄了婆羅多時代樸素的客觀味論,代之以一種玄學色彩濃烈的主觀味論。就情味或情感論而言,西方沒有印度那么細致的條分縷析,沒有區分情感的種類或主味。這體現了梵語詩學的獨特之處。
2、普遍化與非個性化、情感符號、原型論等
對于梵語詩學和西方詩學的情感論來┧擔最有比較價值的在于印度的“普遍化”(sādhārankarana)原理。在那耶迦這里,味論普遍化原理已經初具雛形,并且,他開始擺脫婆羅多客觀樸實的戲劇味論,進入到主觀神秘的詩學味論領域里。這是梵語詩學合乎邏輯的發展。
新護對那耶迦的味論提出了批評,但基本接受了他的普遍化原理。在新護看來,味就是情,一種以品嘗為特征的、完全擺脫障礙的感知對象。新護使用了佛教的“遮詮法”(apoha vāda)闡釋味體驗的本質,其實就是對味的普遍化原理的論述進行鋪墊。這涉及到一個關鍵詞即“潛印象”(vāsanā,samskāra)。以戲劇欣賞為例:“由于觀眾自身具有愛的潛印象,觀眾的自我也介入這種愛。這樣,觀眾不是以與己無關的態度感知這種愛……因此,艷情味是經過普遍化而成為持續或單一的知覺對象的常情愛。常情的普遍化依靠情由、情態和不定情。”④黃寶生:《梵語詩學論著匯編》(上冊),昆侖出版社,2008年1月,第493、485頁。)新護理解的味的品嘗,既不完全執著于自我或客觀對象,也不是出于┦導市瑾要。在他看來,觀眾或讀者沉迷于自己的常情潛印象,而潛印象又是通過情由等的普遍化而被喚醒的。這便是新護味論普遍化原理的核心。
新護的普遍化原理最具東西詩學比較價值。從審美接受的角度看,味論普遍化原理在德國古典美學家康德那里也能發現相似的思想痕跡。康德認為:“審美判斷既然在主體意識中不涉及任何利害計較,就必然要求對一切人都有效。這種普遍性并不靠對象,這就是說,審美判斷所要求的普遍性是主觀的。”③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362、365頁。)在康德這里,普遍可傳達的東西不能是認識對象,而只能是審美判斷中的心境。這種審美心境是審美活動的主要內容,它之所以可以普遍傳達,是根據人類具有“共同感覺力”(幾近于新護所謂“潛印象”)的假定,即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康德給美下了一個新護式的定義:“美是不涉及概念而普遍地使人愉快的。”③不過,康德更多地站在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上分析審美普遍性原理,新護則時刻沒有忘記味的普遍化與“梵”的體驗的宗教關系。
新護普遍化理論與艾略特“非個性化”理論相似。新護說過:“讀者(或觀眾)在理解了這些詩的文字意義之后,立即產生另一種超越詩句特定時限的感知。這是一種內心的、直接的感知……因此,它具有普遍性,不是有限的,而是廣大的。”
④這是指審美體驗即品嘗詩味的一種特殊心理程序,它涉及詩歌情感的普遍化問題,即艾略特所謂“逃避情感”的問題。艾略特提出了“非個性化”理論:“詩是眾多體驗的集中表現……詩不是情感的放縱,而是逃避情感;詩不是個性的表述,而是逃避個性。”拉曼?塞爾登編:《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劉象愚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13頁。)這是對詩人情感“非個性化”亦即詩人情味普遍化理論的最好揭示。詩人“逃避情感”便是創造一種普遍的、抽象的“人類情感”,在這一情感“非個性化”進程中,詩歌的美得以生成。這和新護的思想幾無二致。按照新護的觀點,味是普遍化的知覺或情感。詩人描寫的是特殊的人物和故事,但他傳達的是普遍化的知覺。新護的味論揭示了文學創作中特殊和普遍的辯證關系,也闡發了藝術欣賞的心理規律。新護的普遍化原理既重視詩人的創造性活動,也關注觀眾和讀者的審美接受心理,顯示出一種科學而合理的思維邏輯,而艾略特似乎給人一種印象,他只注重詩人創造性的一面,忽略了讀者一維。
蘇珊?朗格認為:“藝術是人類情感的符號形式的創造。”(注: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劉大基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51頁。)所有的藝術只有在創造形式符號來表現情感這一點上才有共性。換句話說,只有通過普遍意義上的形式結構來表現感情,藝術才能成其為藝術。朗格的情感符號與味論普遍化思想有著十分相近的地方。新護說,讀者在閱讀理解詩文后,會產生一種超越特定時限的感知。這種味體驗“具有普遍性,不是有限的,而是廣大的”④黃寶生:《梵語詩學論著匯編》(上冊),昆侖出版社,2008年1月,第485、485頁。)。由此看來,蘇珊?朗格和新護之間跨越時空和文明的詩學對話是成功的。
在論述普遍化原理時,新護涉及到一個關鍵詞“潛印象”。新護味論的獨特貢獻在于:靈魂里的情感是以“潛印象”的形式而存在,這種潛印象用榮格的話說是“原型”(arche-type) 。印度學者指出:“探索西方的‘潛印象概念,我們還得尋求榮格心理學的幫助。正如印度美學中的潛印象概念來自瑜珈心理學,同樣,榮格的情結(complex)同印度哲學中的潛印象概念存在可比性。”(注:Padma Sudhi, Aesthetic Theories of India, Vol. 3, Delhi: Intellectual Publishing House, 1993, p.6)這從一個側面點明榮格思想與印度思想的親和力。
卡爾?榮格對西方現代文藝理論產生重要影響的有“情結”說、集體無意識學說和原型理論等。集體無意識學說是榮格對弗洛伊德無意識理論的發展。榮格說:“集體無意識不能被認為是一種自在的實體;它僅僅是一種潛能,這種潛能以特殊形式的記憶表象,從原始時代一直傳遞給我們,或者以大腦的解剖學上的結構遺傳給我們。沒有天賦的觀念,但是卻有觀念的天賦可能性。”(注:陸揚主編:《二十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第二卷、回歸存在之源),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1頁。)榮格的“觀念的天賦”和“特殊形式的記憶表象”和新護帶著瑜珈哲學觀念提出的“潛印象”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新護說:“所有觀眾的心理意識中都有各種沒有起始的潛印象。正是這種潛印象的一致性,形成感知的一致性。”
④新護認為,藝術感知是由演員等等戲劇手段撫育的。通過這些戲劇手段,真實存在的和詩歌提供的時空等等有限原因互相抵消,完全消失,為感情的普遍化鋪平道路。而觀眾感知的一致性,導致味的充分發育。因為所有觀眾的心理意識中都有各種潛印象。這種潛印象與榮格的原型即原始意象一樣,同樣來源于人類意識的最深處。榮格對原始意象即原型的推崇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這與味論派帶著神秘的宗教哲學體驗討論心理潛印象的姿態相近。
新護的潛印象和榮格的原型論存在一些不盡相同的地方。例如,新護的潛印象更多地強調情味的品嘗。因為,新護畢竟是味論者,探索觀眾和讀者心理中的潛印象是在味論的前提下進行的。新護首先是從觀眾或讀者品嘗味的這一角度入手,闡發自己的潛印象理論,而榮格卻無法擺脫弗洛伊德關注藝術家主體創造性的影響,這是他和新護的區別所在。
3、波伽的艷情味與弗洛伊德的原欲
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藝術通過性或原欲(libido,又譯“里比多”)來表達。性是靈魂無盡止的裸露展示,美也是性愉悅的一種手段。“原欲”在弗洛伊德那里成了人的科學和藝術活動甚至宗教行為的終極原因。藝術便是原欲的補償。印度美學家認為,在印度文化傳統中,得到滿足的愛欲(kāma)成為美。但當這一愛欲得不到滿足時,它便自我擺脫情感的羈絆,轉而升華為一種藝術哲學。梵語詩學家波伽認為廣義的艷情味(它有別于婆羅多的狹義艷情味)是唯一重要的味。波伽與弗洛伊德的美學觀存在思想交匯。
波伽味論觀受到歡增和新護的影響。不過,他的味論仍屬于別開生面的創新學說。波伽所謂的“自尊、自愛或艷情”實際上指原始的味。“自愛”(ahankāra)是自我意識,“自尊”(abhimāna)是自覺,而這里的“艷情”(srngāra)不是婆羅多式的艷情味,而是廣義的味。按照波伽的觀點,“自愛、自尊或艷情”是最高意義的味。它原本潛伏在觀眾或讀者心中。藝術作品中的情由、情態和不定情觸動自愛,激起自愛中的情。波伽認為通常所說的各種味就是達到高潮的各種情。波伽還認為,味是超越對常情的沉思而進入心中的品嘗。所謂心中的品嘗就是達到高潮的各種情轉變成喜愛,返回自愛、自尊或艷情。因此,波伽實際上認為自愛、自尊或艷情是唯一的味。“對波伽而言,味只有一個,那就是艷情或自愛或自尊。”(注:V. Raghavan, The Number of Rasas, Madras: The Adyar Library and Research Centre, 1940, p.131)波伽對味的獨特思考受到奧義書哲學思辨的影響。奧義書哲學將“自我”視為最高存在。波伽也是這樣,將“自愛艷情”即自我意識視為味的起源或歸宿。
梵語詩學研究專家拉格萬認為:“我們可以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中發現與波伽理論驚人相似的地方。”
⑤⑥⑦
V. Raghavan, Bhojas Srngara Prakasa, Madras: Punarvasu, 1963, p. 503)首先,弗洛伊德和波伽都將文藝創作與心理分析聯系起來加以考慮。在波伽那里,與現代心理學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微妙關系的“味”成為文學創作的必要前提。例如,他說:“詩達到可愛的境地,在于有味相伴。味被稱作自尊、自愛或艷情。它在人的內在自我中,產生于前生的經驗積累。它是自我各種性質的唯一根源。如果詩人充滿艷情,詩中的世界便有味;如果詩人缺少艷情,詩中的世界就乏味。”(注:黃寶生:《印度古典詩學》,第326頁。)這里,“自尊、自愛或艷情”、特別是其中的艷情味與文學創作成敗關系莫大。而在弗洛伊德那里,原欲即里比多是文藝創作的原動力,文藝的升華作用與此密切相關。弗洛伊德說:“性力特別把文化活動提供給那些杰出的精力旺盛的人……原來的性的目標置換成了另一種不再是性的但在心理上仍舊與性有聯系的目標,這種置換能力稱為升華的能力。”(注: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5頁。)波伽和弗洛伊德一樣,都將文學創作和心理動因結合起來考慮,反映了他們試圖通過語言和宗教哲學以外的維度探索文學規律的共同立場。其次,在波伽廣義的艷情味論和弗洛伊德的原欲論中,都有一個最基本的理論出發點。這一理論支點是二人得以建立自己美學觀的重要元素。在波伽那里,“自愛”即艷情味是他獨特味論的重要理論支點。在弗洛伊德那里,本我或里比多是其原欲論乃至整個精神分析大廈的基座。拉格萬認為:“波伽的自愛艷情可以稱為精神分析學中的本我即伊德或里比多。里比多分為本我里比多(ego-libido)和客體里比多(object-libido)……本我里比多就是波伽的靈魂自愉的自愛。當它向外部客觀世界流溢時,就會成為各種形式的自尊。在這種自尊里,同一種本我里比多就是客體里比多。里比多就是包羅各種形式的愛的一般自愛(general ahankāra)。”⑤
拉格萬認為,弗洛伊德與波伽理論之間有相通之處,但必須記住:“波伽的理論更為透徹,更富哲理色彩,而很少糾纏性欲問題。”⑥
弗洛伊德的里比多指涉的是與客體相聯系的性本能,它包括性愛、自愛、對父母朋友的愛及對具體或抽象的觀念的愛。波伽則將各種情(bhāva)視為一種“喜愛”(preman),所有的情和包容各種情的喜愛都是自愛的一種體現。“因此,波伽自愛中的里比多要比弗洛伊德的里比多蘊涵的東西豐富得多。”⑦
盡管波伽和弗洛伊德存在精神契合的地方,但是,他們之間由于時代地域和文化土壤的差異,仍然存在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波伽往往將自愛思想與宗教四目標(法利欲解脫)聯系起來加以考慮。這就不難理解,他為什么要論及法艷情、利艷情、欲艷情和解脫艷情。而弗洛伊德的里比多則在很多時候與心理分析有關,有時純粹只與生理性欲有關。其次,波伽的“自愛味”即艷情味賦予讀者以福祉,這是升華。自愛味的喚起使人們成為善于品味的知音(rasika)。這就是說,波伽的艷情味除了探索詩人創作之謎外,還重視讀者或觀眾的審美接受一維,而弗洛伊德則多探討藝術家在里比多即原欲推動下怎么創造而升華自己的問題。另外,波伽的弗洛伊德的著述都存在形式分析的特點,但波伽似乎更勝一籌。オ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楊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