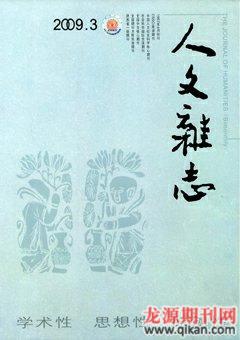《金瓶梅》與《唐吉訶德》“戲擬”敘事之比較
戴承元
內容提要 以諷刺世相來揭示生存的荒謬和人性危機的《金瓶梅》與《唐吉訶德》,都采取了傳統小說既成的“戲擬”敘事謀略。但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境遇及美學價值指歸,兩部作品又各有其諷刺的具體內涵。因這一緣故,讀者從兩部文本同一性的“戲擬”敘事方式中獲得的審美體驗是完全不同的。
關鍵詞 《金瓶梅》 《唐吉訶德》 戲擬 諷刺視角 悲劇的崇高
〔中圖分類號〕I0-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09)03-0147-03おおお
16—17世紀之交的世界文學史上,有兩部經典永遠不會被人們遺忘。一部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創作的《唐吉訶德》,另一部是署名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將兩部大致創作于同一歷史時段的經典并置,通過細讀文本,我們可以在兩部作品中發現二者雖然旨趣有異,但在“戲擬”敘事方式及喜劇效果上卻具有一定的同一性,同時這一同一性也彰顯出了中西文化中喜劇審美各自不同的價值歸屬。
一、“戲擬”的運用
《金瓶梅》頭十回借用了《水滸傳》潘金蓮偷奸鳩夫的情節,但借用中有轉化和戲擬。在詞話本中,對潘金蓮身世進行了重構和鋪陳,她本是“大戶人家”的使女,在王招宣家學會了“描鸞刺繡,品竹彈絲,又會一手琵琶”,轉賣給張大戶之后,以其淫蕩害得“大戶得陰寒病癥,嗚呼哀哉死了”。這一重構豐富了這位女主角的文化儲備和淫邪尤物色彩,也開始改變了寫潘金蓮是為了寫武松的描寫角度。 “最后讓武松在獅子橋下酒樓打死的不是西門慶,而是‘替身李外傳,則實在是讓這位打虎英雄,表演了一場誤把風車當魔鬼來大戰一場的滑稽劇了。”“第一奇書本《金瓶梅》首回,把‘景陽崗武松打虎改為‘西門慶熱結十兄弟,一方面固然是照應全書以西門慶為敘事中心,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對《三國演義》以桃園結義開篇,或是對《水滸傳》以水泊聚義為扭結的戲擬。”然而在這跪拜結盟前,已有應伯爵諸人在集資酬神的銀兩分擔和成色上作了手腳,結盟之后即有西門慶對花子虛的占妻謀財,有應伯爵在西門慶府繁華時的趨附揩油和落敗后的落井下石,有西門慶死后他的結盟“兄弟”們委托一位秀才所寫的諷刺性祭文,最后還有西門大娘子在兵荒馬亂中所作的云理守殺死她的兒子、并霸占她的惡夢。“這番戲擬,表明戲擬者對桃園結義、梁山泊聚義曾經有過的理想化體現,而玉皇廟拜疏又冠冕堂皇地重復的‘生雖異日,死冀同時、‘安樂與共、顛沛相扶的信念,在市井人情的沖擊下已經動搖破滅。這場‘熱結,實際上包含著以卑劣嘲笑崇高的悖謬。”就戲擬謀略的具體操作而言,《金瓶梅》“戲擬了早期章回小說的豪俠道義,戲擬了話本小說的兒女真情,戲擬了傳奇小說的文酒風流,從而還原了市井社會中的銅臭熏天、人欲橫流的平凡世界,建構了世情書的敘事形態”。
《唐吉訶德》中對“戲擬”手法的運用更是明顯。作者沿襲曾經風靡整個歐洲的騎士小說的一般框架,讓一個冒牌的騎士沿用中世紀騎士小說中的常規模式去行俠。結果,一種習慣性的閱讀期待與唐吉訶德的實際表現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反差,進而制造出了無數可笑的戲劇場面。
在廣為流行的中世紀的騎士小說中,最吸引人的“敘述”,除了騎士的俠義和壯舉外,恐怕就是騎士和他的女“恩主”之間的動人愛情了。按照一般的敘述模式,女“恩主”都是氣質高雅,相貌迷人的。唐吉訶德作為引導敘述進程的一位“騎士”,幻覺中的騎士身份使他本能地渴望能有一次浪漫的愛情遭遇。而敘述者也按照常規給他安排了這樣的一次遭遇。但是,唐吉訶德的女“恩主”——“托博索的杜爾內西婭”,這個有著“悅耳、美妙、有意義”的名字的人,卻是一個還長著胸毛的又丑又蠢的鄉下姑娘。可即便如此,唐吉訶德還是把每一次冒險都當成是為她爭取榮光,仍然在每一次“戰斗”前都向她祈求“恩澤與保佑”。
根據中世紀的慣例,要成為騎士,就得隆重地舉行受封儀式。唐吉訶德當然也有著這樣一種莊嚴的期待,他渴望體驗受封為騎士那一刻的神圣感。可是,唐吉訶德、主持者及作為旁觀者的市井妓女,共同為這一受封儀式涂上了一層滑稽和荒唐的油彩。騎士的尊嚴和榮譽,騎士道精神的神圣,在這一本應莊嚴的時刻卻遭到了殘酷的嘲弄。
還有,按照騎士小說的一般套路,騎士在經歷了一番冒險歷程之后,最終會得到愛情和榮譽。但是,依據常規的騎士行俠方式闖蕩了一番的唐吉訶德,不僅沒有得到他幻想中本應屬于自己的榮光,相反,使他得到了被世俗所認定的“瘋癲者”的身份。
二、諷刺視角比較
《金瓶梅》和《唐吉訶德》都在敘述中采用了“戲擬”的手法,而且,正是通過這一手法,使得兩部小說的敘述始終都伴隨著一種喜劇效應。但是,在一種熱辣、滑稽的喜劇氛圍的背后,卻始終貫穿著中西喜劇不同的美學價值指歸。
《金瓶梅》采取的是一種真實的諷刺視角。這種諷刺來自于作者和不同時代的讀者。當歷代的讀者在為《金瓶梅》中描畫的為欲而生的一群人形動物的丑陋和瘋狂感到驚駭的時候,我們似乎能夠在西門慶死時的掙扎和孝哥兒實為西門慶來世的贖罪之身的敘述中,聽見作者的一身帶有冷靜嘲弄的哀嘆:“看,這就是縱欲的下場!”西門慶在敘述層面上的恐怖死亡和斷子絕孫的結局,構成了小說中最具諷刺和警誡意味的一個隱喻性符號。西門慶的結局,在小說的作者看來,無疑要釋放出這樣的信息:縱欲,其實就是生命的一種死亡形態。由此可見,《金瓶梅》的核心形象西門慶,其實從反面承擔起了反縱欲的說教功能。作為這種說教模式總導演的作者,他對文本中的西門慶,以及以他為中心的那些的游蕩于金錢和本能欲望中的男女們,所進行的諷刺及嘲笑,是真實而直接的。在作者看來,個體一旦唯身色貨利是圖而無文化規范可言,完全依靠肉體的感官沖動而存在,則其個體生命將成為一具純粹的形下之物。目睹由這種眾神狂歡態勢的縱欲之風所導致的已病入膏肓的文化困境和現實困境,以及以縱欲為生之目的的普遍生存病態,試圖在這末世光景中開啟出一種新的文化價值向度的焦慮,不由得變成了絕望和無奈之余的冷眼旁觀。
在《唐吉訶德》中,塞萬提斯的諷刺視角是虛擬的,或者我們可以將其稱為諷刺的諷刺。也就是說,在《唐吉訶德》中,作者真正諷刺的并非唐吉訶德,而是唐吉訶德所處的那個現實中的人。“當作品的現實中的人物嘲笑唐吉訶德‘恢復騎士道的理想時,他們是有了某種優越感的,因為似乎只有他們是頭腦清醒和識時務的。其實,從作品深層內涵和作者此時的視角來說,他們自己成了嘲笑和抨擊的對象。因為在唐吉訶德的心目中,騎士道盛世是一種理想社會,那里沒有邪惡,沒有以強凌弱,而只有公道、正義和自由,所以,他要為之赴湯蹈火而在所不辭。”了解唐吉訶德所處時代文化背景的人都清楚,這只是他的幻想。而唐吉訶德一直生活在這種幻想之中,并以實現這種“幻想”作為自己的信仰。正是由于唐吉訶德對這種“幻想”的堅守和執著,使得他自踏上行俠歷程的第一步開始,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與現實的持續沖突之中。但是,在由一系列的沖突所制造出的滑稽的喜劇場景的背后,一切有思想和良知、有著“善”的追求的讀者,都能體味到一種正在被殘酷的嘲弄甚至蹂躪的悲劇崇高,或者能感受到塞萬提斯正在以悲憫和哀憐的眼光注視著 “可笑”的唐吉訶德。因為,當我們撇開唐吉訶德的理想社會實現的可能性,而從其合理性、正義性看問題時,他就不再是一個結合了呆癡與瘋癲的純粹的喜劇形象,而成了一個獻身信仰的斗士,一個充斥著各色人形爬蟲的世道上的真正的人、真正的英雄。
在實現“騎士”夢想的歷程中,無論是被迫還是自愿,堂吉訶德作為最終的失敗者的身份是確定的。毫問疑問,堂吉訶德的失敗,是理想對現實的失敗,美善對邪惡的失敗。從審美層面上講,唐吉訶德無論是堅持還是放棄那個“瘋癲者”的身份,都具有一種強烈的悲劇色彩。唐吉訶德的悲劇,反映出了在意識深處對上帝有著天生的親近感的塞萬提斯,在重構人文主義時的痛苦和兩難。
結 語
西門慶的丑陋與恐怖的死亡,是晚明亂世的一聲喪鐘,是驚現于仍在人欲之海中放縱自我的世俗男女頭頂的一道暗示懲罰的閃電。西門慶的死亡和他事實上的斷子絕孫,在充分體現了作者對縱欲世風從根本上持一種嚴正的批判立場的同時,也相對充分地實現了一般讀者道德向度的閱讀期待。這種閱讀體驗,帶有一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古訓終于應驗的愉悅。
但在《唐吉訶德》中,我們發現,唐吉訶德的死亡卻是隱喻著一個關于人性的圣潔童話的破滅。當滑稽的油彩從他的行俠歷程中剝落之后,我們再以理性和良知重新審視唐吉訶德試圖恢復“騎士道盛世”的理想,我們體會到則是一種悲劇的崇高。正是這種悲劇的崇高,使得唐吉訶德成了我們文化理想和精神記憶中一尊不朽的雕塑。
參考文獻
1、(美國)韓南:《<金瓶梅>探源》,《<金瓶梅>西方論文集》,徐朔方編校,沈亨壽等翻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3、梅向東:《正反悖謬風月鏡——<紅樓夢>對一種文化困境的意識與隱喻》,《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7年第2期。
4、尹恭弘:《<金瓶梅>與晚明文化——<金瓶梅>作為笑書的文化考察》,華文出版社,1997年第8期。
5、蔣承勇:《西方文學“人”的母體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0頁。オ
作者單位:安康學院中文系
責任編輯:楊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