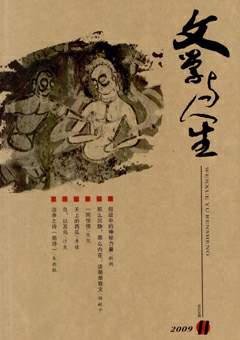假設中的神秘力量(外一篇)
朝 潮
一
睡眠是不穿外套的,包括靈魂;其余的大部分時間被一身外套妨礙著,靈魂也是。萬物之圣高高在上,澤被生靈,他讓我在睡眠中失去了思想的戒備,借此灌輸給我一些神秘的印象。神秘是一類鋪張的東西,像傳說,像夢想之人的隱約聲容,像一九零五年巴黎秋季沙龍上展出的“野獸主義”。狐疑和神秘之事,大多依附于假設,假設是虛的立場,可塑性大,影響力也就此無窮生發。
如果我在乎某個神秘的對象(物質或非物質的),這個對象不太可能在我的反復琢磨中越來越清晰,只要其不現出真相,便是更加的神秘,然后變成一個個懸案;在神秘的日益教唆之下,迷信之間,我把自己假設成了無數個福爾摩斯,卻永遠破不了案。在這類對象面前,我的外套根本抵御不住其無形的力量。
夢,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對象。周公和弗洛伊德在這個對象上已經鉆研過了,在我看來,它像沒有鉆研過一樣。這是萬物之圣羞辱人的方式之一。
夢的無序,以及它毫無意識保障的虛幻狀態,有點接近人類起源時的猥瑣和粗野的局面──我是說局面。夢里,到處是假設,是一往無前的力量,誰也不認識誰,夢里認識的人也有著多重陌生和神秘的成分,包括最親近的人。我做夢,大多是處于最危險、最緊急、最墮落時,夢醒了,一種神秘的力量把我解救出來。為什么總是在那個緊要時刻醒來,為什么?那些在夢中死去的人們,大概是因為神靈的不在場,失去了解救的機會,也存在真正被解救的是他們的可能性。誰知道呢?偉大的“夢想家”納撒尼爾·霍桑就是在睡眠中安詳去世的,我親愛的外婆也以同樣的方式離去。大概人的一生原本就是用夢幻的材料編織而成,睡眠是開始,也是結束,這是技術上的宿命。我懷疑,在生命這張眠床上自己有沒有站起來過,或者我是否具有站起來的力量。相對于信仰來說,這張眠床也許只是一個道具,它讓我一次次流下思考和驚悚的汗水。
夢的方式,必然會融入個人現實主義的聲容,也與幻想中的樣子融會貫通,這種方式和“野獸主義”相仿,都屬于泛表現主義的范疇。在我的印象里,野獸派最為狂放不羈的弗拉芒克的畫作,其假設性便可以用來參照夢的方向。《夏都的住宅》和《布日瓦爾的山丘》都是夢,色彩的夢,它們可以用來填充和寄存多種瘋狂的表現力和想象。《夏托納弗村》是一個村莊的夜夢,黑白主色表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聲音:靜謐和呼嘯、笨拙和輕靈。那些從顏料管直接涂上去的色彩,形式上像隨意的夢一樣的自由,張狂,神秘。它們在印象派的基礎上又橫向地假設了一大步。批評家路易·沃塞爾說它們是“野獸之籠”,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發明,這個概念本身就具有夢幻色彩。弗拉芒克的色彩素養,得到過凡·高的間接提示。他沒有見過凡·高本人,但他在其畫作面前曾激動得大聲喊叫:“我愛凡·高,勝過愛我的父親!”這種激發出來的力量,來自于凡·高作品中的假設。在那個神秘的繪畫的夢鄉,是一位現實中的父親無法抵達的地方,誰也看不清它的廬山真面目。
夢的面目是什么樣的?沒人說得清,但它作用于人的一生。在我無法區別睡夢與夢想的日子里,常常覺得自己無比強大。沒有這種夢想和強大感,我不知一生該如何鋪伸。這是人類的共同點,個體的強大感(或者說夢想的力量)是人與其他物種區別開來的最重要因素。人類的文明進程便是從夢想開始的,無論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假想了嫦娥奔月的神奇傳說,現在,創造這個傳說的后人正在實施真實的奔月步驟。其他物種好像沒有夢想和假設,或者說它們沒有這項功能,實際情況卻很讓我這個人類困惑至極,它們傳奇般的生存歷史和感官組織的神秘力量,都讓我驚嘆。我只粗糙地知道,許多動物是有睡夢的,或許這正是它們生命力的源頭。
五億年前,混沌初開,第一批動物從海水里上了岸,這當中包括蝎子和蜘蛛,它們是地球生命的變革者,是先驅。這個過程比人類從假設到真實地登上月球,肯定要漫長得多。第一批動物上岸一億多年后,其中的部分動物長出了翅膀,以小型昆蟲為主,它們是冷血動物,熱愛光照,在光的作用下演化出雙翅。又過了一億年左右,飛行動物中出現了翼龍,它們憑借翼膜纖維結構在空中飛了另外的一億多年。大約在六千五百萬年前,翼龍和陸地的恐龍一起滅絕了,沒人知道這是如何發生的,期間發生過什么,人們只能通過億萬年前的化石作出一些假設,化石上的構圖也因此被打上神秘力量的印記。考古學家假設著說,翼龍在空中的滑行樣子,很像人類的滑翔機。這個說法應該倒過來才對,人類現今所擁有的飛行器具都是從動物身上模仿的基礎上假設出來的。地球上真正的羽毛的出現,應該是在翼龍之后,隨著空中和陸地的集權的消亡,才有了物種的相對自由的繁榮。
現在,人在地球上集權在握。人的霸道,客觀形式很像恐龍,其他物種不可能自由繁榮。當人穿上外套之后,也就永遠失去了生長羽毛的可能性。幸好人擁有別的物種不具備的精神上的羽毛:夢想和假設。
夢想的進程,肯定比動物長出羽毛的進程要快。這是我個人的猜想。一九零五年,法國冒出精神夢想的“野獸主義”之時,俄國的民眾還在集權之下為生存和自由而暴動,中國在這一年則剛剛廢除了集權之下的科舉制度。同一年的事情,如三個臺階,不同的進程。
二
有自然的力量,人才唯物;有神秘的力量,人又唯心。在人類依存的哲學理論方面,唯心和唯物是不應該對立起來的,不管誰是核心,都無法避開看不見的力量;就像有人說男人是第一性和有人說女人是第一性差不多,關鍵是思想權力的傾向。統治階級經常被左派人士(或者僅僅讀過幾本書、關心過幾天政治局勢的人)拿來比畫,拿來罵,這比較冤,統治階級的上頭還有思想集團在起作用,那就是個體的人組織起來的夢想的力量。集體的夢想力量,才是無敵。上帝對于巴比倫塔的恐慌,就是一個杰出的例子。同樣,拯救一個民族的往往起始是集體的夢想力量。
藝術家的創作,很大程度上是一項夢想的“唯心”的勞動,是把心里的向往和神秘用不同方式解釋出來的過程,也可以說是尋找和發現的過程。這項工作是做夢,不太可能直接為經濟建設添磚加瓦。“野獸主義”代表人亨利·馬蒂斯的畫作,就像對人的精神上的多種解釋和關懷,他放棄了傳統的透視法則,大膽假設,心靈盡量擺脫那一身外套的妨礙。
說實話,人身上的外套太厚了,厚得讓人看不清真相。有位剛師范畢業的朋友問我:什么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結果我說了一大堆,也不知說清楚了沒有。現在我覺得可以用很簡單的一個說法來解釋:人的外套是形而下,外套帶來的影響是形而上。如果這個答案讓他印象深一點的話,是因為我使用了簡單的假設。
所有的力量,不同程度存在著神秘性。機械工業的力的啟蒙,是阿基米德的杠桿原理。阿基米德從假設的立場出發,跟國王艾希羅說,他有力量可以撬起地球;之后他又在跟羅馬人的戰爭中發明了一種特大的弩弓(發石機)。現在人人都知道這個力的原理了,它有嚴密的邏輯依據,不過,就算真有一根若干光年長的杠桿,親愛的阿基米德先生也不可能去撬起地球。那只是一種假設。
萬物從假設中開始,到假設中結束。假設,是人類創造力的不竭源泉。在藝術創作對象上,不要片面地提及體力和機械時代的勞作性生活,也不要指責創作者有沒有“生活”,那樣很沒有藝術的品和德,起碼是歧視。不管是打工的、撿垃圾的,還是隱居的、長年癱瘓在床的,只要在呼吸、在思想,就是在生活。生活方式也是由假設構造出來的一部分,先有假設,然后再存在。應該說,假設也是生產力。沒有假設的話,人是不可能成為流水作業車間里的一件產品的,最多就是一堆廢銅爛鐵──作為一個獨立的人,如果在別人的假設好的一生中生活著,跟物質產品有什么區別呢。大概豬圈里的主人極少假設,它們只剩下吃喝拉撒的嚴重感官退化的生活方式。人本身也在退化,片面重視周圍環境和質量。人的一生,最重視的東西是表面的東西,就是自己的外套(甚至別人的外套),也是束縛自己的東西,以及失去想象羽毛的原始阻力。
不同的物質產品由人來假設和設計,人又是誰在設計呢?這是另一種假設,永遠停留在唯像理論的一個假設,同時具體影響人類的最強大的力量。人類的住地,因為各種力的相互作用而存在,人(包括人周圍的萬物)本身顯得很無助。各種力的作用,都是人類假設中的神秘力量。
人類對于假設的癖好,會成為精神負擔,也是現實的敵人;如果某人已經是現實的敵人了,就無所謂了,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夢想除外,人被召喚的機會其實還有很多,這些機會包括孤獨、苦難、危機,等等,它們是世上最有效的創造性精神激素,是萬物之圣發出的邀請書。我懷疑,夢想是人類精神上的挽救力量,也是靈魂的表現方式之一;對夢想的無視,緣于對物質的依賴,是一種精神上的渙散──這是我的另一個懷疑。世上值得懷疑的東西太多,我懷疑不過來,尤其是那類具有號召性的集體力量。我不太可能被別人號召,但沒有辦法抵抗來自自身的號召,包括每天的所思所感。
三
許多人我都想記下來,不記下他們,我擔心以后再也叫不出他們的名字,記不清他們的模樣。這些人很亮,似片段或碎星,在某一時間內閃爍著劃過我的面前,又悄然消遁。那種印象像黑夜里驟起驟落的閃電,隨即晦暗四合,心野里依然混沌一片。記下那種印象,對于我的反應來說是一件不值得鼓舞的事;大多數時候我記不下他們的神秘,像夢。一團無序的想象的亂麻,無論如何穿不過時間的針孔。
山,海,天,地,通常以個體的量數來概念它們,以便將它們的寬廣籠統起來。我看到的卻是群體,是龐大。他們以具體的影像落實在那里,用來觀望他們的那雙目光,長時間傾向于教條,傾向于抽象。一個叫做“我”的個體,掙扎在雜亂無序的群體里,顯然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可能因為這個原因,我小時候一直懷疑神的力量的存在,有神的保佑,群體也就不顯得那么可怕了──也許那不叫懷疑,是本能。宗教信仰是靈魂的假設,是意識超越肉體而延續的假設。那種力量的無窮性,誰都知道。
我在鏡子里拜訪自己這具身體時,感覺上缺乏可以操控的力量,似乎也是一個抽象的對象,鏡子里的人只是一個名字的替代品,他沒有更多的呈示,連形容也相對陌生。對于自己的形容,我比別人要陌生,起碼比我敬崇的、喜愛的、牽掛的、熟悉的那些人要陌生。我不清楚自己眼里的我,和別人眼中的我有多少區別——或者我們眼里看到的事物有多少區別。研究量子物理的人,大概是對于碳結構組織(人類)最困惑的人,他們從不認為自己觀察到的世界是真實的。除了假設中的萬物之圣,不知道誰是最終的觀察者,我只相信我處在一個有著無窮可能性的時空里。我所有的認知是所在文化環境帶來的印象,并未經過個體思想的檢驗,它們對于我來說,是一類暫時的假定的存在。
照鏡子也是假設。在鏡子前長時間盯著自己的瞳仁,感覺極為恐怖,像置臨兩處神秘的望不到頭的深淵,我不知道到底是誰盯著誰在看,使用的是鏡子外還是鏡子內的那雙眼睛——這個問題我請教過一位老師。老師說,媽的,這還真是個問題。兩千多年以前的人在河水和盛滿水的陶器里映照自己時,有很多的假設和想象,否則美少年納瑟斯也不至于為水里那個人憔悴而死。就算現在面對鏡子,如我,也容易傻乎乎地把自己假設出去,用其他形式(身份)來觀測。這類方式更恐怖,因為缺少一種神秘的力量的在場。那個叫文森特·凡·高的畫家,就常常在鏡子前觀察自己,然后把自己假設成商人、中產階級、平民等等,畫下來。長時間地假設,長時間地忘記自己,人很有可能會瘋掉。博爾赫斯在寫小說時,人稱的假設上就比別人多了一些可能,也多了一些神秘的力量;胡安·魯爾福的小說也重視假設,帶來的也是人事發展的神秘;曹雪芹拿夢作假設;蒲松齡以鬼神作寄托……這類名單我可以不辭辛勞地列出一長串。無論如何,這是寫小說的魅力之處,無窮的假設,而不至于瘋掉。他們把主觀的想象成分(假設)在某個特定的范圍內普及了,分散了。寫不出“好看”的“生活”化的故事的作家,只好拿自己作假設,比如卡夫卡、霍桑,這類方式相對于過日子來說,比較危險。
鏡子的出現,消滅了作為主體的人自身形象的一些神秘,也帶動了更多身體內部的假設。它因此比夢更抽象。在中國,鏡子是春秋戰國時期開始鑄造的,就是在青銅器上打磨;照西漢《淮南子》上面所說,是用“玄錫”作反光涂料,再用細毛呢摩擦的結果。那時的“玄錫”,大概就是指水銀和錫粉的混合劑,這種技術用了很久。秦漢以后,用鏡子陪葬比較普遍,人們認為鏡子可以容納他們的靈魂。秦始皇的皇宮里曾有一面銅制方鏡,寬四尺,高五尺九,據說可照見人的五臟六腑,能見疾病和人心善惡;秦始皇常用它來照宮里的人,見有膽戰心動之人,就要殺頭,它比曹雪芹先生杜撰的“風月寶鑒”要可怕得多。我猜想這是秦王的野蠻假設,他利用了秦國獨一無二的“珍寶”,并以神的名義來定義它,從而假設出神秘的功用。帶著政治目的的假設是最野蠻的,也最具有煽動性,這一點,我的父輩們最有體會。
鏡子相對于人來說是客觀的,照鏡子的行為是不客觀的,原因是鏡子需要用人的眼睛去照現,每一雙眼睛都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在鏡子中看到的對象,只是投射在鏡子中的一種狀態,重要的不是這種狀態,是當時那一雙眼光審視的狀態,審視是一種想象力的加工,它在心情裝束和欲望等東西的內外作用下,可以加工成多種可能性。我從鏡子中看到的自己,和別人視網膜上呈現的我,客觀來說是一樣的;因為有看不到的那部分,雙方也就存在不同程度的假設。這種假設的神秘之處,是主觀的,唯心的,甚至跟信仰有關。
約翰·貝歇爾在《致睡眠》中說:睡眠是死神的友好拜訪。這是詩人的假設。
諸葛亮設下空城記,操琴退敵。這是軍事家的假設。
平民如我,則多的是日常的假設,是泛假設。假設的力量,通常有著似是而非的面目,是不確定;確定性的假設,是大多數人的工作,或者僅僅是日常性的。太多依賴真實的場景,對于從事創造性工作的人們來說,是一件件厚重的外套,那樣的假設跟別人的假設沒有質的不同,最多是把一件別人穿過的外套拿來洗染了一番。外套再洗染,也阻止不了它的舊,它遲早會被時間所遺棄。
我只相信,在一無所有的地方,什么都可以假設。
咖啡物理
J說,我們在雙安商場見面吧。
我趕去那里時,西伯利亞來的風和寧夏、甘肅的沙子在北京千里喜相逢,結伴狂舞。J鮮紅的長圍巾在空中攪拌。見到我那一刻,J搓了搓雙手,同時笑,一種親切得不可置信的笑容。我們愚蠢地站在風沙里,等對方開口;或者,不說比說出來更好,也更容易解讀和融化。萬千繽紛詞語,遠遠不及一個表情來得豐富和深刻。
在雙安商場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兩人喝了很多咖啡,那種黑色的液體迅速澆灌著我密密的感覺神經,并在我的體內茁壯成長。J的眼睛像藍色晶體,說:咖啡是信仰。我也感覺到了,那幾杯液體改變了我形象上內斂的歷史,它們帶有三分傳奇、七分勁道。
J笑,說我不像中國人;我也笑,強調自己根正苗紅。J不懂“根正苗紅”這個說法,我指了指她手中的咖啡,說:就像它的來路,正宗,地道。當時我們都在喝哥倫比亞咖啡。接著,我們說咖啡,和傳奇。
生命里總有些時間是偷工減料的,需要回憶去填充它們,比如那天。那天的上午一拐彎就到了傍晚。J離去時,鮮紅的長圍巾在暮色寒風中向我揮別。J送給我一件精致禮物,說:明天就回巴黎了。然后沖我輕輕笑,那么輕的質感,像咖啡的泡沫;那么輕淺的笑,居然也笑出了眼淚。我大概沒有笑,身體被風沙吹麻木了,什么都不記得,只記得J說:永遠,永遠。一個單詞,輕輕兩錘,就嵌入心胸。
再沒見面。
永遠,肯定不是人間的日常事物,它是用來珍藏的,也有可能是無法破解的咒語或魔法。讓一個人永遠停留在某個時期,保持永恒的精神狀態,只能動用魔法。
在我的意識里,鮮紅的長圍巾就是彼得·潘的魔法。
同一家星巴克,我見過兩個人,一男一女。現在,一位在貝爾法斯特,一位在巴黎。后來我聽到英國人肖恩·沃特的一首歌:《沒有承諾》,歌詞很像是J擅長的精神態度。十多年前,我希望自己成為歌者;十多年后,我的身份是聽眾。歌者只能是一種體驗方式,不可能成為別人,歌者熱鬧的背后偏偏就是孤單;聽眾有無數的體驗可能,聽《我的太陽》時你就是帕瓦羅蒂,聽《蝴蝶夫人》時你就是安娜·辛托夫。我適合做聽眾。聲音在我耳膜(或者心胸)里震蕩時,就產生了一種叫做“共鳴”的物理反應,它不是對聲音的回答,是在向聲音本身致敬。
那以后我多了一個酗咖啡的習慣,開始喝現磨咖啡,并且義無反顧地愛上了不加糖的哥倫比亞咖啡。我煮咖啡時,只要開著窗戶,鄰居也能聞到,現在他們已習慣這種超乎尋常的香氣。那種吸引,是它熱氣騰騰背后的靈魂。這種生長在火山灰形成的高山地區的咖啡,包裝袋上印著這樣的圖案:一個戴草帽的哥倫比亞人,牽著一頭驢。它是當地咖啡生產者聯合會的標志。一個人愛上了咖啡,如同愛上了一種旅程。
在北京時代廣場地下一層,原先有家咖啡店。店內唯一的飾物就是來自各國的咖啡袋,它們以藝術品的面目鑲嵌在墻面上,在極不明朗的光線下,顯得神秘而莊重。每個周末我都會去那里喝一杯相同牌子的咖啡,坐在相同的位置上。那里的老板常常像顧客一樣坐在某個固定的座位上,喝咖啡,神游。他原先在外交部工作,去過很多地方,每到一處,第一件事就是去當地的咖啡店,喝咖啡,也收集咖啡器具。
每個周六,我像那位老板一樣坐在某個固定的座位上。那么執著。還有一個定勢反應:看到有紅圍巾從窗口飄過,就想到揮別,和“永遠”。
兩年后,我突然在北京失蹤。我花了兩年時間尋找自己。我去了廣州、長沙、衡陽、鳳凰、杭州、寧波、濟南……和咖啡店老板一樣,每到一處,我第一件事也是找當地的咖啡店,喝咖啡,也收集記憶。那個過程相當困苦,我通過記憶尋找被消磨掉的最初容顏。
容顏肯定是時光的一件外衣。短短的幾年之后,原先認識我的人,極大多數不認識我了。這對我來說是個好消息,我從別人的反應里看到了自己,找到了卑微的職位之外的自我,熱鬧之外的自身。也許這跟咖啡有關,它改變了我的容顏,和內心。依然認識我的人,是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在乎過我的容顏。
我喜歡神話和傳說,喜歡沒有根據地的游動的人事。小時候去外婆家,外婆習慣給我沖一杯糖茶,講故事。在我幼小的邏輯里,糖茶和故事是有機在一起的,來自兩種感官聯合的滋養。后來,我在麥克風前講話時也保留了這種聯合的方式:喝茶和講述。那時咖啡還沒有進入我日子的主流。中醫說,茶的作用在于清腸養氣,是調理。咖啡是什么呢?四百多年前,意大利的神職人員在沒有喝過咖啡的情況下,說它是魔鬼,是“撒旦的杰作”;親口嘗了以后,又改稱其是“上帝的飲料”。或許如J所說,咖啡是信仰。
咖啡對我來說,首先是傳說。我永遠看不清它的面目。
二零零六年春天,廣州一位編輯朋友在宵夜時,喝著咖啡,突然想到了我。他撥通了我的電話,說要給我寄咖啡。隔了些天,一包印度咖啡粉就送達了我的住地。夏天時,去參加一位朋友的圖書首發式,當地朋友也送我一大盒藍山咖啡。藍山是牙買加島上的一座山。牙買加島被加勒比海環繞,每當晴朗的日子,燦爛的陽光照射在海面上,遠處的群山因為蔚藍海水的折射而籠罩在一層淡幽的藍色氛圍中,顯得縹緲、空靈。很久很久以前,一群英國士兵首先發現了山峰上神秘的藍色光芒,島上種植園的陽光由此而著名。藍山,一個有魔法的名字。
兩種咖啡遠道而來,我到現在還沒喝完。不喝完,是為了給自己留個謎底。
寫字和喝咖啡這兩種行為有相似之處,事后都不易相信當時的精神面貌,都有超越自我的力量。它們本身就帶著傳奇的顏色。在困倦和麻木、丑陋和惡性的人世面前,咖啡會帶給我神奇的精神因子,賦予我好奇的心情、純樸的欲望、美好的發現、孩子一樣的快樂(寫字也如此);咖啡是不會動的,它喝進我的身體后,就能動了,而且動得很厲害。
我知道,遲早有一天我會揮一揮紅圍巾跟自己告別。寫字和喝咖啡會不會成為我生命中最后的事物,我不知道,這跟信仰有關。我不信仰存在的看得見的東西,我只相信傳奇和精神上的魔法;另外我相信,它們都會成為我的卑微旅程的一部分,如同命運手上牽著的一頭倔強的驢,在自己的旅程上,永不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