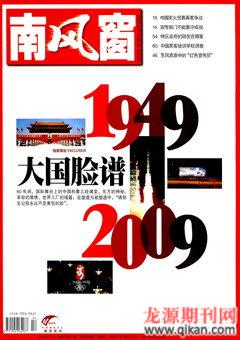金融危機是中國的發展機遇
趙靈敏
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主張既不可以也不可能。把自己和其他國家隔離開來,或許能獲得短期利益,但從長遠看沒有好處。我們也鼓勵德國企業家不要在這時離開中國,中國是大市場,只有長期堅持才能成功。
60歲的德國駐華大使施明賢博士(Michael Schaefer)有一個非常中國化的名字,顯然,他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賢明”的人。和其他深居簡出的駐外使節不同,施明賢表示自己不是一個被關在大使館里的大使,他希望到處走走,和中國社會和普通民眾保持接觸。6月1日,藉“德中同行”活動舉辦之機,記者在德國駐華使館和施明賢大使進行了對話。

堅持市場原則
《南風窗》:“德中同行”已經舉辦了3年,經歷了南京、重慶、廣州之后,今年還會前往沈陽和武漢,“德中同行”活動的舉辦,對德國而言,其意義是什么?
施明賢:德中同行是一個為時3年的德中友好合作活動。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于2007年8月28日在南京為“德中同行”活動揭幕,整個活動足跡遍布南京、重慶、廣州等6座中國城市,并將于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期間落下帷幕。
德中同行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機遇,把兩國關系提升到全新的水平,密切兩國多層次的接觸和在經濟、科學、藝術、大學生交流等方面的合作關系。我們的活動在中國各地舉辦,就是希望能和中國的老百姓、年輕人、專家等進行對話,建立廣泛深入的關系。
我們在每個城市開展有針對性的活動。比如遼寧正在進行老工業基地的改造,我們在沈陽站的活動,就希望把德國魯爾地區的類似經驗和教訓介紹到這里,希望沈陽在這方面比我們更成功和圓滿。另一個就是職業培訓,遼寧省原來主要以加工業為主,現在正在向高新技術地區轉型。以我們的經驗,有天才的、訓練有素的職工才有好的企業。我們希望德國成熟的職業培訓制度能對遼寧有所借鑒。
本次活動的一個特點,就是參與者的廣泛性,德方有外交部、經濟機構、歇德學院以及許多文化機構,而中方也有政府、民間機構、民企、國企等機構參加。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國老百姓對“德中同行”活動的歡迎程度。在沈陽,幾千人參觀了德中大道,大部分是中青年人,大家互相交換意見,彼此都很有興趣。我想清楚地表明,我們不希望這些活動是一次性的,而是能成為推動兩國各領域合作、尋找新合作形式的橋梁。
《南風窗》:目前的金融危機對德國有哪些具體影響?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方面,中德可以開展哪些方面的合作?金融危機是否會對“德中同行”,活動產生影響?
施明賢:本次金融危機是從美國開始的,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的直接后果。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經濟上的互相依存決定了從美國開始的危機對參與全球化的國家都帶來了負面影響。中德兩國的經濟都依賴出口,受危機的影響都很大。兩國政府都出臺了刺激經濟計劃,對危機做出了反應,我們需要進行密切的協調,共同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需要明確的是,金融危機不會影啊“德中同行”活動。
危機當前,我想有兩個原則必須堅持:一是保持市場的開放;二是堅持經濟規律,在世貿組織的規則內行事。兩國的政府領導人都完全同意,市場應該是完全開放的,不應該進行地方性的保護。那種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主張既不可以也不可能。把自己和其他國家隔離開來,或許能獲得短期利益,但從長遠看沒有好處。在中國,不僅中央政府領導人反對保護主義,地方政府的領導人也在刺激經濟計劃中鼓勵企業公平競爭。我們也鼓勵德國企業家不要在這時離開中國,中國是大市場,只有長期堅持才能成功。雖然有德國企業家抱怨在某個領域沒有得到公平對待,但我們相信這只是個別例子,不是中國官方的決策。
金融危機之后,中國面臨著更大的發展機遇。首先,中國很可能在未來進行經濟結構改革,推動內需的增長,通過相關的措施,中國能更好地參加國際競爭;其次,中國會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引入外國的投資和技術。中國中央政府決定要在2020年前把中國建設成知識型的社會,那就需要和科技發達的國家進行更密切的合作。第三,中國會進一步融入全球化機制中,會舉辦越來越多的國際會議來討論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在這些方面,中德之間的合作前景都很廣闊。比如,2009年3月30日在柏林舉行了德中科技教育年活動的開幕慶祝儀式。德國教育與科研部部長Annette Sehavan女士和中國科技部萬鋼部長參加了開幕儀式。今年6月,Sehavan女士還到沈陽參加了德中大道的活動。

目前,氣候變化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和挑戰,歐盟、中國和美國應該在其中起領導作用。德國企業在環保技術方面居全世界領先地位,能夠提供給客戶最好的、性價比最高的具備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我們在這方面的合作機會會越來越多。
中國的努力剛剛開始
《南風窗》:前不久在倫敦召開的G20峰會,被認為是彰顯了世界的多極化趨勢。您同意這種說法嗎?您如何判斷目前的國際格局和美國的國際地位?
施明賢:1990年代初蘇聯的崩潰已經說明了,只有兩個超級大國主導世界事務、其他國家無法平等參與的世界體系已經難以為繼。從那時開始,世界的多極化趨勢就已經出現了,雖然沒有一蹴而就,但它是一個新過程的開始。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各個國家相互依存,每個國家都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世界上的事情當然應該由各個國家平等參與和協商。這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就體現得很清楚。
金融危機的發生對美國影響很大,但美國的社會政治體制仍很穩定,在未來很長時間里,美國仍將是世界上的經濟、軍事大國,在新的世界體系中仍將發揮重要的領導作用。歐盟的作用也會越來越大,事實上,歐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合作組織,它能在內部保持和平長達60多年,這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是非常重要的經驗。歐盟能通過協商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它將在政治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在過去30年里成功實行了改革開放,經濟上的成就有目共睹。未來,中國會在世界上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和責任,成為世界體系越來越重要的參與者,這也是其他國家所希望的。當然,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有很多內部的問題需要解決。另外,日本、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國家的作用也會越來越大。
《南風窗》:國作為一個力量不斷上升的國家,在國際上獲得的評價毀譽參半,有人認為中國不過是一個有錢的暴發戶而已。請您告訴我們,在德國和歐洲人民的眼里,中國的形象到底是怎樣的?他們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
施明賢:我個人相信,中國的崛起是世界的機遇而不是威脅。當然,中國是這么大的一個國家,人口這么多,經濟發展速度這么快,有些人害怕中國的崛起,對此有顧慮,這是可以理解的,這主要是因為對中國不了
解造成的。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及其領導人,都認為中國的崛起是機遇,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
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在于,能否在未來一直保持穩定高速的發展。中國的情況很復雜,政府重視內部的穩定,這是很正確的。但我愿意在這里和大家分享德國的經驗:和今天的中國一樣,德國也曾經被認為創造了“經濟奇跡”,全世界都很佩服德國。回顧歷史,我們得出的最重要經驗就是,要建設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僅有經濟的發展是不夠的,對人權的尊重是一個重要前提。2009年,我們慶祝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實施60周年,雖然深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但我們很驕傲在過去60年里所建立的穩定的民主社會。
我們高度評價中國在經濟、人權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時,我們也希望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依據世界公認的人權觀念、公約,在社會政治政策上能進行調整。
《南風窗》:近幾年,中國一直致力于國家“軟實力”的建設,您如何評價中國的“軟實力”?
施明賢:20世紀一個國家的地位是由它的硬實力決定的,而21世紀,軟實力的作用更為關鍵。某種程度上,它就是一種向其他國家介紹自己并獲得信任和理解的能力。今天,由于科技的發展,人們的溝通手段更為多樣和便捷。但無論是電視還是互聯網,都不能代替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在這種情況下,了解其他國家的文化和歷史,學習其他國家的語言,就成為建設國家軟實力的一種重要途徑。因此,無論是孔子學院還是歌德學院,這類涉外文化機構在增加人民之間的了解、避免誤解方面都會產生重要作用。
當然,到目前為止,中國還不是一個軟實力強大的國家。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必然,因為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才剛剛開始,外部世界要調整對中國的看法,還需要很長時間。當然,中國也需要做很多努力來改善內部治理,同時宣傳自己。
“德國制造”的經驗
《南風窗》:大部分的中國人對德國有這樣兩個印象:精良尖端的產品質量和德國的統一。現在,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但產品的附加值低,產品質量事故時有發生。請您簡要告訴我們,德國的產品質量為什么好?
施明賢:“德國制造”是好品質的代名詞,這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歷史上,德國產品曾經是劣等品的代名詞,而當時英國制造是高級貨的象征,英國經濟界甚至把德國貨趕了出去。但到了19世紀,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到了19世紀末,德國制造已經成為高品質的代名詞,這是因為德國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首先,從19世紀中葉開始,德國一直以中小企業和家庭企業為主,大企業集團很少。中小企業靈活、反應快、專業化程度高,更容易在市場中找到自己的優勢所在。中國目前比較注重大企業的發展,對中小企業支持不夠;其次,德國有一個幾百年的傳統,那就是注重質量而不是注重數量,重視特殊的、專業化強的產品,而不是鼓勵大規模的制造;另外,德國有完善的職業培訓制度,不是每個高中生都只有上大學,很多對技術感興趣的學生可以上職業培訓學院、中心,在那里,他們不僅可以學習相關理論,還要參與實際的生產,這可能是世界上大學生之下最大的工程師群體。
《南風窗》:德國從分裂到統一,歷時41年。西德主導德國統一的基礎是什么?
施明賢:在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之前,西德和東德都已經在各自所在的集團中扎了根。之所以能統一,蘇聯的解體是重要原因,但更為根本的是,東德的老百姓希望到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政治制度中去生活,而在統一前很多年,人們都已經看到。為;德的政治制度在這方面并沒有成功,因此統一也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在此之前的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倒塌,我們親眼目睹了東德的老百姓是多么高興。很多東德人開車到西柏林,表示再也不愿意在一個不自由的體制中生活了,他們要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20年來,統一后的德國經歷了復雜的發展道路,當初的很多夢想還沒有完全實現,東、西兩部分的差距依然存在,我們面臨很多不好解決的問題,但每個德國人都認為,統一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