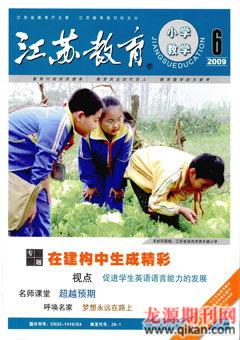要重視新知的完善與強(qiáng)化
王廣闊
傳統(tǒng)的數(shù)學(xué)教學(xué)忽視學(xué)生的主體地位,往往是從知識(shí)到知識(shí)。例如,公倍數(shù)的概念是“幾個(gè)數(shù)公有的倍數(shù)叫做它們的公倍數(shù)”。學(xué)習(xí)過程就是由倍數(shù)的概念拓展到公倍數(shù)的概念。采取這樣的編排方式勢(shì)必讓學(xué)生感覺到數(shù)學(xué)是抽象的、枯燥的,教師也無法根據(jù)教材引領(lǐng)學(xué)生深入體驗(yàn)數(shù)學(xué)的應(yīng)用價(jià)值。與之相反,蘇教版國標(biāo)本實(shí)驗(yàn)教材。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生活情境。為學(xué)生建立數(shù)學(xué)概念提供了生活原型。如教材利用正方形能否鋪滿指定長(zhǎng)和寬的長(zhǎng)方形的實(shí)例,巧妙地引入公倍數(shù)的概念,使學(xué)生感受到數(shù)學(xué)與生活的聯(lián)系。這樣的教材安排,不僅彰顯了數(shù)學(xué)的價(jià)值,更有效地激發(fā)了學(xué)生的探究欲望。有利于教師組織探究性學(xué)習(xí)。
事物總是具有雙面性,如此好的教材走進(jìn)課堂之后,同樣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主要的問題是教師在組織探究性學(xué)習(xí)時(shí)把新知的獲得當(dāng)成了探究性學(xué)習(xí)的最終目標(biāo),似乎學(xué)生經(jīng)過一番探究并得到了結(jié)果也就完成了教學(xué)任務(wù)。例如,在教學(xué)“公倍數(shù)”時(shí),根據(jù)情景揭示了公倍數(shù)的概念之后,就匆匆轉(zhuǎn)入下一個(gè)環(huán)節(jié)——“求兩個(gè)數(shù)公倍數(shù)”。眾所周知,一個(gè)概念的形成必然要經(jīng)歷由具象到抽象、由表面到深入、由籠統(tǒng)到清晰的過程。僅僅根據(jù)一個(gè)生活情景獲得的認(rèn)知顯然是具象的、表面的、籠統(tǒng)的,教師以此為新知教學(xué)的終點(diǎn),學(xué)生獲得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是不穩(wěn)固的,教師接著進(jìn)行下面環(huán)節(jié)的教學(xué),實(shí)際上是把教學(xué)演變成了一個(gè)不斷積累困惑和難點(diǎn)的過程。如此水過地皮濕的做法,由于不夠深入,缺少強(qiáng)化,致使學(xué)生的理解浮于表面,大多數(shù)學(xué)生一知半解。長(zhǎng)此以往,學(xué)生的雙基會(huì)越來越不牢固,缺少后勁,無法建構(gòu)數(shù)學(xué)知識(shí)體系的大廈。
許多一線教師忽視新知的強(qiáng)化和完善,不應(yīng)該簡(jiǎn)單地歸結(jié)為教材本身的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教師習(xí)慣于循著教材的思路按部就班,不能夠深入鉆研教材和有效把握學(xué)情所致。因此,我們數(shù)學(xué)教師更有必要多一份理性,多一份獨(dú)立思考。讓新知在強(qiáng)化中得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