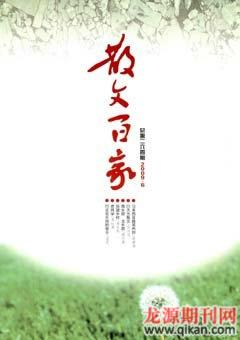普希金故居
楊振喜
在俄羅斯,有多處普希金的故居和博物館,如果停留的時間過短,就只能有所選擇舍棄,找那些有代表性的看。本來,這次參觀圣彼得堡的普希金城是首選,因為這里最典型,它是一個普希金文物保護區,幾乎包括了詩人一生的全部,像詩人生活和居住過的皇村,曾經就讀的中學,房舍還在,收藏著普希金當年生活用品、他的作品、以及私人細軟。這地方恰在圣彼得堡的郊外,風景秀美,自成一域,特別是聞名于世的葉卡婕林娜宮,還有尼古拉二世興建的富麗堂皇的亞歷山大殿,構成一個獨特的景點。當然,尤使我們難以忘懷的還是名揚天下皇村了,令人朝圣一樣地追逐不舍。自然,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一隨其便,皇家宮殿建筑堂皇巍峨不同凡響,但詩人的人格精神和風情一世的經歷,與他那永恒魅力的詩歌更令人景仰不止。這塊皇家園林正是因了詩人的大名而永垂不朽。導游小姐列娜對我們說,由于它的內部正在裝修,這次就看不成了,只好作罷,以待來時。這消息使大家遺憾;她是本地人,頗能理解我們的心情,便繞道到皇村中學門前,在一座普希金雕塑像前,讓大家照相、紀念。塑像真人一般高大,斜靠在一個長椅上,正凝神沉思,頗具詩人氣質,許多中文版詩集封面經常見到這張照片。睹此,大家的情緒被重新調動,先時的懊惱一時間消失,轉為興奮。畢竟這是在詩人的故居旁邊拍照。同行者中多為詩人,他們的文學之旅,起步時大都與這個人物有關。著名詩人劉章的老伴,乘機發言,她說:“我們就是沖著這個來的,劉章年輕時學習寫詩,最喜歡的就是老普。直到,一說起普希金,精神頭兒就來了。”于是抓緊時間照相,搶著站在詩人塑像前拍照,熱鬧起來。機會真的難得。你瞧瞧,詩人凝重地望著大地,望著遠道而來的這群異國他鄉的詩歌信徒,不知該作如何感想?他們都已雪染鬢發,然而愛詩的心依然燃燒,赤童一樣地依偎在老爺爺的身旁,流露出少見的天真。我當然也不肯例外,先照上兩張再說。第一張是與老伴合影,自不必說,我們相濡以沫四十年,風雨兼程走到今天,不容易呀。我的文學之路,只有她清楚,每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是她給我以支撐,當一切盡失之時,又有她從旁鼓勵。她常常說:“既然喜歡上的東西,就不能夠放棄”。我的多次舉家搬遷,都多虧了她一雙勤勞的手,付出了太多的汗水。每次搬家,都是她整理行李、家物,囑咐最多、擔心最大的,莫過于我的手稿,那一摞摞的文稿,都凝結著我的心血與汗水。2000年我主編一本《重溫舊夢》,稿子是從全國各地寄來的,是她忙中偷閑幫我整理,一一過目、校審。照片不夠,她不吝辛勞,跑到幾百里之外的母校去補拍。僅此也就足矣。第二張是我的單人照,我站在偉大的普希金腳下,讓“俄羅斯詩歌的太陽”照耀著,仿佛也詩人了一回,頓使我長了志氣,壯了臉面,威風許多。
談到皇村中學,不禁想起詩人的成名之作《皇村回憶》,我讀這首詩的時候,也是一個13歲的中學生,少年普希金對自由的追求,愛情的謳歌,對黑暗的鞭撻,和對祖國的情懷,都與皇村這片美麗的土地有著關聯,詩歌將我深深感染,詩中那不可一世的宏大氣魄,美麗動人的語言節奏,不敢相信是出自一個中學生之手,讓人贊嘆。那時節,和新生的中國一樣,充滿朝氣與陽光,理想主義盛行,青少年們正有許多文學夢幻,有著美麗的人生幻想與期待。普希金在天幕上的出現,使我們眼前一亮。生活就如同詩章一樣。我的身邊就發生了這樣的故事。當我考取河北南宮省中不久,同村的高小同學先我一年已在河北邢臺省中就讀。這年暑假,他弄到一本查良鏞(金庸)翻譯的《普希金詩選》,視如珍品,他講,在他們班里,普希金的詩已很風靡,幾乎無人不能背,說著說著就背出了好多首,使我特別驚訝。他之所愛很快也感染了我,于是我就借了來,他限我一天讀完,并立下保證。在家里一盞暗淡的煤油燈下,我將詩集從頭至尾抄寫在一個草紙本子上,許多詩當時都可以背誦下來。比如《高加索的囚徒》、《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騙了你》、《漁夫與金魚的故事》、《致同學們》、《致恰阿達耶夫》等,直到現在印象還很深。后來,因為家鄉發了洪水,那個手抄本不知被沖到哪里去了。我的這個同學,因為家庭經濟困難,沒能讀完中學,提前參加了工作,娶妻生子,沉重的生活擔子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但在饑寒交之空閑,他依舊堅持著讀詩、寫詩。六十年代初,我已經是天津某所中學的教員了,他以為我很有能力或辦法,就把整理好的一本厚厚的、未曾發表過的詩集寄給我,求我發表或出版。他不知道我還沒有爬進文壇的圈里呢,沒人買我的賬。但我一直在推托著,等待著,不愿撲滅他那個微小的念頭。沒有料到,日后不久,他卻因肝癌浮水過早離開了人世,只有二十多歲。一個未竟的詩人,一個普希金的忠實“粉絲”,就這樣無聲無息地走了。想起這件事我就非常難過。未能幫忙實現他的夙愿,一直是我心頭難泯的愧疚。文學這東西,是個魔鬼,既然沾上了,就會被它糾纏一生的,除非你不是真正愛它,倘若是玩耍,游戲,那就另當別論。所以,我們不必去責怪他太傻呆,更不能去“怪罪”普希金,一切都和他無關。
讀大學時,在外國文學課堂上,不只學了他的抒情詩,還學了他的詩體長篇小說《歐根·奧涅金》,老師還專門分析詩中的人物,因而也就知道了文學上“多余的人”的來歷。參加工作后,我在閱讀中,偏偏喜歡上他的小說。如他的《別爾金小說集》,不只是喜歡它的短小雋永,詩性的氛圍,自然明快的語言特點,更喜歡他的小說故事的單純、簡潔,因而便一讀再讀,不愿釋手。讀中篇小說《上尉的女兒》和《驛站長》,感受到作家與現實生活的對應關系是那么貼近,真像一位戰士極力捕捉社會前進的動力,作品的主旋律是那么鼓舞人心,催人向上。尤其,作家還明確、大膽了普加喬夫農民起義領袖這一人物形象,他毫不在乎當局的政治壓力;同時,他又注意揭示底層小人物的原生狀態,從而開創了俄羅斯文學描寫“小人物”的先河。我一直在想,這種源于現實生活的創作走向與文學精神,是俄羅斯文學的一個重要元素,構成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優良傳統。這也是普希金能成為“俄羅斯文學之父”的重要原因。以上,只是我從作品中,從前人的解讀,認識到的普希金。但是,近距離地接觸普希金并撫摸他,走進他生活的現場,去感受、體驗那個實在具體的普希金,還是要到莫斯科阿爾巴特街普希金博物館之后。
阿爾巴特大街,有五百多年的歷史,是莫斯科最有名的步行街道,距外交部大樓很近,它為東西走向,往前,可與新阿爾巴特街接通。前蘇聯時代,在這里曾發生過許多政治事件,比如斯大林的肅反運動。后來出版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小說,轟動一時,其背景就在這條街上。在我國很有市場,最近又再版。街市上有古玩店、舊書店、黃金珠寶店。有人說,它類似中國的琉璃廠,也許有些道理,因為它充滿濃濃的文化氣息。我們抵達得比較早,許多商店還沒開門,顯得有點冷清,幾家小商販在街中心擺了攤兒,一家在賣楊梅、蘋果,還有叫不上名字的水果,都是遠道而來,看上去不甚新鮮,價格卻昂貴,一個小梨兒就要十幾盧布,蔬菜品種不多,買菜的也寥寥。一位老年婦女買了兩根黃瓜,一綹韭菜,搖晃著腦袋走了。莫斯科的物價奇高,普通職工月收入僅有一二千盧布(合人民幣六七百元),新鮮蔬菜是吃不起的,他們光顧市場而不購買。往前,有專門為人畫像的民間藝術家,藝術功力不低于國內專業畫家,要價卻不高,不抵他們的十分之一,還有幾個叫賣手工藝織品的,糾纏不放,一塊粗毛毯繪織上俄羅斯風景人物油畫,夠檔次了,要價也很低廉。俄羅斯是以油畫著稱于世的藝術大國,許多著名的博物館,都有世界頂級的藝術大師的作品展出,而且真品居多。詩人浪波夫婦購買了一幅繪有俄羅斯田園風光的毯畫,僅一百盧布(合人民幣只三十元),這在中國恐怕是買不到的。值得一提的,是這條街53號,在大街中間之右側,有一個不甚顯眼的門洞,一塊小匾牌掛在旁邊,由于不識俄文,我們差一點從這里走過,就如一個極為平常的店鋪。導游出面告訴大家,說: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普希金博物館。當然,此是最早建造成的,而非最完整的一個。他在1986年重新裝修后開館,一切都恢復了百年前的原貌。普希金住進這所公寓時,是他與娜塔麗婭新婚不久,只在這里住了三個多月。一座二層小樓,樓上樓下有五六間廳室。導游不給講解,只能自己買票參觀。上樓,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先走到書房,靠墻而立的書架上都是外文書籍,散散的擺放著,并不多,再進去,是一個寫作間,桌上和畫案上是詩人的手稿和書信。外文是天然飄逸放縱式的,加上詩人的桀驁不馴生性,給人的印象太深了。繼續往里走,是一間很寬綽的大廳,裝飾的豪華典雅,天花板上懸掛著精致的水晶燈,在當時也很高雅,可能是為妻子專門安排的一個舞廳。大家都知道,他的妻子美麗超群,風情萬種,上流社會的公子與顯赫的貴族都特別關注這個“莫斯科第一美女”,所以,在大廳里經常舉辦一些舞會,滿足這些人的窺探欲,也是應當和值得的,而且也是普希金樂見所為的,因而,每天這里熱鬧非凡就很自然了。我們在這里特意留影作為紀念。有誰,還在娜塔麗婭像前駐足凝神,揣想詩人的悲劇命運是否與這個美色的女人有點瓜葛?在小客廳,還有詩人一尊大理石的頭像,與他在皇村的那個沉思狀態的雕塑不同,充滿了青春氣息。我在他的像前拍照,感受到的是詩人的甜蜜與幸福。這是青春的普希金。從普希金的創作經歷上看,他的不少優秀之作,都是在莫斯科期間寫作的。書桌上與墻版上展出的手稿、書信,也都是他躊躇滿志的神情流露。我還發現,有幾幅普希金隨意涂鴉的速寫畫,簡約,明了,質樸,一種生生不息的精神,天馬行空,隨意揮灑,這就是天才,俯拾即是。三個月后,這對新人離開這里去了美麗的皇村,去享受那皇家園林的豪華盛宴了。
從博物館出來,與故居斜對面,是一座新建起的普希金夫婦的大型雕塑。基本上是按照兩個人原貌創作的。普希金氣質浪漫瀟灑,娜塔麗婭美麗動人。雕像外表被擦拭得煥然一新,高高地矗立在大街一邊,有人走過來,對他們投下尊敬的目光,或隨手獻上一束鮮花。經常有志愿者來為雕像作清潔,對藝術品珍愛有加,俄羅斯人的文化修養和素質,隨處可見。遠比國內一些景點的雕塑一夜之間被身手異位、面目全非的情景要好許多。在俄羅斯,無論走到哪里,堅守公民道德,愛護公眾秩序,自覺為社會做好事,平常易見,實際上也是一種公眾的覺悟。
我們沒有去了莫伊卡河的另一個普希金紀念館,那是1925年建立并開放的,是最早開放的故居博物館。人們知道,那地方是詩人的傷心地,是他辭世的地方。在一間書房里,當年的寫字臺,鵝毛筆,小黑奴的墨水瓶都依然如故,決斗時所穿的那件薄呢背心也保存完好,那個座鐘永遠地停了在2點45分上,這是他與世長辭的時刻。據說,每到一年的2月10日中午2點,無語的人流就會擠滿普希金的門前濱河街,幾百支蠟燭圍繞在通往詩人銅像的小徑上,集體出發送別詩人,170多年過去了,依然如此。俄羅斯人守護他們民族的精神文化,永愛自己“詩歌的太陽”。我們沒能見到這個沉重的場面,但我們的心一樣的沉重。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曾照耀過我們的昨天,還會照耀我們的今天和明天,會永遠地繼續下去,關于這個,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