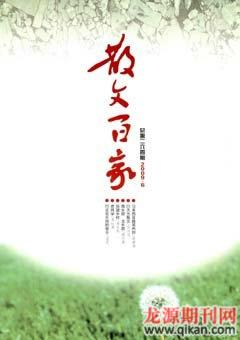書恩書緣
梁儷千
“書恩書緣”原是山上小城里一家書店的名字。第一次見到這個名字時,心中有種別樣的感覺,覺得這名字里有一絲淡淡的溫馨,這名字下面還可能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這種感覺吸引著我,常常在休息日里去買書,在等公交車的間隙里去瀏覽書架上各種風格的書名。
書店不大,半間門面,除了臨街的一面開了一個大玻璃門,其他三面墻壁均被書擠滿了。像一個家底非常殷實的小戶人家,讓人暗暗贊嘆。每次去都買幾本書,張愛玲的全套珍藏版就是在那兒一次性買回來的。那兒的書正規,又可以打折。
店主人的態度和我猜想的差不多,平和又親近書。通常有兩個人輪換值班,憑感覺應該是母子。母親稍微開朗一些。那次我去買書時,她即興對我發表議論:“農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為啥差別那么大?就是因為農村孩子從小讀書太少,家長不重視。就知道給孩子買吃的買玩的,不知道給孩子買書!”她的觀點我是百分之百贊成的。兒子有些靦腆,長得高高大大,一說話先微笑,還有些不好意思,像個害羞的小姑娘。每次去都是見他坐在桌前,或是看書或是看桌上的袖珍電視。
書店正中擺著一張鐵床,鐵床上鋪著葦席,春夏秋冬,沒有改變過。床的四周剛好留下一個環形通道,供顧客們來來回回地走動挑書。挑好書之后便坐在床沿上翻看,看多久算多久。反正坐著也不累,店主人也不驅趕。常常因了這一點拿它和宜昌的書店做比較。無非是一個政府所建,一個私人所開;一個大,一個小。實質都是一樣的,不只為賣書而賣書,而是出于對書和讀書人的敬重。
我在“書恩書緣”曾買過一本劉墉的圖文合集《在我最浪漫的時候》,里面的山水國畫很美,文章也是我很喜歡的。作者自己也在前言里說,是自己二十三歲到三十五歲之間最唯美的篇章。買的時候封面已被無數的手摸得很臟,字跡有些模糊不清。很多日子后才發現書皮正面印著一個小小的“上”字,才知道這本書原是一套中的其中一本。那個“上”字剛好在書名第四個字的右下角,又是同一種顏色。封面上其他的字全是黑色,獨這兩個字是橘紅色。大概是這種別樣的設計,吸引了很多獵奇的眼睛。因此無數次地被抽出來翻看,又無數次失望地放回去。連書背上的“上”字都給摸丟了。在買書的時候,我習慣于看書背上的文字介紹,看準了就抽出來直接翻看,對正面封皮只是一掃而過,并不怎么留意。出于對那“上”字疏漏的愧疚,我又仔細查看整個封面,又在書背上發現了幾個小字“畫文精品”。書皮實在太臟了。這種現象也只能出現在“書恩書緣”這樣的書屋里,你可以把它當作閱覽室,愿看多久就看多久,不買也罷。書臟了舊了隨其自然,因為愛書人明白,書的質量是沒有新舊的,只有內容上的優劣。從這一點來說,“書恩書緣”的主人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播種一種文化了。
總覺得這書店背后應該有個書氣很濃的人支撐,但在“書恩書緣”里始終沒有見到。
一個傍晚,下了班又去“書恩書緣”買書,卻發現人去屋空,書店關門了。臨家店主告訴我,店家的兒子上班了,沒人看店,開不下去了。那么多的衣服店都可以雇人打理,可見書店生意的冷清。心中不免生出許多感慨蒼涼來。
回家后,將這件事說給女兒聽,“媽媽失去了一家最好的書店。”女兒說:“媽,不必擔心,我同學在職工醫院住。她告訴我靠近醫院的水邊有一家‘文苑書屋,是和山上的‘書恩書緣一家的。這家書店特別好,書又全又便宜,我同學就喜歡在那里買書。”女兒的話讓我一陣欣喜。
在以后的日子里,傍晚只要和女兒一起去水邊散步,便去“文苑書屋”一覽。不管買不買,總愛在那里逗留一會兒,隨便翻幾本書。有一次看書時間太長,心中有些過意不去,便買了一本珍藏版《古蘭經》。可惜這本書到現在我也沒來得及好好看,變為純粹的收藏了。
書店主人的確是一位文縐縐的老先生,戴著一副眼鏡,神態祥和,說話不緊不慢,很親切,原先是在舞陽教書的,我稱他陳老師。山上的“書恩書緣”是他的一個分店,看店的是他的妻子和兒子。老先生告訴我,他聽家人說過,山上有一位很文靜的女讀者,經常光顧他們家的“書恩書緣”。而且,書店關門的時候,還欠著這位女讀者幾本書。(我常常把想要的書列個單子留在店里,好讓他們進新書時特別留意一下。)我一去“文苑書屋”,老先生便感覺到是我了。
老先生的案頭養著一盆文竹,特別茂盛,像一叢郁郁蔥蔥的竹林。看著那根根綠莖仿佛能感覺到叢林深處散發出的清涼之氣來。我問老先生這文竹是否修剪過,因為之前見到的文竹總是藤條一樣彎彎曲曲,伸得很長,似乎已失去了竹的品性。他說沒有,就是這品種。從文竹的長勢看,老先生應該是養竹有法。一般愛書的人都和植物有緣。
市里要“四城聯創”,一些影響市容的舊屋都陸續拆除了。回鄉下老家時途徑“文苑書屋”,發現那里的房子全被寫上了“拆”字。再經過那里時,又見屋的牌子沒有了,門關著。我想,老先生的書屋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要是搬回舞陽老家,在這水邊小城里也失去了一個好去處,而且這次失去恐怕真的沒有希望了。我在山上小城上班,在水邊小城安家。
幾個月后,去醫院看病,見書屋旁邊的幾家店鋪仍然經營著,獨書屋關了門,就去打聽。臨家店主說,書屋還在,不知老先生這會兒去哪兒了,剛才還在呢,你等一會兒吧,不會太遠的。知道書屋還在就好,改天再來拜訪吧。有一種失而復得的欣慰。
又一次去書屋時,正是夏季,我給老先生送我自己寫的書,順便再核實一下情況。我在整理從前的文章,有一篇寫到了老先生家的書店。
走進書屋,感覺比先前凌亂了些,書案上的那盆文竹也有些憔悴,挨著文竹的旁邊多了兩個魚缸,一個魚缸里面養了一只小烏龜,另一個魚缸里養了幾條小魚。書屋正中多了一個冰柜,冰柜上趴著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正聚精會神地看著一本書。看來老先生的生活不似從前那般悠閑從容了。我問冰柜邊的孩子是誰,老先生說是他的孫子,每天他把小孫子從幼兒園接回來就呆在自己的書屋里,和他形影不離。說到孫子,老先生的談興高漲,連眼睛都放出光芒來。他說孫子如何聰明機靈,幼兒園的老師如何喜歡自己的孫子,孫子如何愛看書,知識面如何廣、如何懂事等等。還說有一次領著孫子從湖濱走過,看到湖里的水泛著微波,小孫孫就說:“爺爺您看,湖里邊波光粼粼的。”老先生很高興,又接著問:“如果波浪再大些呢?”小孫孫脫口而出:“波濤滾滾!”老先生的幸福溢于言表,簡直是滔滔不絕了。
受老先生的感染,我也把贊美的目光投向孩子,發現孩子的注意力一直在書上,似乎我們的談話與他無關,爺爺為他唱的贊美詩他一句也沒聽到。依然是我剛進屋時看到的那副專注神態。老先生有些激動,一連聲地叫著小孫孫,想讓他和我們一起說話。叫了好幾遍,那孩子才極不情愿地放下書,走了過來。看得出,孩子的確是愛書非常。我問孩子都讀些什么書,老先生說,剛開始的時候讀一些小畫冊,后來,連書架上的《作文大全》之類的書都看了一遍,課堂上,老師特別喜歡提問他,因為他知道得多,問到哪兒都難不住。我問孩子這么小怎么認識這么多字,老先生竟然有些說不上來了:“我也說不清他怎么就認識了那么多字,就是天天來了就看書,看著看著就認識了。沒有誰專門去教他認字,我們家的人好像對書有一種天生的悟性。”說著,老先生就說起了自己的家事,自己兄弟姊妹六人,后代都沾了書的光,全都通過考學從農村走出來了。村里出了八個大學生,有五個是他們老陳家的。老先生一臉的榮耀。老先生無意間忽略了自己的典范作用,把自己對這個家族的熏陶結果說成是晚輩們自己的悟性,并大加贊賞,這是多么可愛又多么高明的家長。
也許,好書的氛圍催生了賞識,賞識讓晚輩更加愛書,這是個良性循環。難怪新華書店把“家有藏書子孫賢”的宣傳橫幅掛在最醒目的位置上。
老先生的書屋里沒有這樣的標語,但老先生心里有。試想,如果老先生開的是玩具店,小孫孫天天隨他來會是什么情景;老先生開的是食品店,小孫孫天天隨他來會是什么情景;老先生如果只長了顆錢心,什么書掙錢就賣什么,書架上烏七八糟,小孫孫天天隨他來又會是什么情景。老先生書架上的書是可以讓小孫孫隨意翻閱的,因此小孫孫就知道了宇宙的黑洞,知道了螞蟻的很多種類,還知道了“波光粼粼”和“波濤滾滾”,還知道了媽媽背地里稱爺爺為“老頭兒”不對,應該叫“爸爸”。
我發現來書店的人不多,生意顯得很冷清,就問為什么不添些新書,老先生說:“晚上來這里看書的人多。開書屋是一種樂趣,指望它吃飯是糊不住口的。再說這房子指不定什么時候就拆掉,書屋開不長了。”我問將來往哪里搬,老先生說:“還不知道呢。書店的生意不好做,到時候再說吧。”
真希望老先生的書屋再次掛上“書恩書緣”的牌子,在這山水小城里獨成一道永久的風景,成為更多人溫暖的去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