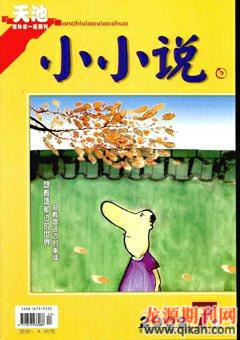礦山
張新福
山丘的臉黝黑而粗糙,散發著煤炭般的光澤。礦山的天總是懸浮著一層凝重的灰沙,壓得人喘不過氣。山丘抬頭,瞇著眼睛,看見一輪灰黃的太陽墜入西邊的山坳,心中對女人的思念便像雨后的野草漫山遍野地瘋長。
山丘的女人賢惠,勤勞,任勞任怨;女兒漂亮,懂事,成績優秀,是學校的優等生。老師說,孩子以后一定能考上一所好大學,前程似錦。家里的幾畝地長不出茁壯的莊稼,也長不出一沓沓鈔票,為了女兒的未來,為了治愈女人的癆病,山丘離開女人,走向礦山。走向礦山,透過煤炭的厚重,他看到了女兒光輝燦爛的未來和女人健康圓潤的身體,于是心里就亮堂了。
礦山危險,多個心眼。女人的話像女人一樣樸實,山丘聽了十多年仍不嫌膩。
唉!山丘回答。
實在扛不住就回來。女人說。
唉!山丘答道。在這個貧寒的家,山丘放不下的東西太多太多,看到女人的淚心里酸溜溜的。
你去吧,娃比什么都重要。女人說這話時,臉上掛著欣慰的笑。
記得吃藥,有什么事做不了,喊喊娃她堂叔。山丘說。
女人無語,默默點頭。
山丘是跟同村的狗生一起上路的,狗生走南闖北多年,確切地說,是狗生引領著山丘走向礦山的。那晚,狗生看著唉聲嘆氣的山丘說:跟我去礦山吧,那些黑乎乎的煤塊都是鈔票吶。起初,山丘對狗生的話半信半疑,但一想到女兒和女人,上礦山的決心一下子變得堅定。
身后,女人嬌小的身影定格在寂寞的村口。
別扭扭捏捏的,外面有的是女人。狗生推了一把山丘,臉上露出詭異的壞笑。
狗生,你個狗日的。山丘罵道。
狗生聽后哈哈大笑。
礦山的生活天昏地暗,單調,枯燥。錢雖不多,但比種家里那幾畝地不知強上多少倍。攥著散發著汗味的工錢,山丘再次看到了女兒光明的前程和女人俊俏的身體,他幸福地笑了,干起活來虎虎生風。夜里,躺在板床上,山丘開始想女人,想女人的身體,回味女人細微而均勻的呼吸。越是枯燥乏味的日子,越渴望女人的體貼,山丘越想心里越是熱辣辣的不是滋味,難以入眠。
離家半年多,山丘給女人打過一次電話,是打到隔壁堂弟家的。好大一會兒,他聽到女人喘著粗氣的聲音從電話里傳來,很顯然,女人是跑著來的。
家里一切都好。女人說。
給你寄了三百塊錢買藥,養好身體。山丘說。
加幾件衣服,吃好點穿暖點,別省那幾個小錢。女人說。
唉。山丘回答。其實,山丘只是想聽聽女人的聲音,女人的聲音像女人一樣樸實,他聽了十多年仍不嫌膩……
晚上,躺在冰冷的板床上,對女人的渴望折磨得山丘輾轉反側。
夜里,礦山腳下的鎮上,數十家發廊的燈光與礦山上的燈光交相輝映,與灰沙漫天的礦山相比,鎮上的夜晚是另一番誘人景象。發廊的小姐搔首弄姿,細嫩的小手專往礦工們腰包伸。剛開始,山丘對那些一到夜晚就往山下跑的工友嗤之以鼻,他的心中只有家里的女人,他的工錢是女兒的學費。
別死撐著,狗生扯扯山丘的衣角說。山丘聽后,默不作聲,心卻怦怦亂跳。
一天,狗生突然高燒不退,到礦上的醫務室一查才知,他感染了嚴重的性病。
不久后的一個下午,山丘也開始咳嗽發燒,工友們勸他去查查,是不是也染上性病了。山丘的情緒一下子陰暗下來,自己雖然去過發廊一次,但什么也沒做,怎么也染上性病了?要是真的染上性病,該怎么辦?
山丘懷著憂郁的心情走進醫務室,檢查結果出來了,他只是患上了感冒,并沒有感染性病。走出醫務室那一刻,他的心變得像向日葵一樣燦爛。山丘急匆匆走向電話亭,此刻,他心中掛著的只有家里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