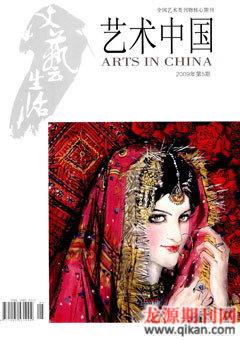紅光亮與春風已經蘇醒
唐機敏
油畫藝術到中國已經有一百多年。一百多年間,它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曲折成長,逐漸融入中國社會,浸染上中華民族的特色。在這段歷史里,最富意義、最令人回味的應屬1976年——1989年之間中國畫壇的蛻變,即文革時期“紅光亮”美術向多樣化新潮藝術的轉型,這段時期無論是藝術家還是風格流派都如雨后春筍一般飛速出現與發展,藝術生態圈生意盎然。中國寫實油畫作為這一美術流變初期的一把燃情大火,引領了中國美術潮流的變遷。至今回味當時的畫家們從文革時封閉的環境與思想跨越到文革后起死回生重染生機的藝術意識與形態,其中所做出的努力令人感概,而中國寫實油畫經歷了這一華麗的轉身,也迎來了蘇醒的春風。
這段美術史起于1976年,當時的社會背景為文革十年中統治階級對中國的文化精粹進行無情的摧殘,精華殆盡,糟粕橫行。回顧文革之前的油畫,一直有著良好的發展勢頭。自馬克西莫夫來中國進行文化支援,展開相對系統的油畫講學,中國油畫家才對油畫有了進一步真實與深刻的了解,而“馬訓班”也的確培養了一批日后在中國畫壇成氣候的油畫家。在摸索中進步的畫家與逐漸成熟的作品源源不斷地產生,為寫生初來乍到的油畫添加了新鮮血液。然而到了文革時期,油畫家和他們從事的藝術受到前所未有的束縛與壓制,僅少量作品被容許為“文革”的宗旨服務。期間的畫作大多描繪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象,夾雜記錄熱火朝天的農村生活、青年人的朝氣蓬勃,實則浮夸暗涌、粉飾太平,像湯小銘的《永不休戰》這樣旗幟鮮明一針見血的作品少之又少。這種風格后來被人稱為“假現實主義”,與文革之后的現實主義相對。從藝術角度看“文革”時期的油畫,除極少數藝術家冒天下之大不韙私下做出的藝術探索外,公開展示的大多數作品由于受制于客觀的社會條件而缺少現實主義意義,無論社會怎樣變遷,從當時的作品中很難看到警醒與真實。文革時期的美術被稱為“紅光亮”的美術,名稱背后的暗諷超過了正面的贊同。這是受狹隘文藝觀念與偏差文藝政策牽引的結果。對“審美”偏狹的理解,影響了中國油畫全面健康的發展,成為我們回顧這段歷程時不可回避的事實。值得肯定的是:任何事物發展順利之前都有一段黎明的潛伏。“文革”摧毀了絕大多數藝術的幼苗,但是土壤里的萌芽是不容毀滅的:文革美術雖然扭曲,但當時的畫家無論是對領導形象的描繪還是對形式的贊頌,大多懷有盲目而是又真實的情感,這種情感正是藝術創作所需要的,無疑這種情感的培養,有了后來生動真切的寫實主義繪畫。這一點在《紅太陽光輝曖萬代》、《挖山不止》等作品中有所體現。
經過“文革美術”的長期訓練,中國美術養成了歌功頌德的習慣,并成為一種藝術習性。這樣的創作基調在文革后延續了兩年左右,逐漸被“傷痕美術”代替。“傷痕美術”是1978年后的幾年時間畫家們廣為采用的創作方式。“傷痕美術”出現的原因是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從繪畫角度講,是向現實主義繪畫的回歸。1978年8月1日的《文匯報》上發表了盧新華創作的小說《傷痕》,引發了一場關于文學價值與意義的爭論,這場爭論喚起人們對文革的批判與反思,這種思潮也直接感染了美術界,之后的美術作品有了明顯的傷痕傾向。1978年四川美術學院學生高小華創作了《為什么》,1979年程叢林創作了《1968年×月×日雪》,這些作品在“四川省慶祝建國30周年美展”上引起了觀眾強烈的反響。后來羅中立的《父親》、王川的《再見吧,小路》、張紅年的《那時我們正年輕》、何多芩的《我們曾經唱過這首歌》、《青春》等作品都有著濃郁的傷痕色彩。以標志性的《為什么》和《1968年×月×日雪》為例,當時描寫文攻武衛的情節性作品很多,畫家們通過畫筆盡情地宣泄著自己或者大眾心里的不平、委屈與憤恨。畢竟,那是作為紅衛兵的年輕化盲目作為的見證,是他們為“文革”這一浩劫造勢助威的見證。畫家們從真誠對待假象到真誠對待真相的轉變,使自身變得真實,從而使得作品也染上真實的情調。
從寫實主義風格分析這些作品:《1968年×月×日雪》延續了油畫重要人物居中的焦點透視結構,從場面的營造上來講,眾多人物動態的描繪與情節的生動重現使這幅油畫藝術含量頗高。《為什么》則從畫面緊湊、俯瞰的構成關系與鉛灰色調及厚重筆觸的處理,使視覺上造成相當的壓迫感,這種構圖讓人耳目一新。人物的姿勢、表情、服飾、道具及周圍的環境安排,刻意營造了一種悲劇氣氛,屬于“主題性”創作的作品。再有聞立鵬、羅中立、張紅年等畫家以反“四人幫”女英雄張志新為主人公創作的一系列油畫作品,體現了當時的政治和藝術上的主張,也顯示了畫家們的創作風向標的轉向。畫家們從粉飾到正視、從歌頌到批判的轉變,直接影響了創作的思維與手法,使美術作品有了新的面貌。
如果說傷痕美術是反思與控拆的話,那么同時出現的“鄉土寫實繪畫”是真正使藝術回歸到現實生活中來,而且更加情感化、深入化,更加深入地反映現實。“鄉土寫實”以羅中立的《父親》、陳丹青的《西藏組畫》和何多芩的《春風已經蘇醒》相繼出現為標志。鄉土寫實藝術的意義在于畫家已經超過了自身身份的局限,直接面對了當時中國面臨的普遍問題。羅中立的《父親》以描繪領袖和統治者的尺寸出現在1981年的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上,難說沒引爆一聲驚雷,其寫實主義的畫風至今仍是中國油畫的重要風格之一。陳丹青則以一個城市知識分子的眼光好奇地窺探藏族人民的生活,在他的筆下充滿真誠與贊美,不能否認陳丹青注定是一個滿懷人道主義的歌頌型畫家。何多芩的《春風已經蘇醒》則為畫壇刮起一陣清新之風。受美國畫家懷斯藝術影響,何多芩的作品有著對人性、生命、情感的復雜性、豐富性的理解和描繪。他的筆下多是弱勢群體中小孩和婦女形象,富有人道主義,也是從側面來反映生活本質的創作手法。羅中立、陳丹青和何多芩表現出三種不同的藝術態度,使鄉土寫實主義展示出人道主義精神的不同方面。而這種“生活流”、“鄉土風”藝術追求成為替代“傷痕”的新的藝術潮流。以鄉土寫實風格為創作風格的藝術家為數眾多,朱毅勇、程叢林、孫為民、周春芽、艾軒、王沂東、龍力游、韋爾申、朱義勇、張曉剛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畫家,代表著鄉土創作的高度。其中王沂東和龍力游一直堅持鄉土題材的創作。王沂東在二十世紀80年代創作的鄉土作品,長于描繪人物場景的處理,具有“生活流”的偶發特征。在新中國美術史上,鄉土寫實主義藝術并不是因為它的寫實,它就是中國農民和農村生活的真實表達而具有感召力,它實際上是因為以鄉土的名義呈現和表達中國面臨的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問題,將階級的人上升至人道的人而具有重大意義。
說到這里,文革的主題已經敘述完畢,中國寫實油畫在“文革”期間的忍辱負重,至“文革”后接受了摧枯拉朽的拯救,在經歷了“傷痕美術”與“鄉土寫實主義美術”之后,無論內容或者形式,意識或者語言、及至深度上。都完成了自己的華麗轉身,在中國美術史上留下繽紛足跡。但任何學習過美術史的人都不會怠慢之后的“85思潮”,因為它就像一股新風,掀起了畫壇的新局面,對當時盛行的寫實藝術帶來了根本性的沖擊。所謂“85思潮”,實際上是引進西方現代主義的青年藝術思潮,期間藝術風格種類繁多,新潮藝術逐漸膨脹,爭相表現各自所長,占領一席之地,使寫實主義藝術一度徘徊于邊緣境地。現在看來,這種思潮帶來激進色彩。在當時,之所以很多藝術家都表示關注或參與其中,是因為它否定的有些東西是我們應該摒棄的,如虛偽的理想主義、紅光亮、粉飾太平。以及藝術創作方法的程式化、陳陳相因等等。它引進的有些藝術觀念是我們原來較為陌生的,但對我們不無啟發。它是一種沖擊力量,使我們換掉一層層破舊衣服時,才認識到哪些衣服能夠真正御寒。歷經二十多年后回顧這場藝術運動,“85思潮”并未束縛我國油畫的寫實主義傳統,寫實主義藝術從中受到錘煉走向更加廣闊健康的道路。文章題中的“春風已經蘇醒”取自何多芩的成名作名稱,筆者認為用來形容中國寫實油畫的這段歷史很貼切。在風格多變的圖像時代,寫實主義油畫始終有著自己的位置與方向,哪怕受到沖擊也不停歇前沿的探索、追求新的發展與進步。我們應該為中國寫實主義油畫喝彩。搖旗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