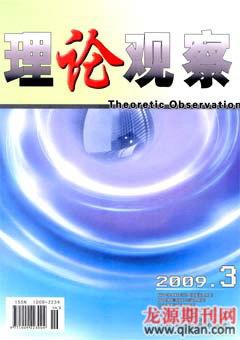生態文明與生存精神:從海德格爾談起
黃 侃
[摘要]生態文明的提出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新要求,它既表達了我們對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期望。它是經濟發展的物質文明的跨越,更應該是思想、意識、觀念及心理等層面精神文明的跨越。從人類思想史的空間性與時間性來看人類的生存問題,它不僅是某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如何把握人們在這方面的思考,則必須從整個人類的生存精神上看。在這方面的借鑒,對我們深入理解生態文明是有所助益的。
[關鍵詞]生態文明;生存精神;生活;神圣;自然
[中圖分類號]G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234(2009)03-0047-02
生態文明建設的目的是讓人民群眾在良好的生態環境下生活得更舒適、更幸福。這一目的和要求可以突出地表現為兩方面內容:第一,人民群眾生活得更舒適、更幸福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只有將經濟社會發展作為前提,人民群眾的生活才能夠是舒適的和幸福的。第二,人民群眾生活得更舒適、更幸福是精神文明建設的外在表現。只有將生態文明建設問題作為思想、意識、觀念、心理的先行條件,人民群眾的生活才能夠是舒適的和幸福的。
在這里,顯而易見的是,生態文明作為一項政治訴求,它的提出最終關系到每一個人,關系到每一個人的基本生存要求。而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這樣一個情況,即外在的政治話語賦予了我們生存的要求,賦予了我們的舒適感和幸福感。那么,這里必然會產生這樣的問題:生存的需要究竟是外在地通過政治行為給定的呢?還是自身給定的?恐怕這個問題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去問及的。但是,這確實是個問題。如果我們對此視而不見,那么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是一句政治話語,而且終將是一個政治話語;如果我們對此置而不論,那么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沒有群眾基礎,而且終將沒有群眾基礎。
如果人民群眾對“生態文明”不了解,人民群眾對生存的要求不清楚,那么,生態文明只能是政治訴求。如果人民群眾了解了“生態文明”的重要性以及生存的急迫性,并主動地參與到這一過程中來,它必然就成為一種哲學訴求——生存精神。這里我們有必要來解釋生態文明建設為什么是一個哲學問題?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就是關于一個“生活”和“神圣”的問題。
一、從“生活”的本體論角度看生態文明
在哲學領域,尤其是在西方哲學領域中談本體論談得最多的要算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海德格爾的思想的出現,重新開啟了西方人關注人的“存在”問題的大門。他討論存在意義問題,旨在揭示人的“遺忘”狀態,“遺忘”了人的本真本己性。因此在他看來,當代人需要完成的任務是讓這種被“遺忘”的本真本已性從“遮蔽”中開啟、展露出來,即“去蔽”,也就是他所說的“無蔽”。而這一工作主要是圍繞著討論“存在”和“時間”展開的。
從根本上來說,海德格爾關注“存在”和“時間”,不如說他更關注“生活”和“生命”。對于人而言,喪失“生命”與“生活”,其他的就無從談起。然而,“生活”和“生命”不能簡單做日常性的表述。因為“生命”是“神圣”的,所以“生命”可貴。但是,“生命”即便是“神圣”的也不免有終結之日。往往正是這點,人們才懷著茍且偷生的信念。所以人們怕死,就是害怕走向“終結”。而“害怕”是一種急迫,急迫獲得生的渴望。這種“渴望”就是獲得“生命”,而這時的“生命”是為著“生”——“活著”的“生命”。可是,人的“生命”又是“神圣”的,之所以“神圣”在于:“終結”的背后有一個不為人知的“世界”,即“無”的“世界”。面臨“死”也就不只是要面臨“終結”的現實,更是要面臨“造就”“終結”的“世界”。
海德格爾提出人是“被拋”,并為“沉淪”而“畏懼”和“煩心”,則都是站在“常人”——為“活著”而“生”的“人”的立場來討論的。同時,證明了“人”不僅可以“活著”而且還可以“去”“神圣”,這個“意義世界”就比為“終結”而“活著”更源始,更“前”。于是,放棄或“遺忘”“源始”就必定離“神圣”越來越遠,人也就越是無可奈何。這是“遺忘”了“生命”。海德格爾說哲學史是一部被遺忘的存在史,也就是這個道理。
“生活”,和“生命”一樣是一種“生”,也是“活著”,但是“生”的“活著”更是一種“熱情”,這種“熱情”是一種“熾熱”,同是一種積極的態度,和一種“流動”的“愛”——“熱愛”。生命有限,便顯得彌足珍貴。珍惜“生命”不是“怕死”,而是懂得“生命”為何“生”。因此,“生活”的意愿就應該是崇高的、自由的,“生活”的自由在于“生命體”的“創造”,不是聽任擺布或按部就班。它的“創造”本就是一種“活力”,“涌現”。
哲學家從思想深處來尋找“生活”的道路,而常人則從現象中去生活。我們從海德格爾談的“生活”所得到的啟示是:生活不是為了“生”與“活著”,而是為了生命的有限性而活。因此,對于每一個生命而言都有一個有限性的問題,所以都必須珍惜和熱愛,因為包括人在內的所有生命都有著同樣的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人與其他生命沒有任何優越性可言。于是,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對自身負責,同樣要對其他生命負責。用海德格爾從本體論思想的生活來理解生態文明,從根本上來說,就不光是用植樹造林維持生態的問題,更應該是從內心的精神向度來維系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因為,人與自然都是生活的部分,兩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限的。所以,我們除了要珍惜、熱愛和善待自身,還要以同樣的態度朝向自然。中國古人對待自然的態度大致和這里相當。
實際上,單單從外部世界來對生態系統進行保護雖然是必須的,但又是遠遠不夠的。換句話說,植樹造林是從政治的外在要求的方式來建設一種文明體系。然而,自古以來這方面的建設都沒有可能性。因為文明有其自身的生成形式。所以,必須要有一種從政治的外在主張或要求到內在要求的轉變。即,生態文明建設應在這一轉向下才能為其建設提供根據。從另一種角度來說,就是主動地和積極地去建設這一新的文明形態。文明的創造者是人民大眾,沒有大眾的理解和參與,任何文明都有可能是曇花一現。這里實際上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所謂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問題。即,人民群眾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力量。
文明是在文化或精神維度的深層次發展,如果沒有這種發展,“文明”也只是空殼罷了。那么,我們如何從內在的文化或精神維度上提高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呢?我們又如何能相信人民群眾就一定會參與到這樣一種新的文明建設的任務中來呢?
二、從神圣的角度看生存精神
海德格爾認為,人在現代生活的影響下,“遺忘”的“生存”不僅是“遺忘”了諸如“存在的意義問題”,還“遺忘”了“神”,“遺忘”了人自身(神性)。而這種“遺忘”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所以,我們要在充分意識到這一點過后重新“召喚”那個沒有被“遺忘”的“自己”,“召喚”隱退的神圣。當我們問及是誰在召喚神時,這個問題就再清楚不過了。海德格爾曾經舉過這樣一個例子:當我們不知道怎么游泳時,我們接受
的各種關于游泳的指導都不如跳入河中,只有親身經受它,我們便清楚怎么游了。“投入”其中便是海德格爾對“生活”的態度。
同樣,當我們問什么是生態文明,生態文明建設是干什么等等此類問題時,我們就已經開始“投入”并試圖去進入和參與其中了。這是我們對大眾疑問的解釋,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第一步。可是接下來我們又應該如何來面對這個問題呢?
關于“召喚”隱退的神圣。海德格爾認為,“召喚”神,無非就是說只要我們樂于去“召喚”。從另一個角度看,“神”不是作為“人”的“對象”,雖然說“人”和“神”不同,“投入”神似乎看來是“人”和“神”各置一方。而事實上,人“召喚”神就是,“人”到“神”那里去。然而,這樣也就將“神”擱置在一旁。按這種理解我們要“切近”神,也只能是這樣了——將神隱退。但是,在海德格爾看來這些顯然歪曲了事實。往往按照這種理解,我們只認定“人”和“神”具有差異,而就是這樣才使我們忽視了,“人”和“神”可以是同一的。但這又不是說人和神是一個東西——人就是神。神是(Gott ist)和我是(Ich bin)指明“我”和神是可以“同在”的。人和神正是在差異性——區分(Unter-Schied)的基礎上才能談同一性。
所以,海德格爾說:“‘區分僅僅是作為這個(dleserEine)。它是唯一的。區分從自身而來分開‘中間,而世界和物向著這個‘中間并且通過這個‘中間才相互貫通一體。”“區分不是事后從世界和物那里抽取出來的聯系。”這里海德格爾談到世界與物是在區分中成其本質的。以這種“區分”的觀念理解“人”和“神”的差異性和同一性,表明“人”和“神”在這種區分之間形成了其親密關系,并成其自身。但是,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區分,也就是差異性,兩者才能在之間“相互貫通一體”。也即是說,無論神和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具有差異的。然而從根本上而言,神和人是可以合一的。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就是:神邀請人,人召喚神,人召喚神的“言說”,在神的自身“道說”中,傾聽它,并守護它。神和人共同“出席”,才相互融通——聚集。
物我區分的觀念在西方思想史上持續了幾千年,在海德格爾這里被充分意識到。從同一與差異的觀念中,我們發現我和物從事實領域來看是彼此有別的,但是我和物又歷來是同一的。在本文,我們可以理解為人和自然有著天壤之別,但是人和自然之問的親疏關系是歷來有之。在這方面,中國的古代文獻早有論及,而現在我們不常談人和自然的和諧同一關系(這就是海德格爾所謂的“遺忘”人的自身存在問題),更不用說去理解自然自身的發展和規律。神圣在這里不僅意味著自然界的每一生命體(包括人)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和原因,神圣還意味著她是需要生命體之間的相互尊重的關系。
因此在這里我們就不難看出,生態文明建設的第二步就是要回到自然世界當中去,即回到人與自然原初的同一關系中來。由此,才能從精神上生發出相互尊重的情感。即,我們所說的生存精神。與前面內容相應的是:人的“生活”與自然的“生”是和諧而同一的,它們之間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區別。而這里,人與自然則可以理解為既是不同的,又是相同的。因為不同人才能認識自然,因為相同人才能去親近自然。而最關鍵的就是對自然的敬畏,這也是我們強調神圣的原因所在。
從另一方面來說,現時代的我們在精神的超越性上是低微的。無論是在一百年前尋求救亡圖存的道路上。還是現在經濟建設的要求被提到第一位的情形下。人們不會去考慮所謂的靈魂和精神的意義,更不用去談神圣的問題。這是我們貧弱的一方面,更是我們需要深刻認識的一方面。
生態文明的提出不僅是政治的需要,更是人民群眾生活的需要。在這里頭如果處理不好植樹造林的原因和價值的外在要求,和內在精神的動力之間的關系,生態文明建設的長遠計劃也會成一時的“追風”“熱潮”。如果在建設生態文明問題上樹立不起人民群眾精神的內在要求和價值導向,實際上也很難完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因此,我們才說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是一項長遠的實際工作,它還是一項長久的精神導向工作。由此,在重視生態文明這個問題的同時,還必須重視生存精神的整體要求。海德格爾給我們的啟示無非就是從生存精神上讓我們重視“生命”的崇高性和神圣性。
[參考文獻]
[1][德]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責任編輯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