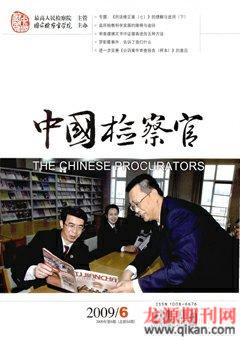論我國民事再審抗訴權(quán)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劉祥林 趙春鳳
一、民事再審抗訴權(quán)性質(zhì)是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后者是公權(quán)力的分工
民事再審抗訴權(quán)性質(zhì)是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要論證其存在的必要性,必須溯本求源分析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存在的必要性。國家與法律是一同產(chǎn)生的,“在社會發(fā)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chǎn)生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fù)著的生產(chǎn)、分配和交換產(chǎn)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的規(guī)則概括起來,設(shè)法使個人服從生產(chǎn)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guī)則首先表現(xiàn)為習(xí)慣,后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chǎn)生,就必然產(chǎn)生出以維護(hù)法律為職責(zé)的機(jī)關(guān)——公共權(quán)力,即國家。”[1]生產(chǎn)的社會化產(chǎn)生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分工,進(jìn)而要求國家權(quán)力的細(xì)化和分工。“從權(quán)力分工的角度看,資本主義國家需要權(quán)力分工,社會主義國家也同樣需要對權(quán)力進(jìn)行分工。對國家權(quán)力進(jìn)行分工是人類進(jìn)步和文明的表現(xiàn)。”[2]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的產(chǎn)生正是國家權(quán)力進(jìn)一步分工的結(jié)果。
資本主義國家設(shè)置國家機(jī)構(gòu)的基本原則是三權(quán)分立原則,社會主義國家設(shè)置國家機(jī)構(gòu)的基本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原則,這兩類基本原則雖然在性質(zhì)上不同,在國家權(quán)力之間的配置和國家機(jī)關(guān)之間的關(guān)系上也不同,但它們的基本政治理念都是相同的。”[3]我們必須認(rèn)識到,對公權(quán)力如何分工和控制沒有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但對公權(quán)力運(yùn)行的最終目的是保障人權(quán)的認(rèn)識卻是共同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已經(jīng)寫入我國憲法,檢察機(jī)關(guān)是法律監(jiān)督機(jī)關(guān),維護(hù)法律統(tǒng)一正確實(shí)施,保障憲法實(shí)施是其當(dāng)然的職責(zé)。檢察機(jī)關(guān)通過行使職務(wù)犯罪的偵查權(quán)、公訴權(quán)、訴訟監(jiān)督權(quán)和執(zhí)行監(jiān)督權(quán)等具體權(quán)力,對其他機(jī)關(guān)行使的公共權(quán)力進(jìn)行制約,其最終目的是保護(hù)公民的基本權(quán)利。
對國家權(quán)力進(jìn)行分工是人類文明和進(jìn)步的表現(xiàn),而且這種分工從來沒有停止過。二戰(zhàn)后的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從國家權(quán)力中分離出專門的憲法監(jiān)督權(quán),在國家機(jī)關(guān)中增加設(shè)置憲法法院,監(jiān)督其他國家機(jī)關(guān)正確實(shí)施憲法,對公權(quán)力直接實(shí)施憲法的行為進(jìn)行憲法監(jiān)督,最終目的是更周密的保證人權(quán)。可見存在最高法意義的憲法的國家,其公權(quán)力職能中應(yīng)該包含對憲法監(jiān)督的職能,而這一職能的歸屬,各國因法制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shí)國情不同,作出了不同的制度安排,這再次說明了國家權(quán)力分工的原理是相同的,分工的形式根據(jù)不同國家的情況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德國憲法法院是獨(dú)立于立法、司法、行政機(jī)關(guān)之外的一個憲法機(jī)關(guān),是三權(quán)之外另一種的權(quán)力,其存在的目的是為了監(jiān)督所有國家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包括立法權(quán)、行政權(quán)、司法權(quán))正確實(shí)施憲法。德國經(jīng)歷了法西斯獨(dú)裁統(tǒng)治的深刻教訓(xùn),對國家權(quán)力監(jiān)督問題格外敏感和重視,憲法法院的建立實(shí)際上就是一個加強(qiáng)權(quán)力監(jiān)督的結(jié)果。憲法法院的職權(quán)從性質(zhì)上說屬于憲法監(jiān)督權(quán),它是對所有國家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既有對聯(lián)邦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也有對州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既有對議會、政府的監(jiān)督,也有對法院的監(jiān)督;它以對國家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為主,也有對政黨甚至對公民的監(jiān)督。德國憲法法院是憲法監(jiān)督的專門機(jī)關(guān),行使憲法監(jiān)督權(quán),這種權(quán)力是新權(quán)力,不是原三權(quán)的任何一種,兼具司法和政治的雙重特點(diǎn)。憲法法院的憲法監(jiān)督在原理上與我國檢察機(jī)關(guān)法律監(jiān)督作用類似,這也間接印證了將監(jiān)督其他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是否遵守憲法和法律的權(quán)力獨(dú)立出來,成立專門的憲法監(jiān)督機(jī)關(guān)及法律監(jiān)督機(jī)關(guān)的合理性。憲法法院是憲法層次的監(jiān)督,保證憲法的實(shí)施,而我國人民檢察院是法律層次的監(jiān)督,保證法律的統(tǒng)一正確實(shí)施。憲法最高法的性質(zhì)決定了憲法監(jiān)督是實(shí)質(zhì)性和終局性的,憲法法院作出的結(jié)論應(yīng)該得到所有國家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的尊重,包括代表民意的立法機(jī)關(guān),憲法監(jiān)督是自上而下的監(jiān)督。法律的效力低于憲法,我國檢察機(jī)關(guān)是法律監(jiān)督機(jī)關(guān),與憲法上規(guī)定的行政機(jī)關(guān)和審判機(jī)關(guān)是平行關(guān)系,檢察機(jī)關(guān)的憲法地位和權(quán)力性質(zhì)決定了法律監(jiān)督的方式是程序性的和非終局性的,法律監(jiān)督是平行的監(jiān)督。為了強(qiáng)調(diào)檢察機(jī)關(guān)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力的嚴(yán)肅性,強(qiáng)化法律監(jiān)督的功能,當(dāng)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最高人民法院案件抗訴后,最高人民檢察院仍然認(rèn)為判決結(jié)果錯誤,可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裁決。
二、民事再審抗訴權(quán)的功能
(一)監(jiān)督司法權(quán),促進(jìn)司法獨(dú)立和司法公正
1.司法權(quán)是公權(quán)力,應(yīng)該受到監(jiān)督。“一般的說,法律,在它支配著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場合,就是人類理性;每個國家的政治法規(guī)和民事法規(guī)應(yīng)該只是把這種人類理性適用于個別情況。”社會治理方式從人治走向法治是人類智慧的創(chuàng)造和理性的選擇。法治的核心是用法律規(guī)范、控制、保障公權(quán)力的運(yùn)行,保障人權(quán)。“一切有權(quán)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quán)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jīng)驗(yàn)。有權(quán)力的人們使用權(quán)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權(quán)力濫用,就必須以權(quán)力制約權(quán)力。”[4]審判權(quán)也是國家的一種公權(quán)力,也存在被濫用的可能性,也應(yīng)該受到制約和監(jiān)督。在我國,法院主要是依據(jù)法律審判案件的,而檢察院是監(jiān)督法律統(tǒng)一正確實(shí)施的專門機(jī)關(guān),理應(yīng)對法院適用法律的審判活動實(shí)施監(jiān)督。因此,加強(qiáng)對審判權(quán)的監(jiān)督,防止審判權(quán)的濫用是檢察機(jī)關(guān)的應(yīng)盡之責(zé)。
2.司法權(quán)的獨(dú)立是相對的。司法權(quán)的獨(dú)立不是為了獨(dú)立而獨(dú)立,而是為了實(shí)現(xiàn)維護(hù)司法公正、保證人權(quán)的最終目標(biāo)。我國檢察機(jī)關(guān)的設(shè)置是為了保證法律統(tǒng)一正確實(shí)施,維護(hù)司法的公正,保證人權(quán)。二者的目標(biāo)是共同的。但有些同志以三權(quán)分立制度所奉行的司法權(quán)獨(dú)立為由否定檢察機(jī)關(guān)對法院訴訟活動的監(jiān)督,尤其是否認(rèn)檢察院的民事法律監(jiān)督存在的合理性,持這種觀點(diǎn)的人沒有意識到我國的政治體制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審判權(quán)的行使要接受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的一般監(jiān)督和檢察機(jī)關(guān)的專門監(jiān)督;沒有意識到在西方國家三權(quán)分立的制度模式中,審判權(quán)獨(dú)立也是相對的:行政機(jī)關(guān)掌握法院的人事任命權(quán),可在訴訟之外對其進(jìn)行控制,也可以在民事、刑事公訴中指揮檢察官在訴訟之內(nèi)進(jìn)行監(jiān)督;而且在刑事審判領(lǐng)域,對于重罪的犯罪事實(shí)是否成立是由大陪審團(tuán)進(jìn)行認(rèn)定的,法官只決定法律的適用,因此,從案件具體審理上講,審判權(quán)也不是絕對獨(dú)立的。
3.民事再審抗訴與法院獨(dú)立審判并行不悖。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在建立了憲法法院的德國等國家,普通法院的裁決不再具有終局性,當(dāng)普通法院的裁決違反憲法時,憲法法院可以改變其終審裁決。通過司法審查,憲法法院可以宣布立法、執(zhí)法或司法決定,因違反《基本法》所保證的基本權(quán)利而無效,并要求相應(yīng)政府機(jī)構(gòu)作出合適的修正。[5]可見德國憲法法院的出現(xiàn),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普通法院審判獨(dú)立和判決的既判力理論,在效率和公正的價值選擇中選擇了公正,這種修正是實(shí)質(zhì)性的和終局性的。從我國憲法規(guī)定反映出檢察機(jī)關(guān)與法院是平行的關(guān)系,檢察院獨(dú)立行使檢察權(quán),法院獨(dú)立行使審判權(quán),都不受行政機(jī)關(guān)、社會團(tuán)體和個人的干涉。檢法兩家憲法上的平行關(guān)系決定了檢察機(jī)關(guān)對法院民事審判活動的監(jiān)督是程序性的,不是實(shí)質(zhì)性的和終局性的,只是啟動法院審判監(jiān)督程序并參與審理案件,具體怎么審理,怎么判決還是由法院最終決定,從這個角度講檢察機(jī)關(guān)的監(jiān)督?jīng)]有代替法院具體審理案件,也沒有影響審判權(quán)的獨(dú)立行使,而且通過法庭上發(fā)表檢察意見使法院做到兼聽則明,促進(jìn)了審判權(quán)的依法公正行使
(二)民事再審抗訴權(quán)具有保證人權(quán)的功能
1.再審制度是必要的非常規(guī)的權(quán)利救濟(jì)制度。“無救濟(jì)的權(quán)利即非權(quán)利。”要實(shí)現(xiàn)權(quán)利必須有救濟(jì),而救濟(jì)是要國家公權(quán)力發(fā)揮作用,最后的途徑是經(jīng)過法院的審判。法院審理案件要通過訴訟程序,而包括民事訴訟程序在內(nèi)的所有訴訟程序都有可能輸出非正義的結(jié)果,因而也就有糾正這種非正義結(jié)果的特殊的救濟(jì)程序,在國外稱之為再審程序,我國稱之為審判監(jiān)督程序。這種特殊的救濟(jì)程序,各國民事訴訟法有不同的規(guī)定。美國聯(lián)邦民事訴訟規(guī)則規(guī)定的再次審理制度是對生效判決實(shí)施的重新審理,重新審理的法定事由有:錯誤;疏忽;新發(fā)現(xiàn)的證據(jù);欺詐等。德國、法國的民事訴訟法分別規(guī)定了再審的種類和再審的理由,再審的理由有程序性的(無效之訴)和實(shí)體性的(恢復(fù)原狀之訴)。我國自古以來非常重視再審制度的補(bǔ)偏救弊功能,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以整章十四個條文規(guī)定了審判監(jiān)督程序。
2.既判力與再審制度——公正與效率的平衡。從以上這些國家民事訴訟法中再審程序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可以看出,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事訴訟制度的體系結(jié)構(gòu)中,再審都是一項(xiàng)不可或缺的補(bǔ)救性程序和制度,這反映了人民對實(shí)體正義和權(quán)利保障的追求,反映了人類自身認(rèn)識存在錯誤的可能性和對這種錯誤加以糾正的必要性,反映了民事訴訟制度理性發(fā)展趨勢。那種對法院判決既判力的過度推崇,即使是錯誤的判決也要堅(jiān)持,弱化再審制度,主張取消檢察院民事再審抗訴權(quán)的觀點(diǎn)是錯誤的,有違民事訴訟法理性的發(fā)展趨勢。判決不應(yīng)該因?yàn)槭欠ㄔ鹤鞒龅木彤?dāng)然具有權(quán)威性,判決的權(quán)威性來自于獲得判決的程序是公正的、判決的結(jié)果是公正的兩個方面。片面的強(qiáng)調(diào)判決的穩(wěn)定性而忽視判決本身的公正性,不能維護(hù)和形成司法權(quán)威。當(dāng)然無休止的不計(jì)代價的追求判決的公正,而忽視訴訟的效率和法的穩(wěn)定性也是片面的,需要在二者之間尋求平衡,尋求平衡的手段不是取消再審,而是嚴(yán)格規(guī)范再審條件和程序來實(shí)現(xiàn),通過嚴(yán)格的再審條件避免濫訴的發(fā)生,通過限定提起再審的時限來避免判決的過份不穩(wěn)定。再審程序不是常規(guī)的而是非常規(guī)的救濟(jì)程序。
3.民事抗訴權(quán)能最大限度保護(hù)人權(quán)。我國的審判監(jiān)督程序和其它國家的再審程序的共同點(diǎn)是對生效的判決、裁定重新審理,不同點(diǎn)是這些國家的再審程序是國家為個案當(dāng)事人設(shè)置的一種救濟(jì)程序,個人再審訴權(quán)是啟動再審之訴的制度化權(quán)利,而我國的審判監(jiān)督程序從字面的意思到法條的規(guī)定都強(qiáng)調(diào)了國家運(yùn)用公權(quán)力對審判過程實(shí)施監(jiān)督,不管是法院系統(tǒng)內(nèi)部啟動的監(jiān)督還是檢察院提起的抗訴都是公權(quán)力的主動運(yùn)作的結(jié)果,當(dāng)事人對再審只有申請權(quán),不必然導(dǎo)致再審。我國公民的起訴權(quán)和上訴權(quán)是制度化的訴訟權(quán)利,法院僅就形式進(jìn)行審查就可以受理案件,而再審是當(dāng)事人的申請,法院進(jìn)行實(shí)體審查才能進(jìn)入再審程序,如果法院裁定不允許再審,當(dāng)事人無法對此裁定提出復(fù)議或者上訴,因此再審申請沒有制度保障不是訴訟化的權(quán)利。
法治的核心是保證人權(quán),再審制度設(shè)計(jì)是為了保證人權(quán),是以犧牲法院生效判決的既判力為代價,對被害人的權(quán)利進(jìn)行非常規(guī)的救濟(jì),也就是用再審程序糾正審判權(quán)對個人權(quán)利的侵犯。限制公權(quán)力的最終目的就是保證人權(quán),而限制公權(quán)力的手段有兩個:公權(quán)力之間的制衡;權(quán)利制約權(quán)力。在我國審判監(jiān)督制度中,案件當(dāng)事人的再審申請不是制度化的訴權(quán),不必然引起法院的再審,用權(quán)利制約權(quán)力存在制度性障礙。即使把再審訴權(quán)制度化,但是如果由法院把握著再審條件的實(shí)體審查權(quán)并規(guī)定只有經(jīng)過實(shí)體審查滿足條件才能啟動再審程序。鑒于目前法院管理行政化的運(yùn)作方式和案件的層級請示匯報(bào)制度的客觀存在,法院自我監(jiān)督的弊端就會更多的發(fā)生,再審制度的權(quán)利救濟(jì)功能會因?yàn)榉ㄔ哼^度的過濾案件而不能發(fā)揮應(yīng)有的作用。而法院沒有當(dāng)事人的申請而主動發(fā)動再審程序,如果案件不涉及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必然和私法自治、當(dāng)事人的處分權(quán)相矛盾,也與審判權(quán)不告不理的消極運(yùn)作方式相背。因此建立民事審判監(jiān)督一元化的抗訴模式,由檢察機(jī)關(guān)審查當(dāng)事人的再審申請(除涉及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檢察機(jī)關(guān)可以主動抗訴外),決定是否啟動抗訴程序是合理的選擇。理由如下:其一,檢察機(jī)關(guān)是憲法規(guī)定的法律監(jiān)督機(jī)關(guān),監(jiān)督法院在民事審判中正確適用法律是法律監(jiān)督的應(yīng)有含義;其二,檢察機(jī)關(guān)對法院的監(jiān)督是外部監(jiān)督,而且在法律專業(yè)上具有天然的優(yōu)勢,其對當(dāng)事人的再審申請進(jìn)行實(shí)體審查是適宜的,得出的結(jié)論易于被當(dāng)事人接受;其三,檢察機(jī)關(guān)通過審查再審申請可以過濾不符合再審條件的案件,通過釋法析理幫助當(dāng)事人服判息訴,維護(hù)司法權(quán)威;其四,對于符合再審條件的申請,檢察機(jī)關(guān)依法提起抗訴必然引起法院的再審程序,從而實(shí)現(xiàn)對私權(quán)利的救濟(jì);其五,檢察官具有客觀義務(wù),通過對再審案件的審查,派員出庭參加訴訟,在尊重事實(shí)和法律的前提下發(fā)表意見,不受當(dāng)事人意見的左右,因此不會打破民事訴訟等腰三角形的訴訟結(jié)構(gòu),不會破壞當(dāng)事人訴訟地位的平等;其六,檢察官對案件事實(shí)認(rèn)定和法律適用意見的表達(dá),有助于法官全面審理案件,正確認(rèn)定事實(shí)和適用法律。總之,最終事實(shí)的認(rèn)定和法律的適用是法官的權(quán)力,檢察機(jī)關(guān)民事抗訴權(quán)的運(yùn)用不會危及審判獨(dú)立,而是有利于法院正確適用法律,保護(hù)人權(quán)。
三、民事再審抗訴權(quán)的特點(diǎn)——受到規(guī)范、控制的國家權(quán)力
(一)民事再審抗訴權(quán)是受體制制約的國家權(quán)力
民事再審抗訴權(quán)是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的具體權(quán)能,根據(jù)監(jiān)督者也要接受監(jiān)督的原理,民事再審抗訴權(quán)是受監(jiān)督和制約的權(quán)利。主要表現(xiàn)為:其一,制度化的外部監(jiān)督制約。我國憲法和檢察院組織法規(guī)定國家行政機(jī)關(guān)、審判機(jī)關(guān)、檢察機(jī)關(guān)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chǎn)生,對它負(fù)責(zé),受它監(jiān)督;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jī)關(guān)辦理刑事案件,應(yīng)當(dāng)分工負(fù)責(zé),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zhǔn)確有效地執(zhí)行法律。這些規(guī)定體現(xiàn)了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對檢察機(jī)關(guān)的一般監(jiān)督和檢察機(jī)關(guān)與其它機(jī)關(guān)之間的相互制約。其二,改革試點(diǎn)中的外部監(jiān)督,人民監(jiān)督員制度。近年來檢察機(jī)關(guān)在司法改革的實(shí)踐中,主動引入人民監(jiān)督員制度,這一制度是為了加強(qiáng)對檢察機(jī)關(guān)自身執(zhí)法活動的監(jiān)督而設(shè)立的,是對憲法和法律關(guān)于一切國家機(jī)關(guān)必須傾聽人民的意見、接受人民監(jiān)督的規(guī)定的具體體現(xiàn),這一制度試點(diǎn)的領(lǐng)域?yàn)闄z察機(jī)關(guān)的自偵案件,但隨著這一制度成熟和制度化,可以把人民監(jiān)督員監(jiān)督領(lǐng)域擴(kuò)大到民事抗訴領(lǐng)域。其三,內(nèi)部監(jiān)督和制約。我國憲法和檢察院組織法規(guī)定最高人民檢察院領(lǐng)導(dǎo)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lǐng)導(dǎo)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自治州、省轄市、縣、市、市轄區(qū)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任免,須報(bào)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提請?jiān)摷壢嗣翊泶髸?wù)委員會批準(zhǔn)。雖然憲法中規(guī)定了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由地方各級人大選舉產(chǎn)生,地方各級檢察院對產(chǎn)生它的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負(fù)責(zé),但這并不意味著檢察院行使職權(quán)就代表了地方的意志,檢察權(quán)不能理解為地方固有的權(quán)力。檢察機(jī)關(guān)上下級領(lǐng)導(dǎo)體制是為了有利于維護(hù)法律在全國的統(tǒng)一正確實(shí)施,克服地方保護(hù)主義。
(二)民事再審抗訴權(quán)是程序化的權(quán)力
法治的核心是規(guī)范、控制和保障公權(quán)力的運(yùn)行,而對公權(quán)力規(guī)范和控制最好的辦法就是為公權(quán)力的運(yùn)行設(shè)置程序,公權(quán)力在程序設(shè)置的軌道上運(yùn)行就能更好發(fā)揮作用,既不越權(quán)也不會瀆職。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作為公權(quán)力,國家也必須設(shè)置相應(yīng)的程序,規(guī)范和控制它的行使,檢察機(jī)關(guān)法律監(jiān)督者的地位決定了這種程序?qū)⒏鼮閲?yán)格。檢察機(jī)關(guān)的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的行使是以訴訟的方式實(shí)現(xiàn)的,雖然立法權(quán)、行政權(quán)的行使也有其一定的程序,但在所有權(quán)力程序中司法訴訟程序最為規(guī)范、最為嚴(yán)格,這種嚴(yán)格的程序?qū)ΡO(jiān)督者與被監(jiān)督者都是一種約束,因此進(jìn)入司法程序的法律監(jiān)督其隨意性、自由裁量度都相對較少,規(guī)范性較強(qiáng)。在民事再審抗訴領(lǐng)域,檢察機(jī)關(guān)抗訴案件的范圍、條件、時間等程序問題在民事訴訟法中有相關(guān)規(guī)定,但有些規(guī)定還不夠科學(xué)和細(xì)致,有待進(jìn)一步完善。
總之,通過對民事再審抗訴權(quán)的性質(zhì)、由來、功能和特點(diǎn)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那就是民事再審抗訴權(quán)由檢察機(jī)關(guān)行使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3卷第309頁。
[2]胡錦光:“論公民啟動違憲審查程序的原則”,載《法商研究》2003年第5期。
[3]胡錦光:“論公民啟動違憲審查程序的原則”,載《法商研究》2003年第5期。
[4](法)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商務(wù)印書館2006年版,第102頁。
[5]參見張千帆著:《西方憲政體系》(下冊歐洲憲法),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