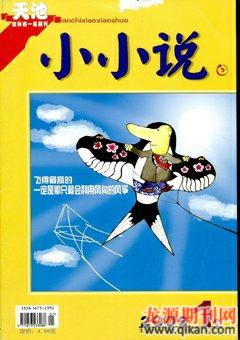感謝父親
2009-08-14 09:28:08吳富明
天池小小說
2009年1期
吳富明
打工之前,父親叫水生和他最后收割一次稻子。
父親的身子就如鐮刀一樣,在濕田里不停地抖動著。父親沒和水生說一句話。只見稻子成堆地被父親擺在身后。
水生想,父親永遠也改變不了老黃牛的本性。水生覺得自己是萬萬不能像父親一樣只知悶頭干活的。
歇歇吧,爹。水生叫了句,他感覺腰像散了架似的。
父親沒有吱聲。能聽見的只是鐮刀鋸裂稻子的雜聲。此時的父親正沉浸在一片喜悅中。沉甸甸的稻穗在他手里就是一年的希望。
終于到了田的另一頭。父親才抬起頭,輕輕直起身叫了句,水生,打穗啦。
歇夠腳的水生從田埂上站起來下到水田中,轉身抱了一把稻穗就打起來。
父親放下鐮刀,也過來打起穗。父親打得很起勁,稻草里幾乎沒有了稻穗。父親說,水生,打干凈些,不飽滿的谷子以后碾了糠還可以喂豬。
水生說,爹,這濕田爛地不好打,弄不好天就暗了。
父親說,你這是最后一次跟爹收割稻子,你就好好打吧,說不定天暗之前就打好了。你以后出外打工可千萬莫急性子呀。
水生說,爹,你就放心吧,我以后會寄錢回來給你的。打工比割稻子要強多了。
父親沒再說話。他手上的稻穗迎空而下,打得谷斗砰砰直響。
夕陽映在田里,像鋪上了一層金粉。父親說,水生,我打了一輩子稻,就喜歡這個時候的光,看起谷子來,像一粒粒金豆子呢。
水生說,爹,那是你的幻覺。小時候,我們村小學的語文老師也常這么教的。現在,我看哪,這個時候是涼,太陽小了嘛。……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