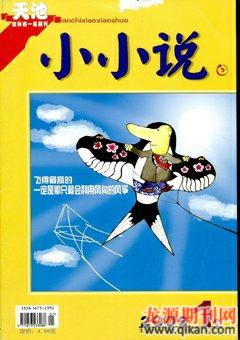量變
2009-08-14 09:28:08無字倉頡
天池小小說
2009年1期
關鍵詞:黨校
無字倉頡
黨校的劉一凡打來電話:“老同學,請你喝酒怎么樣?帶上清若。悅來餐館,我等你們!”我笑了,這家伙準又撈著白吃白喝的了。
劉一凡是個很夠意思的人,有什么好事總不忘舊友。大學畢業,有能耐的老爹立馬就給他在黨校找了個休閑處所,一周兩節馬列主義哲學。而我流浪了一年多才頭破血流地找到一所技工學校,教文化課。人比人,氣死人。
我和未婚妻清若大一認識,戀愛四年做了四年的焦點。
我和清若打車過去。小店不大,倒也干凈,上座率蠻高。這次劉一凡還真不是白吃白喝,餐館小老板請他題了個店名,擺一桌作為酬謝。席間,矮個兒長臉的小老板聽劉一凡介紹我是市作協會員,馬上恭敬有加,一個勁兒地遞煙倒酒,還忙不迭地給清若添茶。
小老板自報家門叫朱永和,年齡長我兩歲,早年也是名文學愛好者。據他說,投了三年稿,一篇沒發。那時候沒電腦,光復寫紙就用了好幾包。
朱老板喝酒上臉但是真能喝,扎啤一口“扎”進去一杯。喝多了又罵又夸,罵編輯罵城管罵工商,夸“3?15”夸女明星夸我們這些教書的。最后,特意夸了清若,“驚為天人驚為天人吶!”
這以后,我們成了朱永和店里的常客。有時候,劉一凡沒空,朱永和就直接給我們打電話。朱永和平時愛繃臉,給人感覺很嚴肅,但一笑又馬上燦爛如花,有點像川劇里面的變臉。我們一去,他這朵花就永遠開著。
有一次,我和清若趕到店里時,劉一凡已等在那里了。朱永和撥弄著手機說:“正想打電話催你呢!說話兒就來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今日農業(2021年11期)2021-11-27 10:47:17
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20年5期)2020-12-14 07:02:12
蘭臺內外(2017年5期)2017-06-06 02:24:11
學習月刊(2016年2期)2016-07-11 01:52:40
中國老區建設(2016年10期)2016-02-28 09:34:37
中國老區建設(2016年8期)2016-02-28 09:33:58
河南科技(2014年11期)2014-02-27 14:18:00
河南科技(2014年14期)2014-02-27 14:12:21
黨政干部論壇(2014年8期)2014-02-27 09:20:50
中國火炬(2012年1期)2012-07-24 14:12:06